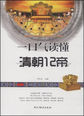熙熙攘攘的人流一出学校门口,就四散开来,像平躺着的一棵大树,学校出门前那一二十米的路就是树干,两头分别是树根和树枝。我站在学校门口,认真地扫描路过学校门口的一张张年轻的脸,他们笑里有一股春风荡漾,眉睫中跳动着朝气蓬勃,举手投足间是满眼里的芳华。不服老不行呀,到了我这年纪,脸上沟壑交错,黄沙遍布,没有一点生机,即使笑也是半是沧桑,半是泪水。
“老公,你回来一趟好吗?我想你了,咱儿子最近有点事。电视上的人说,你们干警察的是经济上的矮人,身体上的病人,生活中的苦人,家庭中的罪人,杨春江你一当警察就不是人了!你离家一走就快2个月了,我打电话你总占线,你这警察当的连自己老婆的电话都没有时间接了,你心里根本没有我和儿子。”老婆给我打电话,我不想接,一看是她的电话,马上就按拒绝键。急得她没有办法,给我发来了这样的短消息。
说实在话,我不是不想老婆和孩子,一进警务室,就像新兵进了部队一样,根本没有家的概念,总被这样或那样的事缠着。刚结婚的那段时间,几天不见老婆裤衩就肿得像小鼓,现在一个多月没有沾上腥竟没有一点感觉,也真奇了怪,不服老不行呀,男人老了,鼻涕多了,怂少了。老婆是人家的好,儿子是自己的好,大部分男人都有这种感觉,一听说儿子有点事,我马上有些紧张了,辛苦来辛苦去还不是为了儿子?
我急忙拨通了老婆的电话:“庆云,我是春江,咱儿子有什么事?”
“没有什么事,就是你儿子最近学习不上心,成绩从全班的前几名,已经滑到了末几名,老师打电话来,说还与一个女学生谈什么恋爱。”
“不可能吧,我到三十多才谈恋爱,他才十五六岁就开始了,这进化的速度也太快了吧!”
“别管怎么说,为了儿子,你回来一趟吧,怎么说也是你的家吧,是不是家外有家了?”
“你说什么呢?我前列腺肥大也不是一天了,哪还有能力家外有家?就是章子怡范冰冰躺在我床上,我也没有能力了。”
“回来吧,人家怪想你的。你不回来,找个生气的人也没有。”
“回来可以,别给我脸色看了,又哭又闹的,我好歹在支队当过支队长,楼上楼下、楼左楼右的都是我的部属,让他们听到了,我的表率作用哪里去了?”
“不——会——了!”老婆拉着长声,在电话里笑了,“保证不会了!”
女人挺怪的,你不理她了,她倒找你了;你天天和她在一起,她倒烦你了,不是吵就是闹。既然老婆有圣旨,也答应不再哭闹了,算是给足了我面子,我也该回家看看了。这女人呀,是张弹簧床,你硬她就瓤。我这个人在女人面前是比较容易满足的,好歹是自己的老婆,我简单地收拾一下警务室,换了一身衣服,就回到了家里。
我老婆姓柳,叫柳庆云,我姓杨,叫杨春江,我俩结婚的时候,她23岁,我32岁。当时部队对于在北京找对象有严格的规定,虽然不是二五八团的说法,至少不到30岁不能结婚,结婚可以,男方或女方必须调离北京市。为了能找一个北京姑娘结婚,我一下子忍了7年,你说我容易吗?我们结婚的第一年就有我们的儿子,我俩属于恋爱时间不长就结婚,结婚时间不长就生育的那种,不像现在的年轻人,不结婚只恋爱,结了婚也不生育,非要等着玩够了再生育。本来我给儿子起的名字叫杨秋收,我儿子是秋天生的,与秋收起义的日子就差一天,多有意义,多气派,这是红军的后代!老婆说你看你那土样,走到哪里也跑不了你那高粱花子样,你姓杨,我姓柳,儿子叫杨柳多好,于是我儿子就叫了杨柳。杨柳这孩子从小就聪明,专家说夫妻双方相隔1000里以上,生出来的孩子最聪明,我们刚刚及格,从河南濮阳到北京直线距离最多1000里。
家还是那个家,样子没有多大变化,却多了我最反感的东西——狗。狗一见我进了家门,先是瞪着两眼围着我团团转,然后汪汪地狂吠起来,我喊道:“滚一边去,狗东西!”这狗并不听我的话,仍是汪汪个不停。
我老婆从卧室里出来,揉着惺忪的眼睛,长睫闪动,红唇微微启动,舌头在她嘴里搅来搅去,我以为她要笑了,最后也没有笑出来,看到她这个样子我倒笑了。
老婆先开了口:“真回来了。”
“真回来了。老婆在家,我能不回来吗?”
“别净拣好听的说,这么长时间不回家,你不知道人家想你吗?”
老婆抱住我,趴在我怀里嘤嘤地哭起来。我双手揽住老婆的腰不知如何是好。狗坐在地上,瞪着硕大的眼睛看着我们,不时发出汪汪的叫声。
不知什么原因,经老婆这一哭一抱,我突然来了感觉,两腿之间的手电筒突然亮了,像汽车碰见了绿灯,让我有了突然加油门的想法。
我问:“孩子在家吗?”
“没有。”
我抱着老婆就上了床,老婆飞快地脱光自己的衣服,闭着眼躺下了。
“防盗门锁上没有?”
“锁上了。”
半年与老婆没有正儿巴经的行房,我似乎年轻了许多,折腾几下,老婆就大汗淋淋了,我一点疲乏的感觉也没有。养精千日用精一时,等我一泻千里的时候,老婆彻底崩溃了。事后,她躺在我怀里,温柔得像只小猫。我俩赤裸着身体拥在一起,仿佛水中并排游动的两条鱼。
“春江,你是不是在外边有新的了。”
“胡说,公粮都不一定有交的了,哪有余粮可卖。”
“你不在的时候,开始没有感觉什么。时间一长,就不一样了,还真有点想你,晚上还做关于你的梦。”
“好,想我就好。咱儿子怎么回事?”
“上一学期末还挺好的,不知什么原因,这次月考考得很差,从全年级的前几名,一下子滑落到班里的下游学生。我说他,他不听,我行我素,他姥姥说是孩子的青春期逆反心理在作怪,这逆反的时间也太长了点,从初一就开始逆反,现在都高二了!最近,我老见他拿着手机瞎按,也不知道人家干什么!”
“他现在几点放学?”
“5点半,回到家里快7点了。”
“离家也就三公里的路,坐公交车得一个半小时?你没有想过这段时间他去干什么吗?”
“没有。咱这孩子原来挺听话的,从来都不乱跑。你还记得不?在部队的时候,你说派司机去接他,他到中关村上课外班回来,让他在上地桥等着,他一步都不敢离,天上下雨了他都不躲,愣是把衣服都淋湿了。”
“记得,那时候不是小嘛。现在多大了?当时8岁,现在16了。”
“你没有要过他的手机看看吗?”
“没有。他不让看。”
“我们公安网监部门通报,有的网络运营商利用手机网络传播淫秽色情信息,是不是我们的儿子也中毒了。”
“不可能,咱儿子从小在部队大院里长大,连女孩的手都没有拉过,还敢干这事?”
“你这就错了,越是没有见过越好奇,越容易出问题。抽时间,把儿子的手机拿过来,你好好看看吧!”这时,狗跑到我们床前,晃动着尾巴,“喂喂”地叫起来。
“男不养猫,女不养狗。你养狗干什么?”
“你不在家,我养条狗还不行了?”
“你不知道我这个人挺烦狗的。”
“狗有什么好烦的,互联网上不是说你们警察是条狗,谁有钱跟谁走吗?”
“你胡说什么?警察是吃地方政府财政的,不听人家的行吗?就如企业职工听老板的一样。人是铁饭是钢,装什么硬汉,饿你3天试试。”
“饿死不出声,冻死迎风站,你们警察应该有骨气。”
“哎,是该有骨气,我们也想有骨气,我们警察本身是政府的一个部门,能不维护政府的政策和规定?何况我们警察本身就是国家机器,没有油机器是不能运转的。狗叫这么凶,你看看它什么意思?”
“没有事,它想找我玩玩,或者见咱俩在一起玩,它嫉妒。几点了?”
“快5点了。”
“你快起来,到学校的路上,看看孩子到底干了些什么?”
“嗯,好的。”
我穿上衣服,就往学校里赶,到学校门口的时候,刚好五点半。熙熙攘攘的人流一出学校门口,就四散开来,像平躺着的一棵大树,学校出门前那一二十米的路就是树干,两头分别是树根和树枝。我站在学校门口,认真地扫描路过学校门口的一张张年轻的脸,他们笑里有一股春风荡漾,眉睫中跳动着朝气蓬勃,举手投足间是满眼里的芳华。不服老不行呀,到了我这年纪,脸上沟壑交错,黄沙遍布,没有一点生机,即使笑也是半是沧桑,半是泪水。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在部队的时候,从来没有感到自己老已将至,看着鲜活葱绿的战士们跳来跑去,感觉到自己和他们一样年轻,除了床上功夫从来没有感到力不从心。一转业到地方,晃若过了一百年,自己突然从青春年少到了耄耋之年,恍忽间怎么自己快退休了呢?在公安系统里工作这一年,特别是到社区工作这一段时间,晚上11点睡,早晨五六点就起,夜里基本上没有睡过囫囵觉。吃饭的时候,往往刚拿起筷子就来事了。一日三餐很少准时,不是早了就是晚了,不是凉了就是热了。就是上厕所这样的事也没有素净过,撒尿撒了一半,手机响了,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按到手机音乐自动播放键了呢。我最怕电话响,就像在新兵连里当新兵时听到紧急集合号似的。
学校门口的人流由稀到稠,由稠到稀,就是没有发现我儿子的影子,这小子干什么去了?我打电话问我老婆,杨柳回家了没有,老婆说没有。从学校到我家坐公交车十几分钟就到,现在已经过了半小时,他还没有到家,是不是出什么事了?我有些紧张起来。到派出所工作后,天天听说些五花八门的案子,今天这里杀人了,明天那里绑架了,弄得我神经兮兮的。最近又听说广东发生了人体器官贩卖案,我的汗毛都要竖起来。
我顺着从儿子学校到家可能走的路,一个站牌一个站牌地查,绝不放过任何一张年轻的脸,包括女性。儿子好像从人间蒸发了一样,老婆说没有回家,我在路上找不到。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越来越担心,不往好处想,张着嘴,瞪着眼,一次又一次地做着深呼吸,努力地控制自己的情绪。这小王八蛋跑到哪里去了,我心里不停地骂着他,好像他并不是我的儿子。
就在我快崩溃的时候,在清缘桥小区站牌前的一个石凳上,我发现两个年轻人正在变换着方式接吻。
男孩静静站立着,仿佛一尊任人顶礼膜拜的英雄雕像,任由女孩吻来吻去,耳际、双颊、嘴唇、脖子、胸脯……他不动弹,也绝不还“口”,她像吸吮果冻那样轻柔地吸吮他的双唇,发出“吧唧吧唧”的声音,然后,她用双手勾住了他的脖子,额头抵住他的额头,边呻吟边说着什么。
接着,男孩伸出他的舌头,像伸头爬行的蜗牛一样,把舌头伸得老长,去吻女孩的耳际、双颊、嘴唇、脖子、胸脯……女孩的热情被点燃了,闭着双眼,脖颈用力向后伸,细长白晰。男孩的舌头突然插进女孩的嘴里,一进一出的。瞬间,女孩的嘴像吃柿子一样,“滋滋”地吸着,两腮时而大时儿小,一鼓一鼓的。
我有些犯傻地看着两个孩子接吻,看着他们激情四射的表演。现在有些孩子太过分了,接吻这样私密的事一点也不避人,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想在哪里干就在哪里干。我想到了我老家农村打圈子的猪,发情的狗,他们才在当街不分场合和时机地干这些事。这个时代怎么了?这些孩子是进步了,还是退化了?
我正看着发呆,突然一个女高音传来:“杨春江,你干什么呢?”我回头一看是自己的老婆。
“找儿子呢?”我有些疑惑看着她。
“找什么找,这不是杨柳吗?”老婆指着接吻的男孩子,向我怒吼道。
“不会吧?”
“什么不会?”老婆像母狮子一样,瞪着眼大叫,“杨柳,杨柳!”
男孩一抬头,他确实是我的儿子杨柳!真没有想到,儿子与他女同学接吻的动作,比我们老两口子都花哨。也真邪门了,现在的孩子学习没有我们那时候刻苦,琢磨起接吻来倒挺专业,进化的速度太快了!
我儿子还真有点幽默大师的样子,一点也不害怕,也不着急,慢慢地推开他的女友:“干吗呢,妈,别把娜娜吓着了!”
我一看真是自己的儿子,脱下那带网网的警用皮鞋就要打他。谁知道我老婆和我儿子都笑了,我向上一瞧自己也笑了:鞋底与鞋帮开胶了,我只举着一个没有鞋帮的鞋底子!
我把鞋底一扔,骂了一句:“畜牲!”
儿子的女友一看势头不对,溜了。人家的孩子咱管不着,我只能管教自己的儿子,穿着没有鞋底的鞋,上去一脚把儿子跺了个狗啃泥。
儿子站起来,左手拍着自己屁股上的土,两个眼珠子斜视着我,放射着仇恨的怒火,咬牙切齿。
我和老婆带着儿子往家里走,他俩在前我在后,儿子不时回过头来看我一眼。老婆搀着儿子,问这问那,絮絮叨叨地说着,儿子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我看着儿子这样直叹气。本来挺好的孩子,这一年不怎么回家,想不到儿子的变化这么快。上半年在警院参加军转新警培训,一周回一次家,全国“两会”期间一个多月没有回家。下了派出所,开始三天一倒班回家一次,后来住到社区里,一二个月才回家一次。这一年,儿子学习退步了不少,接吻交女朋友的本事真是长得太大了。
回到了家里,我们仨人坐在沙发上。
“儿子,你说到底怎么回事,学习不怎么样,谈恋爱倒长本事了?!你现在是学生,学生的任务是以学为主。好好的时光你早恋了,把学习都耽搁了,将来长大了你干什么去?当兵?爸爸不在部队上了,当了兵也留不到部队上。”我的胸脯气得一鼓一鼓的,浑身哆嗦着,拍着茶几。
这时候,狗老实了,屁股坐在电视机前的地板上,两眼瞪着,静静地看着我,像一个懂事的孩子。老婆一会儿抬头看我一眼,一会儿抬头看儿子一眼。
儿子不说话,低着头,鼻子下边的小胡子黑黑的,不时地搭在他的嘴唇上,他像玩玩具似的轻轻地吹着。
“现在你就把胡子刮了,我们那时候穿个喇叭裤留个小胡子的都是小流氓,你现在可好,干的事比流氓都过火,八三年严打的时候,碰一下女孩的手就得判3年。你现在可好,当众都敢接吻。”
“你说什么呢,那不是一回事。”老婆见我说话过火了,怕诛连到她弟弟,顶我一句,“现在大街上这样的孩子多着呢,也不是咱杨柳一个。”
“什么?你还嫌儿子做得不到位,想教教他是不?什么不是一回事,孩子到今天这个样,都是你惯的!”
一听我说孩子是她惯成这样的,老婆立刻火了,一下子没有了下午床上的温柔,凶恶得像只母老虎,也真是,女人躺下是一只羊,坐起来是一条狼:“杨春江,你他妈的说清楚,什么都是我惯的,你一当警察,一年多不怎么回家,孩子我给你养着,我给你看着,怎么着了?孩子有事了,你倒给我发起火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