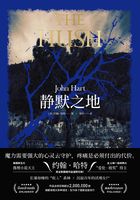冯至
——甚矣,吾衰也!
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也!
仲尼自从春天去了以后,意味的阑珊,情绪的萧索,更甚于前年西狩获麟,春秋绝笔的时候了。那时他满心满意地想,世态是一年不如一年,我的春秋写到这里也尽够了。天啊!你总还可以多给我几年的生命吧,我要努力在我这未来的几年以内,把我们先哲传下来的一本易经,整理一番;把我的哲学思想,都藉着这部古书表现出来,留给我的弟子们——咳,他们真是可怜,像是船没有舵,荒野浓雾中没有指南车呀——哪知到了现在,转瞬间,就快要两年了,易经,一点儿没有着手;春秋,也有刻在竹版儿上的,也有涂在一卷一卷的树皮上的,错错乱乱地在他的房里堆积着,向来不曾有过一个人来过问。就是那张古琴,伴着他流浪他乡,十四年总在身边的,现在挂在壁上,不但着了许多灰尘,并且结上了许多蜘蛛网了。他每每当着黄昏时节,倚着窗子望落日,领略着自然间的音乐,正在忘记物我,融会一切之际,房子里便会发出来一种苍茫的音调,使他回转头来,目光懒懒地落在那张琴上,他这般伤感地自语,不知说了多少次了——
——当年从我困于陈蔡的故人们,死的死了,不死的也多半在远方——只剩下这张琴,寂寞无语的琴……
田陇间一望无边的大麦,都渐渐地被南风吹黄。在这静的乡间,从黎明一直到了日暮,只有一种简单的,博大的情调管领着;风雨都很少有什么变幻。风靡一世,楚晋争霸,吴越消长的狂飚怒浪,总激荡不到这里,正如幽谷内的花木不曾有过一次的摇曳,深潭内的止水不曾起过一缕的皱纹。愚陋的农人们,在他们工作之余,便知道聚在一起谈些荒诞的齐东海滨的故事,他们都知道仲尼是读书知礼,圣人的后裔;见闻广一点的,更知道他曾经作过短期的鲁相,就是所谓当时的诸侯大夫,也是常常向他谈乐问礼的,所以他们对于仲尼都存着一个特殊的尊敬的心。或是河滨,或是原野,他们在那里又歌又舞时,若是一旦望见了仲尼,他那严肃的面庞,端正的脚步,岸然的态度,立刻都鸦鹊无声,歌的停了歌,舞的停了舞,静静悄悄地望着他,等着他走远了许久以后,才恢复了他们原来的欢歌漫舞。甚至于小孩子们,都听惯了他们父母的恐吓,“仲尼不是寻常的人呀”,所以连游戏都很少有在他的住房附近的,虽然他的住房同旁人的是一样的简陋,狭小,三两间泥草砌成的茅屋。
今天早晨,仲尼起得分外的早,这或者是因为他近日神魂不安,时有噩梦萦绕的原故。扶着杖,立在门前,仿佛有什么期待似的,向着远方发呆。鸟儿们的晨歌将罢,草地上的露珠,一颗颗地映着旭日的光;遍地的野花,昂然向着这皤白老叟微笑,含着几分嘲讽的意味,像是还在替那两个争辩不清的宋国的童子问,“你这自命圣者的圣者呀,到底是早晨的太阳近,还是正午的太阳近呢?”——但是他对于这些自然的景象,此时毫不注意;他只是想着,或者有一个弟子能够来吧,或者有什么人带来些外边的消息吧!等到了绝望的时候,便这般说,“咳,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事,哪能影子一般地随我一生呢!”——衰弱的目光,无力地望着,——北方的云雾已散,蔚蓝的泰山余脉,远远起伏地,展开在他的面前了。
二十年前,奔走齐鲁之间,追慕着古代的风光,正是要把自己的理想,实现在这争纷的世上,最热衷的时代。一天独自一个人登上泰山的高峰,澄滓太清,齐鲁俱滂薄于茫茫大气之内,自己不觉得胸怀高朗——
——呵,当初登上东山,觉得鲁国小,现在立在泰山颠,天下并不大呀!
现在呢,泰山依旧是那样嵯峨,可是旧日的气概,一点也没有了,耳边只是缠绕着一个樵夫的哭声,凄凄婉婉地。心里忽地一片苍凉,宇宙都似乎冰化了一般——一个久已消灭了的泰山樵夫的影子,有如白衣的神现在黑漆的夜色中,又回到他的忆念之内了——
——樵夫啊,你是世间的至圣!当我们在泰山的幽径里相遇时,你哭得是恁般的苦闷,岩石为之堕泪,鸟兽为之惊心!我愚蠢的人啊,我那时不但不能领会,还要问你为什么!樵夫啊,你说,你自伤,所以这般哀泣……茫茫天空,恢恢地轮……万物的无着无落,是这样锐敏地感动了你……你深入了人生的真髓,宇宙的深奥;我直到了今日,才能了解了你!
他的头脑眩昏,目光放出许多火花——泰山也似乎旋动起来,地在震动,远方的河水在沸腾……他颤着……
“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
杖,被掷在一边,颓然坐在阶上了。两手托着颐。
——赐呀,你来了?来得怎么这么晚呢!
他远远地望见一个衣冠济楚的人,渐渐辨别了知道是子贡以后,慈母见了远方归来的游子一般,两目射出来消逝了的旧日的光芒,迎上去,紧紧地握着了子贡的手。
——赐呀,你来得怎么这么晚呢!
子贡见他先生的神色,言语,都与往日不同,木鸡般愕然地立着了!使他忘记了种种的繁文,善于词令的子贡,一个字,都不知怎样说,才好。
——先生……
——赐呀,你看这座泰山呀——方才的兴奋,立刻又归于消歇;手扶着子贡的肩,师生两个缓缓地走了几步。你说他有时要崩堕吗?
——先生……
——寂寞呀……赐,你日日锱铢为利,你好久不到我这里来了……
子贡本来是因为货殖的事,由这里过,顺便看看先生,并且想问一问他近来对于政治上的意见。哪知出乎意外,先生说出这样悲痛的话,是他从来没有听过的。
——先生,可是病……
——我哪里有什么病,只是昨夜作了一个梦——咳,这样的梦,也不只一次了。你说,前面的泰山,有崩颓的那一天吗?
——先生,梦是无凭的;泰山是不会崩堕,如同哲人没有陨亡一样……
——赐呀……仲尼皱纹消瘦的颊上,缀了两颗绿豆大的泪珠了。
子贡慢慢地,扶着先生又坐在阶上,这时候太阳转到南方,被几片浮云遮护着。子贡站立在身旁。——等到浮云散开了以后,一只雄鸡高据在树之巅,叫起来了。
——赐呀,这是什么在叫?仲尼侥着头。一切都在白昼的梦里迷迷濛濛地。
——先生,是一只雄鸡。
——啊,一只羽毛灿丽的雄鸡呀!他抬起头,对着那只鸡望了许久。假如仲由还在,恐怕又要把他射了下来,把他的羽毛插在他的冠上;把他的血肉来供我的馐馔。可怜他金星随着太阳一般,傍着我车尘劳劳于卫楚陈蔡的路上,一日不曾离开过我;同着我一块儿受着隐士们的嘲笑,路人们的冷遇,——我又何益于他呢?他终于很惨怛地死了!赐呀,你的故乡,近来又有什么消息吗?我对于旧游的怀念,再没有比卫国更浓厚的。我的多少弟子故人,还都在那里滞留呀!
——自从听说出公跑到鲁国以后,那里沉寂得有如一座古井。
——咳,卫呀,淇水涟涟,绿竹漪漪——他又异样地兴奋了——我在那里的哀乐荣辱,在我的回忆里,一日比一日显明;使我的联想力一日比一日锐敏:我听见雁鸣在天空,便会想起卫灵公对我的冷淡;我听见车声在街心,便会想起南子车马的喧耀,雍渠的娇姿。往事都如梦如烟了。我那时岂不知道卫灵公除了南子以外,不知什么叫作政,什么叫作礼……我为什么又那样恋恋,来了又去,去了又回来呢……多少小人欺凌我,甚而至于南子,我都不能不向她揖拜……过去的,真是……
——先生那年住在蘧伯玉的家里,南子正在她的开花时代;她美丽得像是出水的芙蓉,灵公看待她像是一只娇美的孔雀。那天清新的早晨,我是不会忘记的,她立在轻倩的纱帷里,穿着一身雅淡的衣裳,环佩是泉水般的;虔虔地,弯弯地,向着先生问礼……在先生的面前,她何常像是一个罪过的人呢!
——现在的卫国,想已经不是往日一般地了!恐怕同着灵公墓上的草,是一样的荒乱了吧?——他沉吟了许久。想着卫国的内乱——咳,南子呀,卫国是因为她,乱到这般地步!她那时要见我,她哪里懂得我的一缕头发,她哪里懂得我的一声叹息!她见我,不过因为我的身子分外的高,我的头顶有些凹,想看看我这在她眼内觉得奇异的人罢了!她那没有灵魂的……女子同小人呀,是我生平厌恶的……
我是自己打算定了的,终身作一个东西南北的流浪人;郑人为我编成歌谣,说我茫茫如丧家之狗,这四字,真是恰当啊!流浪的人,是没有家室的,我也从没有一日以家室为怀。我为家室,早已任着它的自然而消灭了,家室啊,是我行为的障碍,是我思想之潮的堤防,我早已把它抛弃在比云还缥渺的虚无之乡了!死的,死了;散的,散了!
我抱着我的理想,流离颠沛,一十四年——卫呀,楚呀,陈呀……没有一个地方,能够用我一天,种种魔鬼的力,恐吓着我,讽刺着我,压迫着我,四海之大,没有一个地方,容我的身躯;终于不能不怀着惆怅,回到我这儿时的故乡——故乡真是荒凉呵,乡音入在耳里,泪便落在襟前了!没有一个人不说我是陌生人,没有一个人对我不怀着一些异殊的意味!儿时的门巷,变成一片瓦砾,生遍了鬼棘向我苦笑!防山侧父母的坟茔,已经被人踏平!我哪里还有读易奏琴的心情呢!
我悔不该回到故乡,故乡于我,失尽了它的意味了,赐呀,我还有几天的生命呢,天也无边,地也无涯,悠悠荡荡,我种种的理想,已化作一片残骸,由残骸化成灰烬了!后世呀,不可知的后世呀……
——后世,一定有认识先生的人……子贡寻不出另外可以安慰先生的话了,这淡如白水的慰语,丝毫不引起仲尼的注意——
——我为什么回到这个故乡来呢?我早就应该……我为什么不死在匡人的手里!为什么不死在陈蔡人的手里?那时候的死,是怎样的光荣!怎样的可以自傲!那个时候,有颜回在我的身边,仲由在我的身边,百十个弟子在我的面前!在弦诵声中死去,韵调是怎样的幽扬!怎样的美丽呀!现在,不肯“先我死”的颜回也死了,勇健的仲由也死了,百十个弟子,都个人走上个人的路了……死也要有死的时候……天呀,天呀……
仲尼一气说尽了多少天积蓄着的郁抑,两目像着了疯狂,两手按胸,不住地咳喘,淤塞着,再也说不下去了。子贡终于不大了解先生的这种心情上的骤然的改变,想用旁的话把先生的话路岔开,却寻不着适当的。
——先生,该是午餐的时候了吧?
——啊,——似乎;仲尼没有听清。
——午餐?
——……
——先生的精神太疲劳了!
——咳,疲劳呵——
——先生到房子里休息休息——
——休息?
——我到菜圃里去剪一些菜,为先生煮汤吧!
——你去吧,我到房子里……
子贡一步三回顾地,怀里怀着鬼胎,不知将来究竟要发生什么变故,走到房后的菜园里去了。仲尼依然坐在门前,他怕走进房内,同怕阴森的坟墓一样。远远近近,静悄得使人听着了万籁的极细微的呼吸……
正是傍午的时分。
泰山的余脉,又蒙上一层薄薄的云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