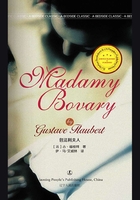沙汀
坐在其香居茶馆里的联保主任方治国,当他看见从东头走来,嘴里照例扰嚷不休的邢幺吵吵,他简直立刻冷了半截,觉得身子快要坐不稳了。
使他发生这种异状的有下面几个原因:为了种种糊涂的措施,他目前正处在全镇市民的围攻当中,这是一;其次,幺吵吵第二个儿子,因为缓役了四次好多人在讲闲话了;加之,新县长又是宣言了要整顿兵役的,于是他糊糊涂涂地上了一封密告,而在三天前被兵役科捉进城了。
但最重要的是:如全市镇所批评,幺吵吵是不忌生冷的人,什么话都说得出来的。而他本人虽不可怕,但他的大哥是全县极有威望的耆宿,他的舅子是财务委员,县政上的活动分子,并且,就是主任的令尊在世的时候,也是对幺吵吵那张嘴表示头痛的。
但幺吵吵终于吵过来了。这是那种精力充足,对这世界上任何物事都抱了一种毫不在意的态度的典型男性。在这类人身上是找不出悲观和扫兴的。他常打着哈哈在茶馆里自白道:
“老子这张嘴么,就这样,说是要说的,吃也是要吃的;说够了回去两杯甜酒一喝,倒下去就睡……”
现在,他一面跨上其香居的阶沿,拖了把圈椅坐了下去,一面直着嗓子,干笑着嚷道:
“嗨,对!看阳沟里还把船翻了么!”
他所参加的桌子已经有着三个茶客,全是熟人:十年前当过视学的俞视学;前征收局的管账,现在靠着利金生活的黄光锐;会文纸店的老板汪世模汪二。
他们大家,以及旁的茶客,都向他打着招呼:
“拿碗来,茶钱我给了。”
“坐上来好吧,”视学客气道,“这里要舒服些。”
“我要那么舒服的做什么哇,”出乎意外,吵吵红着脸叫嚷道:“你知道么,我坐了上席会头昏的……没有那个资格!”
本分人的视学禁不住红起脸来。但他立刻觉得幺吵吵是针对着联保主任说的,因为在说的时候,他看见他满含恶意地瞥了坐在后面首席上的方治国一眼。
除却主任,那桌还坐着的有张三监爷。他们都说他是方治国的军师,但实际上,他只能跟主任坐坐酒馆。在紧要关头,尽点忠告。但这又并不特别,他原是对什么事也关心的,而往往忽略了自己。他的老婆在家里是经常饿着饭的。
同监爷对坐着的是黄毛牛肉,正在吞服着一种秘制的戒烟丸药。他是主任的重要助手;虽然并无过人之才,唯一的特点是毫无顾忌;“现在的事你管那么多做什么哇,”他常常说,“拿得到的你就拿!”
他应付这世界上一切足以使人大惊小怪的事变,只有一种态度,装做不懂。因此,他小声向主任说道:
“你不要管他的,”他眨眼而且努嘴,“发神经!”
“这回子把蜂窝戳破了。”主任发出苦笑说。
“我看要赶紧‘缝’啊,”监爷拿着暗淡无光的黄铜水烟袋,沉吟道:“另外找一个人‘抵’怎样?”
“已经来不及了呀。”
“不要管他的,”牛肉道,“他是个火炮性子。”
这时,幺吵吵已经拍着桌子,放开嗓子叫了。但他的战术还停留在第一阶段上,即并不指出被攻击的人的姓名,只是隐射着,似乎像一通没头没脑的谩骂。
“搞到我名下来了。”他佯装着打了一串哈哈,“好得很!老子今天就要看他是什么鸡巴入出来的:人鸡巴,狗鸡巴,你们见过狗鸡巴么,嗨,那才有兴趣!”
于是他又比又说地形容起来了,虽然已经蓄了十年上下的胡子,但他是以粗鲁话出名的。许多闲着无事的人,有时甚至故意挑弄他说下流话。他所谓的“狗”是指他的仇人说的。因为主任的外祖当过衙役,而这又是方府上下人等最大的忌讳。
因为他形容得太难堪了,那视学插嘴道:
“少造点口孽,有道理讲得清的。”
“我有什么道理哇!”吵吵忽然正色道,“有道理我也当什么鸡巴主任了。两眼墨黑,见钱就拿!”
“吓,邢表叔!”
气得脸青面黑的瘦小的主任,一下子忍不住站起来了。
“吓,邢表叔,”他说,“你说话要负责啊!”
“什么叫做负责哇!我就不懂,——什么人是你的表叔,你认错人了,是你表叔你也不吃我了!”
“对,对,对,我吃你。”主任解嘲地说,一面坐了下去。
“不是吗?”吵吵拍了一掌桌子,“兵役科的人亲自对我老大说的!你的报告真做得好呢。我倒要看你今天是长的几个卵子……”
他愈说,就愈觉得这并非玩笑的事。如一向以来的瞎吵瞎闹一样,他感到愤激了。
他相信,要是一年或者半年以前,他是用不着怎样着急的,事情好办得很,只需给他大哥一个通知,他的老二就会自自由由走回来的。而且以往他就避掉过四次。但现在是不同了,一切都要照规矩办了。而且更重要的,他的老二已经抓进城了。
照经验,事情一露了头,弄到县长面前去了,就难办的。他已经派了老大进城,但带来的口信是:因为新县长的脾气还不清楚,而且一接印就宣布他是要整顿兵役的,所以他的伯爷和舅父都表示情形的险恶。额外那捎信人又说,壮丁就要送进省了。
凡是邢大老爷们都感觉棘手的事,人还能有什么办法呢?这也是说,他的老二只有作炮灰了。
“你怕我是聋子吧,”幺吵吵简直在咆哮了,“去年蒋家寡母子的儿子五百,你放了;陈二靴子两百,你也放了!你比土匪头儿肖大个子还厉害,钱也拿了,脑壳也保住了,——老子也有钱!你要张一张嘴呀……”
“说话要负责啊!邢幺老爷!”
主任咕噜着,而且现出假装的笑容。
这是一个糊涂而胆怯的人。胆怯是因为富有,而且在这个边野地方,从来没有摸过枪炮的原故。这里是每一个人都能来两手的。他一直规规矩矩地吃着祖宗的田产,在好几年以前,因为预征太多,许多人怕当公事,于是在一种策动下,他当团总了。
他明白这是阴谋。但一向忍气吞声的日子引诱他接受了这个挑战。他起初老是垫钱,但后来他发觉甜头了:回扣,黑粮等等,并且走进茶馆的时候,招呼茶钱的声音也来得更响亮,更众多了。
而在五年以前,他的大门上已经有了一道县长颁赠的匾额:
“尽瘁桑梓。”
但不管怎样,如他自己所感觉的一般,在回龙镇,还是有人压住他。他看得清楚,所以他现在很失悔做了糊涂事情。他老是强笑着,满不在意似的说道:
“你发气做什么啊,都不是外人……”
“你也知道不是外人么?”对方反问道:“你知道不是外人,就不该搞我了,告我的密了!”
“我只问你一句!”
主任又站起来了。他笑问道:
“你说一句就是了:兵役科什么人告诉你的?”
“总有那个人呀!”
吵吵说,十分气派地摊在圈椅里面;一面冷笑着加添道:
“像还是我造谣呢。”
“不是,你要告诉我呀。”
看见吵吵松了劲,主任知道可以说理的机会到了。他就势坐向视学侧面去,赌咒发誓地分辩起来,说他是一辈子都不会做出这样胆大糊涂的事情来的。
但却并不向着吵吵,而是视学们。他说:
“你们想吧,”他平摊开手,侧仰他那瘦瘦的铁青的脸蛋,“你们想,我是吃饭长大的呀!并且,我一定要他去做什么呢?难道委员长会给我一个状元当么?没讲的话,这街上的事,一向糊得圆我总是糊的!”
“你才会糊!”吵吵叹着气抵了一句。
“那总是我吹牛啊!”主任无可奈何地说,“别的不讲,就拿公债来说吧,别人写的多少,你写的多少?”
他又挨近视学的耳朵呻唤道:
“连丁八字都是五百元呀!”
他之所以说得如此秘密的有两个原因,其一,是想充分表示出事情的重要性;又其一,是因为街上看热闹的人已经多了。公开宣布出来究竟太不光彩,而且容易引起纠纷。
大约视学相信了他的话,或者被他的诚意感动了。兼之又是出名的好好先生;因此他劝解道:
“幺哥!我看这样啊,”他斯斯文文地扫了扫喉咙,“人不抓,已经抓去了,横竖是为了国家……”
“这你才会说呢!”吵吵一下撑起来了:“这样会说,你怎么不把你自己的送去呢?”
“好!我不同你讲。”
视学红着脸说,故意勾脑袋吃茶去了。
“你讲呀!”吵吵重又坐了下去,继续道,“真是没有生过娃娃不晓得×痛!怎么把你个好好先生遇到了啊!东瓜做不做得甑子?做得。蒸垮了呢?那是要垮的,——你个老哥子真是!”
他的形容引来了一片笑声。但他自己并不笑,他把他那结实的身子移动了一下,抹抹胡子,宣言道:
“闲话少讲!方大主任,说不清楚你走不掉的!”
“好呀,”对方漫应着,一面懒懒退回原地方去;“回龙镇只有这样大一个地方哩。往那里跑?要跑也跑不脱的。”
他的声口和表情照例带着一种嘲笑的意味,至于是嘲笑自己或是对方,那就要凭你猜了。他是经常凭藉了这点武器来掩护他自己的。而且经常弄得顽强的敌手哭笑不是。他们叫他做软硬人。
当回到原位的时候,他的助手一面吞服着戒烟丸,生气道:
“我白还懒得答呢,你就让他吵去!”
“不行不行,”监爷意味深长地说,“事情不同了。”
他一直这样坚持自己的意见是有理由的。他确信镇上已在进行一种大规模的控告;而且邢大老爷是可以左右它的;他可以使这成为事实,也可以打消它,所以连络邢家乃是一个必要的步骤。
何况谁知道新县长是怎样一副脾气的人呢!
这时候,茶堂里的来客已增多了。连平时懒于出门的陈新老爷也走来了。新老爷是科举时代最末一次的秀才,当了十年团总,十年哥老会的头目,八年前才退休的。但他的说话还是同团总一样有效。
这可见幺吵吵已经布置好一台讲茶了。茶堂里响着一片呼唤声,有单向堂倌叫拿茶来的,有站起来让座位的,有的甚至于怒气冲冲的吼道:
“不许乱收钱啦!嗨!这个龟儿子听到没有……”
于是立刻跑去塞一张钞票在堂倌手里。
在这种种热情的骚动中间,争执的双方,已经变平静了。主任知道自己会亏理的,他在殷勤地争取着客人,希望能于自己有利。而幺吵吵则一直闷气着,这是因为当着这许多漂亮人面前,他忽然直觉到,既然他的老二被抓,这就等于说他已经没面子了。
这镇上是流行着这样一种风气的,凡是按规矩行事的,就是平常人,重要人物都是站在一切规矩之外的。比如陈新老爷,他并不是惜疼金钱的脚色,但就连打醮这种小事他也是没有份的;不然便是惹起人们大惊小怪,以为新老爷失了面子,快倒霉了。
面子在这里就如此的厉害,所以吵吵闷着脸,只是懒懒地打着招呼。直到新老爷问起他是否欠安的时候,他才稍稍振作地答道:
“人倒是好的,”他苦笑着,“就是眉毛快给人剪光了!”他一连打了一串干燥无味的哈哈。
“你瞎说!”新老爷严肃地晃着脑袋,切断他。“你瞎说!”
“当真呢,不然也不敢劳驾你老哥子动步了。”
为了表示关切,新老爷叹了口气,并且问道:
“大哥有信来没有呢?”
“他也没办法呀!”
吵吵呻唤了。但为了免除人们的误会,以为他的大哥已经成了没面子的脚色,遂又立刻加上一番解释:
“你想吧,新县长的脾气又没有摸到,他怎么办呢?常言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他又是闹起要搞兵役的;谁晓得他会发什么猫儿毛病呢!前天我又托蒋门神打听去了。”
“这个人怕难说话,”一个新近从城里回来的小商人插入道,“看样子就晓得了:戴他妈副黑眼镜子……”
但严肃沉默的空气没有使小商人说下去。
大家都不知道应该如何表示自己的感情才好。表示高兴是会得罪人的,因为情形确乎有些严重;但说是严重吧,也不对,这又将显得邢府上太无能了。所以彼此只好暧昧不明地摇头叹气,喝起茶来。
看出主任有点焦灼和担心的神情,似乎正在考虑一种行动,牛肉包着丸药,小声道:
“不要管,这么快县长就叫他们喂家了么!”
“去找新老爷是对的!”监爷说。
这个脸面浮肿,常以足智多谋自负的没落者的建议正投了主任的机,他是已经在考虑着这个必要的办法的了。
使他迟疑的是他和新老爷的关系,与新老爷同邢家的关系的比较。他觉得差得多,并且虽然在派款和收粮上面,并没有对不住团总的地方,但在几件小事情上,他是开罪过他的。
比如,有一回曾布客想压制他,抬出老团总的招牌来,说道,
“好的,我们在新老爷那里去说!”
“你把时候记错了!”他发火道,“前几年的皇历用不上了!——你想吓倒我不行!”
后来,事情虽然依然在团总的意志下和平解决,但他的话语也一定散播开去。团总给记下一笔账了。可是他终于站起身来,向了新老爷走去。
这行动立刻使人们振作起来了,他们都期待着一个新的开端和发展。有几人在大叫拿开水来,以图缓和一下他们紧张的心情。吵吵自然也是注意到主任的攻势的,但他不当作攻势看,以为他是要求新老爷转圜的。但他却猜不准转圜的方式。
而且,他又觉得,在他目前的处境上,任何调解他都是难于接受的。这不能道歉了事,也不能用金钱的赔偿弥补,那么剩下的只有上法庭了。然则在一个整伤兵役的县长面前这件事他会操胜算么!
他觉得苦恼,而且一切都不对劲,这个坚实乐观的人第一次被烦扰所袭击了。
他在桌面上拍了一掌,苦笑着自言自语道:
“哼,乱整吧,老子大家乱整!”
“你又来了,”那视学说,“他总会拿话出来说呀。”
“这还有什么说的呢?你个老哥怎么不想想啊:难道什么天王老子还有面子把人给我取脱手么?!”
“不是那么讲。取不出来也有取不出来的办法的。”
“那我就请教你,”吵吵依旧忍耐着说,“什么办法呢?!说一句对不住了事?打死了让他赔命……”
“也不是那样讲……”
“那又是怎样讲?”他简直大发起火了:“老实说吧!他就没有办法!我们只有到场外前大河里去喝水。”
他愤怒地吼叫着,真像要拚掉他的命了。
这宣言引起一阵新的骚动,许多人都像预感到节目的精彩部分了。一个看客,他是立在阶沿下人堆里的,他大声回绝着朋友的催促:
“你走你的嘛!我还要玩一会!”
茶堂倌也在兴高采烈叫道:
“让开点,你个龟儿子,看把脑壳烫肿!”
在当街的最末一张桌子上,那里离幺吵吵隔着四张桌子,一种子心静气的谈判已近结束。但效果显然很少,因为长条子的团总,忽然板着脸站起来了。
他仰着脸把颈子一扭,大叫道:
“你倒说条鸟啊!”
但他随又坐了下去,手指很响地击着桌面。
“老弟!”他一直望着主任,“我不会害你的!一个人眼光要远大点,目前的事是谁也料不到的。”
“我知道呀!你都会害我么?”
“那你就该听大家劝呀?”
“查出来要这样呀,我的老先人?”
他苦滞地叫着,用手在后颈一比:他怕杀头。
这确也可虑,因为严惩兵役舞弊的明令,已经来过三四次了。这就算不上数,我们这里隔上峰还远,但县长于我们的情形却全然不相同了:他简直就在你的鼻子下面。并且既已捉去,要额外买人替换是更难了。
加之前一任县长正为壮丁问题撤职的,而新县长一上任便宣称他要扫除兵役上的种种积弊。谁知道也如一般新县长一样,说过了事,或者他更认真干一下?他的脾气又是怎么样的呢?
此外,他还有不能冒这危险的理由。他已经四十岁了,但他还没有取得父亲的资格。他的两个太太都不中用,虽然一般人把这责任归在他的先天不足上面,好像就是再活下去,他也将永远无济于事。
但不管如何,便从他那畏惧的性格着想,他也是决不冒险的了。所以停停,他又解嘲地继续道:
“我的老先人!这个险我是不敢冒的。你说认真是我密告他的我都想得过……”
他佯笑着,而且装得很安静的神情。同幺吵吵一样,他也看出了事情的诸般困难的;而他应该否认那密告的责任。但他没料到,他是把新老爷激恼了。
那个人并不让他说完便很生气地截住他道:
“你才会装呢!可惜是大老爷亲自听兵役科说的!”
“方大主任,”吵吵也直接插入了,“是人鸡巴搞出来的你就撑住吧!我告诉你:赖是赖不脱的!”
“嘴巴不要伤人啊!”
主任认真起来了;但对方的嗓子也更提高了:
“是的,老子说了,是人搞出来的你撑住!”
“好嘛,你多凶啊。”
“老子就是这样!”
“对对对,你是老子!哈哈……”
联保主任干笑着,一壁退回自己原先的座位上去。他觉得他在全市镇的人家面前受了辱,他决心要同他的敌人斗了。
他的同伴依旧担心着他。那牛肉说:
“你愈让他就愈来了,是吧!”
“不行不行,事情不同了。”监爷叹着气。
许多人都感到事情已经闹僵了局,接着而来的一定是谩骂,是散场了。因为情形很明显,争吵的双方都是不会动拳头的,有的人是在准备回家吃午饭了。
但茶客们却谁也不能动身,这会很失体统,得罪人的。并且新老爷已经请了吵吵过去,在互相商量着,希望能有一个顾全体面的办法,虽然一个二十岁的青年人的生命不会恰恰就和体面相等。
然而由于一种不得已的苦衷,幺吵吵终于让步了;他带着决然忍受一切的神情,说道:
“好好,就照你哥子说的做吧!”
“那么方主任,”于是团总站起来宣布了,“这一下就看你怎样:一切用费幺老爷出,人由你找。事情由你进城办;办不通还有他们大老爷,——”
“就请邢大老爷不更方便些么!”主任插入说。
“是呀!也请他们大老爷,不过你负责就是了。”
“我负不了这个责。”
“什么呀?”
“你想,我怎么能负责呢?”
“好!”
新老爷简紧地说,闷着脸坐下去了。他显然是被对方弄得不快意了;但沉默一会,他便耐着性子问道:
“你是怕用的钱会推在你身上么?”
“笑话!我怕什么,又不是我的事。”
“那是什么人的事呢?”
“我晓得的呀!”
主任说这些话的时候一直带着一种做作的安闲态度,而且嘲弄似的笑着;好像他什么都不懂,因此什么也不觉可怕,但他没有料到吵吵冲过来了。而且那个气得胡子发抖的汉子一把扭牢了他。
他扭住他的领口朝街面上拖,嚷叫道:
“我晓得你是个软硬人,我晓得你是个软硬人!”
“有话好好说啊!”人们劝解着;“都是熟人熟事的!”
但一面劝解,一面偷溜开的人也就不少。堂倌已经在忙着收茶碗了。监爷在四处向人求援。
“这太不成了,”他摇着头说,“大家把他们分开吧!”
“我管不了!”视学微笑着说,“看血喷在我身上。”
牛肉在包裹着戒烟丸药,一面咭咕道:
“这样就好!那个没有生得有手么!好得很!”
但当他收拾停当的时候,他的朋友已经吃了亏了。他淌着鼻血,左眼睛已经青肿。他已经被团总解救出来;他一只手摸着眼睛,嚷叫道:
“他姓邢的是对的,你打得好……”
“你嘴硬吧!”吵吵则在唾着牙血,喘着气,“你嘴硬吧!”
黄牛肉建议主任应该即到医生那里去,但他被拒绝了,反而要他赶快去租滑竿。他觉得还是保持原样的好,因为他就要进城向县署控告了。
他的眷属,尤其是他的母亲,那个以悭吝出名的小老太婆,一看过主任的成绩便连连叫道:
“咦,兴这样打么!这样的眼睛不认人么!”
那幺太太也在丈夫耳朵边咕咕哝哝着:
“眼睛都肿来像毛桃子了!”
“不要管!”吵吵吐着牙血,一面说,“打死了还有我偿命!”
别的来看热闹的妇女也不少,整个市镇几乎全给翻了转来。吵架和打架本身就值得看,一对有面子的人的动手动脚,自然也就更可观了。
但正当人心沸腾的时候,一个左腿微跛,满脸胡须的矮汉子忽然挤将进来。这正是蒋米贩子。因为人呆滞尴尬,他又叫蒋门神。前天进城吵吵就托过他捎信的。所以他立刻为大家所注意了。首先拖住他的是幺太太。
这是个顶着假发的胖妇人,爱做作,爱谈话,诨名九娘子。她担心地,颤声颤气地问道:
“怎么样了……你坐下来说吧!”
“怎么样,”跛子冷淡地说。“人已经出来了。”
“当真的呀!”许多人吃惊了。
“那还是假话么!我走的时候还在十字口牌桌子上呢。昨天夜里点名,报数报错了,队长说他不够资格打国仗就开革了;打了一百军棍。”
“一百军棍?”又是许多声音。
“不是面子大,你就是挨一百也出来不了呢。起初都讲新县长厉害,其实很好说话。前天大老爷请客,一个人早就到了;戴他妈副黑眼镜子……”
正说着,他忽然注意到了幺吵吵和联保主任。纵然是一个那么迟钝的人,他们的形状,也不免略略叫他吃惊起来了。
“你们是怎么搞的?”他问着,“你牙齿痛吗?你的眼睛怎么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