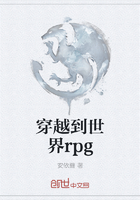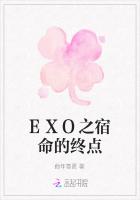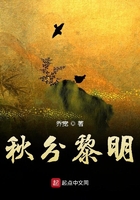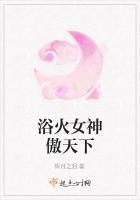栽桩架板的干栏式建筑已远离“居巢”的阶段,它以后改进为栽柱打桩式的地面建筑,先挖柱洞,放入木垫板,再放进柱子。人住到地面来,而且是名副其实的地木板,比起干栏式的居室当然是稳固多了。再进一步,柱洞放入红烧土块、黏土和碎陶片,层层填实加固,形成像倒置的钢盔,当作柱基,立柱构屋。后面两阶段的发展在第二期发掘时都出现过。据报告,栽柱打桩式的地面建筑构件大部分露头于第三层上部,也有在第二层的。碳素和树轮校正年代,第四文化层约在公元前5000年至4000年之间,第三、二层依次推晚五百年,而今第三层末期发现地面建筑,可见,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河姆渡的先民已能克服潮湿,住到地面来。
干栏式建筑遗存除河姆渡外,长江以南地区并不罕见,如浙江吴与钱山洋、江苏凡阳香草河、吴江梅堰、湖北圻春毛家嘴、云南剑川海门口和浙江嘉兴马家滨(存疑)都有考古报告,广东、广西、湖南、贵州和四川等省都曾发现干栏式陶屋;而云南晋宁石寨山的青铜建筑模型,经考证是干栏式建筑。遗址多属新石器时代,也有晚到西周的,陶屋、铜模则晚到两汉。这些资料足以说明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广阔地区普遍采用干栏式建筑,当系适应多雨潮湿、瘴疠蛇虫而发展出来的土著文化。历代文献不乏记载。晚近西南少数民族中这种建筑依然未消灭。
河姆渡的干栏式房子从居住面至柱顶超过2公尺半,除去屋盖的倾斜度,可用空间当有2公尺左右,正常高度的人居处其间是不必卑躬屈膝的。屋前走廊可供休息,夏日不惧炎暑闷热,村外有湖泊,清风徐来,水波不兴,偃卧窗下,就是陶渊明所歆羡神游的义皇上人的世界。半坡早期房子自穴底至顶点约3公尺,“考工记”曰:“葺屋参分,瓦屋四分。”茅草屋顶坡度为1∶3,室内可以活动的高度也有2公尺左右,同样可以抬头挺胸。半坡居室有坚固的墙壁和屋顶以遮风避雨,有烘烤过的平硬地面不怕潮湿,熊熊的火塘用来炊煮、取暖和照明,芦席和草垫当作卧铺。虽不见得安适,足以安心地度过雨雪霏霏的隆冬,在6000多年前也是差强人意的。
无论半坡或河姆渡,村落中住家排列都相当密集。半坡的分布似有一定的规律,例如西部和南部多圆形房子,北部多方形房子,分别聚集,较少交叠,也许是不同家庭的住室。河姆渡住家格局不清楚,但如上述至少160平方公尺(23×7)的木构建筑应有隔间的。清人夏瑚《怒俅边隘详情》记载云南贡山犯龙族的居室说:
离地三五尺不等,上覆茅草,聚众而居,中隔多间,每间即一家,每房有多至十余间、二十余间者。
根据民族调查,这种干栏式房子亦作长方形,面积约160平方公尺,屋内两边分别用竹席隔成十多个小间,土语曰“得厄”,是一对夫妻及其子女的居住单位。“得厄”中央设一火塘以取暖煮食,周围铺着树皮或竹板,是睡眠和待客的地方。两排“得厄”中间有一条较宽的走廊,两端各开一门,准备木梯以供上下。同住在一栋干栏式建筑即是同氏族的成员。河姆渡早期的房子可能也居住同氏族的不同家庭,唯其详情无法细论。
河姆渡两次发掘虽都发现居住遗迹,仍然不能勾勒出当时聚落的面貌,六七千年前此地同时存在多少人,无法估计;但半坡是可以得出近似值的。半坡聚落居住区的总面积复原起来有3万平方公尺,已发掘者只占1/5,这范围内同时有30座房屋,按此密度推算,当时半坡当有房屋二百座以上。每座平均面积20平方公尺,能住2~4人,则当时半坡聚落可有400~800人。约略而言,六千多年前的半坡已经是一个拥有五六百人的大村庄了。他们在村落周围挖掘宽深各五六公尺的壕沟,既备猛兽,也防敌人。河姆渡聚落范围尚未发现,其防卫措施我们也无从推敲,但村落背山面水,天然上就具有防卫作用。
我们现在只能根据有限的资料约略地勾勒半坡与河姆渡聚落的面貌,距离写真尚远,但以这些粗浅的样本来认识新石器时代南北方先民活动起居的情形,尚不失为一个方便法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