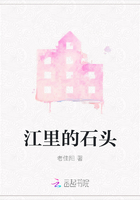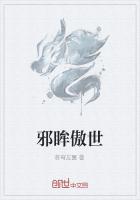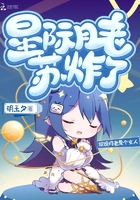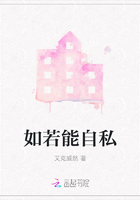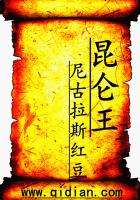上述父老、三老等长老性质的领导者,于其乡里内与乡里民众间有类似血缘的“父老子弟”关系,但其势力仅限于乡里。譬如沛县父老于沛县既轻杀秦所派之沛令,又擅立刘邦为沛公,专断沛县;鲁之父老固可尊项羽为鲁公,为其固守,而陈之三老、豪杰亦能推陈涉为陈王;但逾越了沛、鲁、陈,即无丝毫影响力,这种长老性质的势力,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地方势力。但是经历过秦末“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情况的刘邦,对于这种瞬息间可使政府长吏为阶下囚、俎上肉的地方势力,却是不敢轻忽的,《汉书》“高帝纪”二年有如下的记载:
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
汉高祖刘邦在此条诏令中,正视了能帅众为善的父老势力,并承认他们的地位,准许他们以乡为单位,推选出一人为乡三老,再由乡三老中推举一人为县三老,代表乡里与县令丞尉共议乡里事务。乡三老一职,非高祖所创,秦时各乡已有,并成为一种制度。《汉书》“百官公卿表”即曾有过“秦制,乡置三老”的记载。《史记》“高祖本纪”中说:
新城三老董公遮说汉王,以义帝死故。
董公即新城之乡三老,可知秦时各乡已有三老之置。刘邦此诏的意义不在置三老,而是在调和乡里社会中的中央与地方势力。秦时乡三老,虽深植势力于其乡里,但对支配乡里的县政府,既无参与机会亦无影响力量,若有不满,由于无适当途径宣泄,自然形成积怨,秦末父老率其子弟刑郡县长吏之事,无他,盖苦秦吏久矣。刘邦增置县三老,并准其与县令丞议事,情形类似今日地方上的民选议员,其人虽非地方政府的行政官,但能代表民意,对行政官之行政措施提出意见。使政府与民众能藉三老而得到沟通。三老的酬劳是“复勿繇戍,以十月赐酒肉”。高祖之后,县三老职务更广,如《汉书》“王尊传”中记载,京兆尹王尊因谗被废时,“吏民多称惜之,湖三老公乘与等上书”。此段记事显示了湖县的县三老公乘与联合了其他县三老,代表吏民上书中央,为王尊请命。同传中也有白马县三老朱英上书称述王尊任东郡太守时的治绩。又如《汉书》“武五子传”载,壶关县三老上书武帝直指追捕太子之非,要求武帝“唯陛下宽心慰意,少察所亲,毋患太子之非,及罢甲兵,无令太子久亡”,对中央之行事不客气地反映了意见。此类三老,不在帝国官僚系统之内,虽有职事,并不受禄,但有印章以表示其身份,他们所担当的职事身份与官相似,但并非政府之官,而是乡里民意的代表者,故当时人乃以乡官称之,其性质可谓地方半自治的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