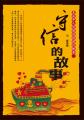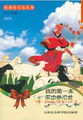社会变革最具体的现象是作为统治手段的国家之出现,族群间的敌对意识愈强,内部的服从意念愈重,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分野也愈明显。承袭大汶口文化的典型龙山文化多有象征身份、权威的文物出土,应是这些现象的反映。山东胶县三里河龙山文化遗址第二期墓葬发现成组的玉器,203号墓殉葬品有鸟形、鸟头形玉器和玉珠等相配成组。第一期的黑陶高柄杯和第二期的薄胎高柄杯多出于墓葬,而为居住遗址所罕见。它们是实用器皿,不是明器,分别代表两个时期陶业的最高水平。因为遗址罕见,可能不是日常家具,而是代表特殊地位,专供特殊用途的器皿。这情形和第一期的石钺一样,多见于墓葬,也许是武器,不像日常用具的锛。日照县两城镇发现的玉锛象征意义更大。玉锛呈长方形,扁平,长18公分,上部较窄稍厚,下部较宽稍薄。墨绿色,近似玉质。背面上半段呈乳白斑痕,下半段几乎全为乳白色,背后尚残留墨绿斑痕,色调光泽。同县安尧王城遗址搜集到的玉斧形制与之相同,呈淡绿色。两城镇的玉锛上端正反两面雕刻兽面纹饰,当是后世铜纹样的祖型。这两件莹润精致的玉斧或玉锛当然是礼器,而非生产工具。它们是权威的象征,“国家”这种机构此时大概快发展成功了。
我们重新来检讨传统史籍,对这趋势的发展也可看出一些端倪。“易”、“辞传”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还以利天下……;服牛乘马,引重致还以利天下……;重门击析,以待暴客……;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
这些发明多在传说的黄帝以前。仰韶文化遗址经常发现石、陶制的纺轮和骨针,那时已从事纺织和缝纫了。裴李岗、磁山和半坡有石磨棒,用来加工壳物,似不比木杵地臼原始。独木舟也该很早就发明的,至于弓箭,人类先经过极其漫长的渔猎时代才开始农业,弓箭之作当更早。河姆渡有水牛,可能是驯养的,仰韶文化只河南高堆、池口寨有牛,与仰韶文化同时的江苏刘林大汶口文化遗址也有牛,至于龙山遗址出的牛骨就更多了;马却罕见,仰韶遗址如高堆,砻山遗址如城子崖数地而已。重门,仰韶文化似未见。郑州大河村发现仰韶文化晚期的房屋,四座毗连,皆独门独户。第一号房子原在东墙开门,后来东侧加盖一间,便将门封堵,改于北墙开门。该号房基中有隔墙分出套间和内间,但仍无重门。反观陕西“客省庄二期”陕西龙山文化遗址所发现的10座房子,双室至少9座,呈“吕”字形。两室中间过道相连,极窄,仅容一人通行,大门开在外室的西南边。考古家推测,由内外两室构成的房屋是“洛省庄二期文化”的普遍房屋形式。重门大概到龙山期才有,和传说的黄帝时代比较接近。
“易经”、“系辞传”作者罗列的这些文明并不是说到黄帝时才有,而是强调这时文物始臻字、图像、衣裳、扉履、杵臼、服牛、乘马、舟楫、簧、生、竽和弓矢等。所谓“作”应是制作,而非发明。这些文物成为文明进展的表征,具有显明的统治意义,“系辞传”或曰“治”,或曰“利”,或曰“济”,或曰“威”,是很有见地的。譬如文字,早在半坡和姜寨的陶器上就有刻画符号,是否文字还有争论。但到大汶口文化晚期,莒县凌阳河和诸城2500年前后。单纯的记号可能极早出现,但作为一种象征,作为广泛人群意识交流的媒介,进而成为统治的手段,则非等到国家雏形萌芽时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