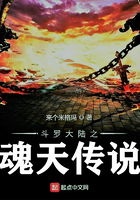“庞澈,从夜袭的角度来看,你觉得骑兵营的训练可还有问题?”赵相如循着墙的最矮处站定,踮起脚看了一会儿,轻声问身边的庞澈。
黑夜中庞澈的眸光闪亮,眼前的女子全神贯注投入在场内的训练情景上,完全没有顾忌到自己此刻自己的动作实在是有失一贯的仪态。许历等人也在偷偷发笑,他敢打包票,以王后的娴熟程度,这样的举动决计不是第一次。
“依属下看来,有可取之处,只是不足之处尚多。”赵相如最欣赏庞澈的一点便是他的纯直。他不如赵奢、许历等人会揣测人心,却也不似他们曲意逢迎,有什么便说什么,“首先便是这马蹄声,只这二百五十人声音便如此之巨,半里之外便可听闻,哪里能算作偷袭?其次,衣衫颜色繁杂,有人夜中着浅衣,数丈外可看清,目标早已暴露。其三,战马不良。王后可仔细看,这类战马都是出自中原,虽也不乏良驹,但真正骑乘种少之又少,大部分马身瘦小,耐力极差,即便短途都算勉强,长途奔袭更是万万指望不上。”
前两条赵相如还能看出来,这第三条非是懂马之人不能看出。赵相如不禁对庞澈刮目相看,她回头看去,庞澈脸上并无一丝骄傲之色,似是知道她的疑惑,又缓缓说道:“属下曾带过楼烦骑兵,他们胯下所乘皆为胡马,胡马与匈奴马皆为一脉,力大且耐力高,远比中原马适合作战。”顿了一顿他又说道:“其实属下曾有幸见过一只西域神驹,头细颈高,四肢修长,皮薄毛细,步伐轻盈,可日行千里,夜行八百,跑动中有汗血渗出,十分难得。”
“汗血宝马?!”赵相如惊出声来。
“是谁!”褒成听见外墙处似有人声,立即驱马上前。一见是王后等人,立刻欣喜异常,翻身下马行礼。
赵相如道:“不是早说过不用行大礼么。”
褒成一口雪白的牙笑得难以抑制:“王后回来,末将欢喜坏了,一时忘了。”
赵相如笑:“以后可不许忘。这么晚了还在训练?”
褒成道:“王后临行前教诲要严加训练,末将不敢忘了分毫,此刻正在教导如何夜间行军,众军士皆已习得马术,进步神速。”
褒成说得正得意,此时小春回来了,给赵相如披上披风,小心系上扣。赵相如拢了拢披风浇了盆凉水道:“只是训练尚有不足。”
褒成听完一愣,然后拱手道:“请王后指点。”
赵相如往场中走去,众人都跟着。“指点谈不上,只是刚刚站了会儿,摸了些门道。”停了会儿又道,“不论是夜中急行还是偷袭,兵家讲求出奇制胜,只是百马奔腾,声音之大可想而知。何况你们虽是私兵,衣着不统一便罢了,怎么还有人着浅色衣裳?!这两点姑且按下不提,你们所配马具,训练方式都是赵国机密,野台虽少人前来,却怎么连个值守之人都无?今日幸得是我在这里察看,若是别有用心之人,岂非将秘密全部窥走?”说到这,赵相如也有些疾言厉色,她缓了缓口气语重心长道:“曾子也说要一日三省吾身,你身为一营主将更要戒骄戒躁,反躬自省。”
褒成顿时锐气全失,双膝下跪认错。赵相如见他并不骄狂,也只是略作训诫,便让他起身。
“许历,明日命人去做一千套黑色胡服,作为狼军军服,每人分得两套。”
“诺。”
“对了,你顺便再取些厚麻布来裹在马蹄上可以静声。”
校场中的士兵还在练习拼杀,并没有因为有人来而丝毫懈怠。赵相如看着很满意,又问了一会情况,便去歇息。
第二日,天色大亮,她甫一起床便命人去请庞澈。
庞澈来得很快,彼时赵相如正在用早膳,看见庞澈一身利落的乌衣短装,以铜簪发,腰挂佩剑,器宇不凡,眼前不由一亮,梨涡浅笑道:“时候尚早,陪我一同用膳吧。”
庞澈看着她青黑的眼眶,知她一夜未睡好,也没说什么,坐在桌前慢慢吃着。赵相如惊讶于他吃饭的模样,十分文雅,不像平日见到的军营官兵,一副狼吞虎咽的样子,时常会因为吃得太急而噎得两眼翻白,倒颇有贵族之风。于是打趣道:“若是只看庞卿用膳的模样,倒真以为是贵族出身。”
赵相如叫的随意,在她看来,既是亲近心腹之人,叫卿也未尝不可。只是庞澈手中微顿,眼皮未抬,也没接话,又默默吃着。
赵相如见惯他沉默的样子,自然不会着恼,兀自说道:“我昨日思虑了一夜,觉得还是如你所言,暂不派狼军前去边城卫戍为善。到底私兵人少,去了也难当大任。与其让他们去填无底洞,不如留待来日。”
庞澈放下筷子,看向王后,“王后思虑周全,应当如此。”
赵相如道:“其实这些不过是幌子,到底是我亲手培养的,舍不得他们。只是我心中不安,国将有难,而我却为一己私利……。”
“既知去了凶多吉少,自然是要保存实力徐徐图之。王后不必自责。”
有了庞澈的安慰,赵相如觉得好受些,想着秦人若真要伐赵动作应该没那么快,于是赵相如放下筷子,拿锦帕拭了拭口:“看来还得求见大王才行。”
“小春,套车,去丛台。”
赵武灵王最喜野台,时常游览在此遥望齐、中山之境,只是他死后,今王更喜丛台,野台便多有荒废,少人问津。
丛台与野台相隔甚远,行到半路竟下起大雨,赵相如乘坐车马的车轮陷入泥沼中,随从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车抬起。大雨和泥浆溅了赵相如一身,让她狼狈不已,心头有股无名之火。待车马行了两日方才抵达丛台,此时她倒也不急了,下车后换了衣物,好好盘问了下人赵王近日的起居,那人见是王后垂询,不敢乱答,一五一十说了。
原来这段日子,赵王沉溺于女色,早已不事朝政,国事基本依赖平原君在打理,即便是平原君有事要觐见,赵王十次有六七次也是推掉不见的,还有几次因为正玩在兴头上,不想被人扫了兴致,特地躲来丛台,整个夏天几乎没在宫中住过。
赵相如一听,见赵王躲来丛台不是专门针对自己的,便放心许多。只是赵王到底是国君,很多事情要由他拿主意,若再一味躲懒,将使政令不通,人心思变。尤其是赵胜,他本身就是王子,平日素有贤名,门客三千之众,又娶了魏国公主,若是心怀不轨,谋夺篡位,也大有可能。即便是赵胜没有异心,一心辅佐,有这样的君主,赵国想振兴也难,自己更谈不上回去。
恨只恨赵王怯懦不中用。赵相如突然萌生了一个念头:要是赵王驾崩就好了。
刚一生出这个念头,赵相如立刻强按下去,毕竟自己在赵国地位虽稳,却还未掌控全局,王位更迭难免会生波澜。
这边赵相如正想着,那边赵王夜幸数女,刚刚才起身,便听侍人来报,说王后来丛台急着要面见他。
赵王心里不愿,但眼见王后都找上门来了,也不得不见。
“不知王后找寡人何事?”赵王有些坐不住,昨晚劳累了一宿,现在止不住的疲乏,看来是该找方技们再炼些丹药了。
赵相如脸上一副焦急的样子:“实在军情紧急,不容臣妾拖延。”
“军情?!”赵王大骇,“寡人怎么未曾听闻?”
“大王莫急,请听臣妾细说。”于是赵相如将她出使中秦国朝臣的反应,以及她的担心说了出来,未免赵王不信,她还说道:“臣妾日夜悬心边城安宁,因而回宫后卜了一卦,只是卦象模棱两可,意味不明,臣妾也只是一介妇人,不知该如何是好,只能赶来报知大王,看是否要调兵防御以备不测。”之所以说卦象不明,是因为她并不知秦军是否会真的攻击赵国,虽然有种种猜测,但她不敢乱说,毕竟卜卦是赵王愿意听信她的重要原因,若是她说卦中显示秦军伐赵,而此次秦军又未如她所料出兵,那么赵王会对她的演卦之术多有怀疑,不再深信。这是她伤不起的,所以在没有确实把握前,她也不能说卦象如何。
“王后只是揣测而已,做不得数。且卦象也未明说,可见此事不会发生。”赵王眼睛浮肿,捻须道。
“可是大王,既然有此可能,防患于未然总是好的。大王只需将兵符交予廉颇,调集五万人马便是足够,无需您太过劳神。”
赵王连忙摆手道:“王后说得轻巧,兵符岂可轻易取出?何况若是秦国并无征伐之意,而我国突然调重病驻防,会引得秦人误解,反而易起战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