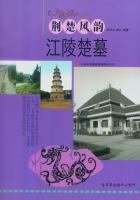老啦。
黄土已经埋到脖子上了。
我经见的死人太多。轮到自己了,却看不见。是让人怕呢,还是让人高兴?能见上亲戚、朋友,能免去阳世里的罪。可那是啥样的地方呢?
贡爷也要死。能了一辈子,突然就成了黄泥巴。
就像一碗凉水,让大日头晒干,剩下个空碗碗。
哎,我真不想讲下去。心上有老多的血往上翻,睁眼闭眼都是血,我可撑不住了呀。但还得讲。要叫血都流出来,流干,我也就安生了。要么就叫血淹死。
就这呀。你嫩娃娃看不着大路的尽头。
喝,喝,别盯着我。我讲。
贡爷咋死的?炸死的。
贡爷收花炮老汉的时候,想不到会给自己身边安上个炸药包。死得真难看呀!浑身的肉沫子飞了一院,满院的白牡丹都染红了。
同时流的是两个人的血。花炮老汉也给炸飞了。
两个人就像两泡烂屎,溅了一院。血差点把大院抬起来。整个贡爷院上空都红通通的,像是在放花炮。
这是虞乡历史是最大的事故儿。
不可想象?是啊,再能是啥,是命啊,人没生下就造就好的命啊!
残忍?不残忍!死不残忍,残忍的是生啊!
小伙子,好好活下去不容易。你们现在坐下来听我胡诌,都能挣上钱,可真是幸福。可我也弄不懂,有的娃儿在福窖里,都会连爹娘扔下不管。一朝一世,理儿都是通的。现在却弄不通了。
你也弄不通?
当然喽,花炮老汉炸死贡爷,真有些荒唐哩。可这却实实在在。
我老汉八十三呀个
没见过小鬼抓判官哎——
那一天冷得冻掉牙齿。可虞乡人心上烧得很,血都流到了脸上。没人去看贡爷的死相,各门各户都关死了。好像贡爷和花炮老汉的血,会穿了街巷流到自家来。
硝烟和血腥在虞乡上空飘了几月。成群的老鸹跟黑云一样,遮得人透不过气来。真像是末日啊。
他们死之前那段日子,花炮老汉可真像个疯狗。一鼓劲地做事,跟个机器样,浑身的汗哗哗哗比柳河的水还大。十冬腊月,雀儿都归窝了,花炮老汉却不停地置办年货,安顿诸事。更重要的是,他在费劲地造炸药。可人都不知道,以为他在造花炮。连贡爷都闻不见一点血腥味儿。他脸上挂着老态,却透着喜气儿。兵荒马乱的,好几年没大办过年事了。今年是悠着劲儿去办,自然脸上风光外露。
贡爷高兴啊。花炮老汉真带劲,啥心都替自个儿操全了。
他也不去拉弓温书。背着手各房里乱窜。一院子的人都说老爷有大起色了。可贡爷真是老了。一笑脸都是歪的,像是酣睡里露出的丑势,让人害怕。他一枚一枚慢腾腾地给下人发赏钱。大家都小心地接了,生怕老爷像棵朽树,一块跟着倒了过来。
可老爷没到死限上。
俗话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老爷六十八,还有几年活头。况且他那儿子无逸还没出人头地。挂记的事儿还多啊,咋能手一摆就走?
那年待客,做祭事,贡爷还是挺上心,样样都过得去。大家看老爷高兴,心上也都安然,都盼正月十五。老爷花的响元不少,自然有大热闹。灯笼糊起了。花炮做成了。元宵也滚好了。
人们都没有预感。没有看见死。
花炮老汉换了净衣,脸上还是那平顺样儿。做事一招一势还是很憨实,看不出会有死神爬在脸上。
十五晚上,也就到了大限了。
红灯笼忽悠悠地转,上面是贡爷画的八仙过海。一院的下人都立在檐下,袖了手等老爷发话。
贡爷坐在圈椅里。他说了老多的话。无非是祥光照地,云布慈岭,可喜可贺,让大伙来年再鼓劲之类的话。咕噜咕噜,跟冒水泉一样。
后来,贡爷就发话点炮。
花炮老汉走到院里。他冲老爷磕了头。花炮老汉说:“老爷高兴,今年也大吉大利,这花炮我亲自点。”他没有叫徒弟石鱼,自个儿搬了木桶粗的三个花炮摆在院当中。
一个,两个。院里像是下着大雨。那可是多少年来贡爷院里放的最好的花炮。
贡爷一脸歪斜地笑着。
火尽花灭。一时黯淡下来。花炮老汉点了第三个花炮。火捻嗤嗤,像蛇吐信子。
花炮老汉走到贡爷跟前。“老爷,我领你一块看个仔细吧。”
花炮老汉一把拽起陷在圈椅里的贡爷,贡爷脸上还挂着歪斜的笑。
“都给我滚远!这是炸药!老子和这老狗一块清算!”
“滚,都给我滚!”
一院的人都吓呆了。有人悄悄挪着腿,可腿却不像是自己的。
就响了,闷闷的,跟个憋了老久的闷屁般。红亮红亮的,也不知是火星子还是血肉,飞得老高,也像是在放花。
天女散花。
是像天女散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