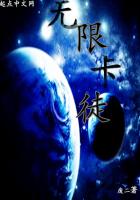取衣服的时间转瞬既到,三日后的下午,栋臣又陪着香儿来到绣衣店,呆儿在后面跟着,他戴了顶帷帽,黑色丝纱罩面,一身灰色土布衣袍,象个小布头儿包着的人。
这时蓉儿正在店里烫衣服,宽大的四方木桌子旁边生起个火炉,烧得火红的炉头上面烧着一块方铁,连着长长的铁柄,包了一层牛皮。
刚刚熨平的衣服叠得整齐,还有一件没有熨完。蓉儿正低着头细心地抚平皱褶,一缕黑丝垂在肩头。
颈中挂着的紫水晶,是生日的时候妈妈特意从美国寄来的生日礼物。因为她的生日是1月30日,是水瓶座。水瓶座内心冰冷,但是待人真诚。不喜欢被拘束,喜欢自由自在。有时候会有点古灵精怪,聪明而富于幻想的星座,所以妈妈才选了一枚花瓶样式的吊坠。
栋臣两人眼见蓉儿正忙,没有出声打扰,先自己四处观看。
呆儿正想着自己的心事,恍惚着跟到店里,猛然抬头见到那垂首忙碌的少女,明艳的阳光下,颈上那紫色花瓶水晶吊坠亮光闪烁,与那日在轿里看到容蓉颈中挂着的紫水晶一个模样,因为水晶的样式是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花瓶,所以记得很清楚。
猛然记起,蓉儿曾给他说过的话:“少帝,以后你就不能再叫本名,我给你起个新名字,以后,你就叫慕梓。”
“那姐姐你呢?”他问。
“姐姐也要改个名字,叫什么好呢?要不,我就叫慕蝶衣,可好?”
可是眼前的少女并不是蓉儿的样子。
少年的心里顿生迷茫。他想问,又不知如何开口,喉咙里好似卡了一块鱼骨,卡的难受。默默地站着,再默默地跟着两人离开。
汴城春夏交融,高大的宫墙内已经万树染绿。宫苑之中,奇花异草,与拖曳长裙的美人一样,各展风姿。
朱温在害死何太后之后,早已没有任何顾忌,霸占了宫中的嫔妃美姬,洋洋然以君主自居。令爱妾昭仪陈氏搬入积善宫,占据了中宫之府地。
这日,朱温在内殿宴饮,盛乘风在侧陪伴。
这座内殿叫做玄德殿,朱温本是个粗人,偏要以虞舜自比,引用“玄德升闻”的成语。看来脸皮厚的也不是一般。
朱温正在饮酒,酒过三杯,醉态已如以前,乡野村夫的粗鄙之态立刻展现无疑。色眼迷离盯着殿中的舞姬,几女中间有一红衣少女,体态柔软,旋起衣裙如跳胡旋舞,一边扭动腰肢,一边向他连抛媚眼,惹得他恨不得立刻揽入怀中。
普宁来到玄德殿,朱温令众舞姬乐师退下。普宁跪拜父王,陈明已选定出行吉日,在三日后既将动身回镇州。
朱温最疼爱这个由张惠夫人所生的爱女。他与张惠夫人做夫妻二十多年,感情很深,也因为夫人贤德,凡事颇有主见,常常能料得先机,是一位奇女子。
他暂忍酒力,好言相劝:“你是父王的爱女,张皇后所生,你母一生积善好德,贤良温顺,你有几分与尔母相俏。父王实是舍不得你到那么远的地方。”
普宁道:“父王,女儿已为人妇,夫君离开老家来到汴城已有经年,现在常常思念家乡,夜时哭泣,家中老父年迈,不得尽孝侍奉左右,实在是有违常伦。女儿也感同亲受,自嫁入王家,也不曾在翁婆身边尽一分孝心,故此才肯请父王恩准,一同回去。这也是遵从先母的教诲。”
朱温又道:“我儿此去,山高路远,一路上要多加小心。为父给你置办了行装,已交待友文办理。临行之时,为父就不去送了,全交由友文代父送你。”
普宁遵命。说还要到后宫看望各位嫔妃娘娘,以示告别之苦。退出大殿。
等普宁离去,朱温嘿然一声:王昭祚常夜中哭泣,是说本王待之不厚吗?本王将爱女嫁了给他,他还不真心归诚。只怕这一去,会生变故。”
盛乘风跟风随音,道:“我王顾虑的极是。王昭祚一旦离了东都,就此却少了钳制,我们就少了对付王镕的筹码。”
“这小子平日装得温顺,谁知道内心是否另有打算?”朱温道。
盛乘风连连摇头,“王镕是个只知道享受的人,本没有什么真谋略,也没有大志向,只不过是守了其父留下的旧业,陛下不必过虑。”。
虽然朱温尚没有正式登殿称王,这些人已不避人,在宫中以王礼敬之,称他陛下。
朱温重新唤来舞姬,越饮越酒乱情迷,老眼昏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