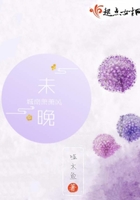亚里士多德说:“求知是人的本性。我们乐于使用我们的感觉就是一种说明;即使并无实用,人们总是爱好感觉,尤重视觉。无论我们将有所作用,或者是无所作为,较之别的感觉,我们都特爱观看。理由是:能使我们认知事物,并明察事物之间的许多差别。”我们可以毫不怀疑地说,正是这种求知欲破坏了人与天然与生俱来的一种和谐的平衡关系。这种求知欲,发展到与理性合作时,便变成一个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力量。这种力量迫使人不断地提出关于宇宙的为什么。人从神秘的自在为他的境界中走出来,便处在一个穷究宇宙为什么的思想以及与之对应的不断的活动之中。这种不断的活动被处于此境界中的自我称之为创造。而当我们重新回归其原始的统一状态时,发现这一切征服自然的创造,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一页。原不过是对自然的机械的模仿而已。人进入这种新的境界,被基督教神学称之为“堕落”。所以,人处在自在为他的境界中时,所关心的仅仅是宇宙是个什么样子,如古东方与古希腊的宇宙观。而当人类从自在为他的境界走出来,按基督教神学的说法即走向“堕落”时,人所关心不仅是宇宙是个什么样,而且更主要的是宇宙为什么是这样。这种力量的驱使,使人的思想从混沌的神秘状态走向清晰的理智状态。这种思想发展到一个高峰是现代自然科学的建立以及与之对应的进步主义哲学的诞生。
科学的目的似乎就是说明世界为什么会这样,并引导人们去认识这个世界。在此之前,人理所当然地将自己与自然割裂开来,以便提供一个绝对的中介——客观,使人主体去认识自然客体。于是哲学史上就有了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的新概念。而科学家们,通过这个客观的桥梁,将自然进行无穷的宰割。科学家相信自然就像一头猪,而自己是屠手,可以凭借客观这把刀子,把猪宰割成无数条块。这种“分割运动”,使人们发现了原子,并以为原子就是不能再分割的“基本建筑材料”。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化,人们发现原子并不是最小的“建筑材料”,还有电子、中子和质子等等更多的更小的粒子。随着量子论的建立,人们终于发现电子是可分又是不可分的。进一步发现,宇宙原来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于是最杰出的物理学理论,成了古老的宗教的“一个例证、一种促进和精细化”。科学家们企图揭示世界的为什么,并且深信对于世界的揭示会越来越清晰。因为他们深信,宇宙是由基本的“建筑材料”组成的。因此,他们可以用分析的手段,用逻辑的武器来寻找这种基本的“建筑材料”。那么,这个世界便最清晰了。然而事实恰恰相反,物理学家对于“基本建筑材料”的探索,使自己进入到一种不可知的神秘的境界中。使世界真相大白的坚定信念其结果是陷入不可知的窘境。量子理论的数学框架几乎不能用语言来解释。亚原子世界迫使科学家不得不放下客观这把屠刀,而恍然大悟:世界原来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物质可以是不连续的粒子,或者是连续的场。”分析的终极是回复到当初的统一。
科学的初衷是提示这个世界的真相。而宗教却全无这种打算。宗教一开始就不是为了使人认识这个世界,而是使人从所认识的现象世界中摆脱出来,回到宇宙的原始统一状态中去。印度教的典籍《奥义书》说:“我的朋友,把最强大的武器《奥义书》作为弓,架上沉思磨尖的长箭,用指向实在本质的思想拉开弦,把永恒作为目标来穿透。”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印度教的宗旨。印度教和佛教都认为:我们所看到的现象世界是虚妄的。只有终极的实在是真实的。在印度教里,这个终极的真实的实在被称为“梵”。“梵”是所有事物的“灵魂”,或内在本质。“它是无限的,超越所有的概念;既不能用理智来理解它,也无法用语言来描述它。”而在佛教中,能深刻地体验到实在的“真如”并能传达这种经验的人被称为“佛”。在道教中,终极的实在被称为“道”。在儒家中,被称为“天”。在基督教中,创立了一个富有人格形象的无所不能的“上帝”。除去基督教“上帝”的人格成分,就与斯宾洛莎的“上帝”完全一致,就与道教的“道”、儒家的“天”不谋而合。在所有这些伟大的宗教中,我们会看到这样一个惊人的相似:所有伟大的宗教,都是艺术地暗示着世界的本质。怪不得冯友兰说:“若所信可以谓之宗教,则其所信即是诗的宗教,亦是合理的宗教。”
世界上的伟大的宗教,对于实在都有着极深刻的体验,然而它们无法用精确的语言表达出来,尤其是东方的这些深刻的宗教经验,常常是超越语言的,它们只重视身体力行的体验。禅宗把这种活动叫做“参禅”。为了表达这种体验到的绝对的知识,各宗教都创造了别具特色的表达系统——与科学的语义符号系统截然相反的系统。宗教用非常模糊且不确定的语态来表达他们对实在的体验。由于对实在体验的深刻性,以致根本无法用逻辑来阐释。科学的逻辑的阐释仅是科学家为了将其观察到的结果告诉别人。而宗教的模糊的不确定的语态,几乎很难理解,而只能参悟。这些不确定的充满了大智大慧的语态构成了宗教的哲学系统。
宗教的哲学常常与宗教的艺术并存。艺术是摹仿自然的,或者更准确地说,艺术是人对实在有所体验而用以描绘体验到的实在的一种语言形式。宗教的艺术主要是神话。印度教就创造了大量的神来传递他们体验到的关于实在的绝对知识。基督教创造了上帝耶和华,艺术地表达了基督教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它用夏娃和亚当的无忧无虑的生活来表达人的自在为他的状态。用亚当偷吃了禁果来表达人的“堕落”——即人从原始的统一状态走向其反面。人必须走向其反面。只有走向反面人才能反观其自我。于是亚当偷吃了禁果后蓦然发现自己的裸体,并产生羞耻心。基督教神学认为,正是人的堕落,上帝才罚男人必须不断地劳动受苦,罚女人必须为生儿育女而劳苦奔波。以此来说明人一旦离开自在为他的“我”,即处于一个走向其反面的痛苦的“我”中。此痛苦的“我”必须不断地创造。此痛苦的“我”在其原始的“我”的反面,才能看清原始的“我”,才能自觉。只有在自觉之后,才能回归其原始的“我”中。回归原始的统一之中,并不是当初的自在为他的“我”,而是自觉了的自在自为的“我”。因此,基督教又以其对上帝的忏悔来描绘“我”的回归。宗教的神话并非如科学所讥之为荒诞的东西。宗教的神话,如同科学的语义模型一样,都是描绘关于实在的知识。从其最终的意义上来说,是方法论的差异。现代物理学对于世界的终极揭示与古东方的宗教体验归于同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科学的方法论是逻辑的分析的理性的揭示。而宗教的方法论是神秘的艺术的模糊的启示。科学是客观的分析,而宗教是主观的体验。由于其方法论的不同决定了它们使用的语言也根本不同。科学的语言是精确的逻辑的推理的直接的数学框架式语义解释。而宗教的语言却是模糊的形象的感应的领悟的直觉的。科学必须借助语言来描述,而宗教常常是超越语言的。科学的思维是形而下的,而宗教的思维是形而上的。科学的语义结构是确定的,因而也是封闭的单一的僵死的。宗教的语言是非确定的,因而是放射性的多义的灵活的。归根到底,科学在于揭示,而宗教在于启示。科学的方法使人和自然分离,而宗教的方法使人和宇宙同一。科学所依赖的是理性的力量,宗教所依赖的是感觉的力量。
靠古希腊哲学的营养长大,同时又生活在基督教时代的圣奥古斯丁,从他的《忏悔录》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位伟大的哲人是如何一步一步地从新柏拉图主义走向基督教神学的。他认为,在耶稣基督降生以前的所有哲学,都有一个根本错误的倾向,就是把理性的力量捧为人的最高力量。同时他又指出,当人被一种“特殊神明的启示开导”之后,就会发现:“理性本身是世界上最成问题的、最含混不清的东西之一。理性不可能向我们指示出通往澄明、真理和智慧的道路。因为它本身的意义就是含混不清的。而关于它的来源则笼罩着一层神秘——这种神秘只有靠基督教的启示才能解清”。《忏悔录》向我们昭示了对两种方法论的深刻体验。
大几何学家巴斯噶在向人类捧出他的杰作“几何学精神”的同时,又向人类捧出了相反的神秘的“微妙的精神”。正是这位最伟大最深刻的几何学家之一变成了中世纪哲学人类学的殿军。他的几何学精神有着“原理的明晰性”和“演绎的必然性”的卓越优点,然而对于有着微妙性和无限多样性的世界却无能为力。正是在这种无能为力的窘境下,巴斯噶捧出了“微妙的精神”。正是这位具有高度的理性思想的几何学家,指出了理性思想的弊端:“理性的思想、逻辑及形而上的思想所能把握的仅仅是那些摆脱了矛盾的对象,只是那些具有始终如一的本性和真理性的对象。”请听这位大科学家的呐喊吧:“呵,人,你在干着什么呀!你是在用天生的理性来寻找你的真正本性吗?低能之辈,沉默吧!要懂得,人无限地超越了人。应当从你的主子哪里去听取你一无所知的你的真正身份!听从上帝吧!”
然而,历史上却有宗教和科学的残酷斗争。如今看来,实在没有必要。对立的两极必然走向统一。宇宙的一切都是在矛盾着的对立的两极之中。科学讥讽宗教是迷信,迷信就是愚昧。然而,正如恩斯特卡西尔所说的那样:“一当我们考察到宗教的真正目的,这种责备便变成了最高的褒奖。宗教不可能是清晰的和理性的。它所叙述的乃是一个晦涩而忧伤的故事:关于原罪和人堕落的故事。它所默示的论据,不可能作任何理性的解释。”宗教毫无揭示宇宙之为什么的打算。它的哲学是晦涩的。宗教的艺术也是那样神秘莫测。如印度教用湿婆的舞蹈来描绘宇宙的运动状态。这样艺术的手段是何等的形象,以致使近代最杰出的物理学家惊叹不已。宗教的仪式看起来似乎很荒唐。然而它的作用是在于引导。如冯友兰所说:“宗教之仪节形式,其可以实现人之幻想,与戏剧同,故亦不必废。”对于这样一个由哲学、艺术和导引仪式组合的庞大的体系,我们不能简单地讥之为愚昧和荒唐。
建立在沉思的基础上的宗教方法,启示我们去体验宇宙的神秘本体,最真实的实在,使我们获得有关于真实实在的绝对知识。而建立在试验基础上的科学方法,揭示了宇宙的终极实在的各个方面。使我们获得有关真实实在的各个方面的相对知识。然而随着科学的发展,最优秀的科学将完全违背它的初衷,放弃征服自然的“客观”中介,而与宇宙神秘本体的走向同一。
1988年
牛顿——笛卡尔的惶惑
——读《熵——一种新的世界观》
我们要改造自然,要做世界的主人!三百多年前,人文运动中一批现代自然科学先驱,为我们树立了这样一个顽固的信念。经过三百多年的奋战,科学技术得到飞速发展,人们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财富。于是,人们似乎已经征服了自然。可是,回过头来一看,人类不但没有如先驱所愿的那样,将无序的混乱世界建设成一个秩序井然的世界,相反,我们生活在一个更大的混乱之中,环境的污染,能源的贫乏,生态环境每况愈下。倘若老先驱们还活着的话,现实不得不使他们感到惶惑。里夫京和霍华德著的《熵:一种新的世界观》向人类敲响了警钟。
于是,我们不得不重新检索一下统治人类意识达三百多年之久的机械论世界观。于是,我们不得不重温一下人类世界观的发展史。
早在古希腊时期,人们并不认为历史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而认为历史是不断衰亡的过程。希腊神话将人类历史分为五个时代: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英雄时代和铁器时代,一个时代比一个时代退化。古希腊人不像现代人一样,以为世界会愈来愈完美。相反,他们相信历史不过是有序到无序的不断循环的过程。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学说里,根本就没有不断发展的观念。他们认为,变化最少的秩序就是最理想的社会秩序。到中世纪,基督教的神学世界观取代了古希腊的循环世界观。然而,基督教神学世界观仍然没有现代人的幸福与完美的观念。他们将历史分为开始阶段、中间阶段与终结阶段,分别表现为创世、赎罪和最终审判。在中世纪生活里,人们并不以为创造财富为幸福,而是在神的驱使下,在社会中尽到他的责任与义务。
直到1750年,巴黎大学的历史教授雅克吐尔古宣读了一个新的世界观,从此改变了世界历史的结构。雅克吐尔古批判了古希腊的循环历史观,也驳斥了基督教神学的历史是不断衰亡的世界观。他断言,历史是直线发展的,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吐尔古的宣言,宣告了现代世界观的开始。
现代第一个实用主义哲学家培根,在他的《新工具论》一书中,打开了现代机械论世界观的大门。他斥责希腊人“像孩子一样荒唐”。古希腊仅把科学用来探索自然之所以然,而培根却试图建立一种用于知其然的科学。他认为科学的目标,应该是“赋予人类以新的发现与力量”。并且断言,这种新的世界观,能“大大开拓人类帝国的疆域,并将无所有能”。随着这种新的世界观的建立,现代自然科学迅猛发展。西方列强运用这种武器所进行的殖民活动,完全应验了培根的话。培根所谓的“科学方法”,第一次将主体和客体割裂开来,并提供了一个所谓发展“客观认识”的中介场所。
随后,笛卡尔又以他独有的天才将机械论世界观推到一个新的阶段。他认为万物都可以归结为数学,并把自然界整个地转化为运动中的简单的物质,把质量完全变成了数世,并声称:“给我空间和运动,我就可以造出宇宙来。”
笛卡尔给人类树立了“征服世界,成为世界的主宰”的信念。紧接着,牛顿以他的伟大的发现,提供了得以完成这一任务的工具,牛顿的三大定律,至今仍是人民征服自然的教条。
这些机械论世界观的大师们,将人主体与自然客体机械地割裂开来,将物质的质从它们的量中横蛮地分离出来。在他们的世界观里,整个世界的模式是一个没有生命的物质组成的冷冰冰的世界。在这种世界观主宰下,历史从基督教时代进入了机器时代。在机器时代里,社会价值首先是精密、速度与准确。人们首先制造了机器,然后是受机器的奴役。整个人们的生活都在机器的专制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