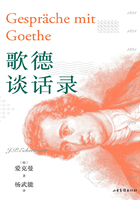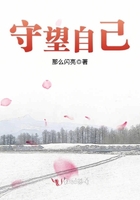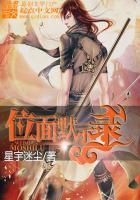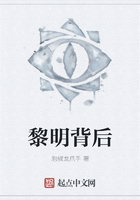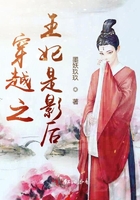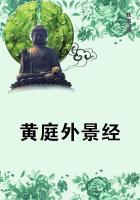耿德旺老汉原来一直是不喜欢和干部打交道的。在他眼里,干部就是每年带着人来家里收这样税、那样费的。为此,耿德旺老汉很有经验,他早早就把谷啊、红苕啊什么的卖一些,凑齐要交的税啊、费啊。干部一上门、一报数字,他就马上掏钱,从不和干部们扯皮。
耿德旺老汉已经活了五十八岁了。五十八岁对于一个农村老汉来说已经是“土埋到颈子了”。他只想一辈子平平安安、不惹事、不出问题就这样过一辈子。在他五十八岁的履历中,一直清清白白,一直遵章守法。耿德旺老汉不像村里的耿二蛋,也不像打工回家的耿三才,耿德旺老汉始终认为像耿二蛋、耿三才他们那样不值得。耿二蛋也是六十好几的人了,火气比谁都大。火气大是因为耿二蛋自认为有资本,养大了四个儿,底气足,常常和村干部顶牛。干部们来收税啊、费啊,就扛着不交。再加上打工回家的耿三才自认为高中毕业,又在外面见了世面,就跟着耿二蛋闹。说五保老人的养老金人均摊不了这么多,又说修村道公路怎么用了那么多钱啊,还说要组织村民代表查账,闹是闹了,结果怎么样?进了乡里的学习班不说,还不是一分不少的交了。还挨了一手铐,值得吗?
耿德旺老汉是最受干部欢迎的。每年干部都把他做榜样:“你们看,耿德旺家里那么穷都交了,你们有什么理由不交,你们比耿德旺还穷吗?我看你们是故意跟政府作对!”一旁的派出所长也吓唬:“谁敢和政府作对,拷了再说!”
的确,耿德旺老汉家里穷。老两口养了一个儿子,三十三岁了仍然没有讨上媳妇。儿子长得膀大腰圆,是种庄稼的好把式。爷儿俩天天在地里刨,一年下来,除了这税、那费的落不下几个钱。最要命的是老太婆有老毛病气喘,做不得却吃得。喂过猪、担挑水什么的就喘得不行,长年累月吃药。家里一年四季就飘着中药味儿。耿德旺老汉和儿子走到哪里都有甘草什么的味道。这样家就拖穷了。
耿德旺老汉就想攒点钱给儿子接个寡妇什么的。一家人在方桌上就召开了家庭会议。耿德旺老汉说:“娃儿,你还没满四十岁,还有搞头,我们搞点钱,把房子修一下,你再买几套新衣服,你接个寡妇什么的肯定没问题。”一说到讨寡妇,儿子两眼放光。老太婆也激动得喘气。接下来就商量怎么搞钱,这是一个难题,很费脑筋的。商量来商量去仍然没有结果。还是讨寡妇心切的儿子说:“春节过后我就出去打工!”
真是急中生智啊!耿德旺老汉也高兴了,儿子在外面去挣票子,自己在家种田饱肚子,这日子啊,离广播、电视里说的小康还远吗?不远了!岂止不远了,简直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啊!就这样定了。耿德旺老汉亲切地盯着儿子,满脸慈祥:“娃,出去吧,家里有我和你妈!”
儿子一过完春节就去广东了。儿子这一去就再没回来,回来的只是一个骨灰盒。儿子在建筑工地打工时从五楼摔了下来,包工头给一万五就了结了三十八岁儿子的一条命。望着骨灰盒和那一万五,老太婆当时就昏了。喘得山呼海啸的。
没有了儿子的耿德旺老汉和老太婆就彻底没有了奋斗的动力和压力。不会再为儿子讨寡妇的钱操心了。
然而,老太婆的病却加重了。医药费也涨了。沉重的负担压得耿德旺老汉腰也弯了,头发胡子也白了。耿德旺老汉变得沉默寡言,一天到晚都弄他的土地。
耿德旺老汉的人生信条是不与官争,不与富斗。与官争就是和政府作对,与富斗就是以卵击石,耿德旺老汉才不干那傻事哩!但是,他仍然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和官打交道,更没想到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
耿德旺老汉有一块好田。这块田一亩左右,挨着公路边,公路外边就是西河。不管是天干水旱基本上都有收成,最好的是,他可以收了稻子再改成土种油菜,一年可以水、旱作物各种一季。因此,耿德旺老汉特别喜欢这块田。两老口的口粮靠这块田,老太婆的药罐也指望着这块田。耿德旺老汉比侍候老太婆还侍候得好。
正是七月,耿德旺老汉望着即将收割的稻子,心里充满了喜悦,今年雨水好,稻子长得好,估计可收水稻三千斤。收稻子后,再种油菜,估计也还能产过千斤左右。耿德旺老汉就这样肩扛锄头在田埂上走着。其实,这月份是不大用得了锄头的,只是几十年习惯了,走哪里锄头都不离身,看见哪里路不平了挖几锄土填一填。看见田里、土里有杂草了,用锄头挖掉。总之,一握着锄头,心里就踏实了。
在田里转了一圈,耿德旺老汉就坐在西河边歇气。他掏出旱烟卷了一支,悠闲地吸着。正在这时,他看见了村主任。村主任在前面走,边走边向后面跟着的人指指点点。耿德旺老汉想,还没到收税、收费的时间啊,干部们走来干什么呢?边这样想的时候,一个人就走到了耿德旺老汉的面前。
跟着后面一个戴眼镜的率先和耿德旺老汉打招呼:“老乡,忙吗?”
村主任马上介绍说:“老耿,这是我们的镇党委刘书记!”
耿德旺老汉就站了起来,两手在裤腿上上下搓,不知该怎么办了。
刘书记很是和蔼,拉着耿德旺老汉坐在地上就拉起了家常。
刘书记问:“老乡,这块田是你的吗?”
耿德旺老汉赶快回答:“是的!”
刘书记再问:“一年能产多少粮食?家里收入怎样?”
耿德旺老汉就一一的作了回答。刘书记边听边点头。耿德旺老汉就说了:“粮食基本够吃了,就是没有钱花!”村主任补充说:“老耿家有个药罐罐!”
这样一说,刘书记就陷入了沉思,半响才说:“光种粮不行,不能致富!”于是大家就低着头想致富门路。尤其是村主任,把头都埋进了裆里,一副愁眉不展的痛苦样子。
刘书记就站了起来,左右环顾了一下,就一拍大腿说:“可以调整产业结构啊!”都望刘书记。
刘书记就说:“你看,老乡这块田地理位置多好,不缺水。这样好不好?”他边问边看耿德旺老汉和村主任,“把这块田修整一下,全部种藕!”
随行的都说:“这主意好!”
耿德旺老汉一听急了:“没有粮食,我吃什么?未必天天吃藕啊!”
大家都笑了。
随行的另一个文书模样的就掏出了计算机,帮助耿德旺老汉算账:“你这块田产稻子三千斤,每斤八角,可收入三八二千四百元。种油菜收入一千斤,一块五一斤,收一千五百元。二千四加一千五等于三千九百元。”
都点头,文书算得对,算得准。
文书又说:“毛收入三千九百元。还没除去种子和化肥以及人工。这样一除,纯收入最多一千左右!”
又点头。是啊,种田没搞头。
文书再算:“如果种藕,这块田起码可以产五千斤,一斤二元,二五就是一万!”
天哪!一算,耿德旺老汉就是万元户了。耿德旺老汉被这突然到来的一万吓了一大跳, 这不是抢钱吗?耿德旺老汉脸红心跳地盯着文书。
文书又说:“除去田的修整,种子肥料啥的,一年至少可以赚六千元!”
大家都同意这一算法。
接下来,就是帮助耿德旺老汉出谋划策了:田要深挖。周围要用石板隔离,一来防漏水,二来防藕窜出田。
商量到这里,刘书记就算大功告成了,他一拍耿德旺老汉的肩膀:“收了稻子就这么干,有什么问题找我!”
村主任也马上表态,就这么干,村里支持!
耿德旺老汉头晕晕糊糊的回家了。回到家就开始向药罐罐宣传致富经。听得老太婆的哮喘又犯了。
耿德旺老汉最后总结道:“听政府的,没有错。”
说干就干。
收了稻子后,耿德旺老汉就开始请人了。把田深挖了一遍。打来青石板,把田周围围个水泄不通,还用了水泥填缝。这期间,刘书记来了一趟,看见耿德旺老汉田里热火朝天的景象,很是高兴。拉着耿德旺老汉的手说:“藕种你不要管,我让农技站的同志去帮你买了,你只管把田整好!”耿德旺老汉就激动了,一连声地说:“感谢政府!感谢政府!”
下了藕种,耿德旺老汉就睡不踏实了。整田加上藕种共用去了八千元啊!他心里痛,那是儿子卖命的钱,连老太婆吃药都舍不得花,这一下就整进去了八千。耿德旺老汉心里堵堵的。他告诫自己:“听政府的没有错!”
耿德旺老汉就咬牙坚持。这期间刘书记和村主任也经常来。刘书记很关心耿德旺老汉的藕田,当他看见新长出的荷叶上有黄色和黑色的斑点后,就马上喊农技人员来解决。
收获的季节到了。
刘书记请来了县上的领导参观。县里领导一行来了三十多人,一来也被壮观的场面震撼了。这块藕田鹤立鸡群,显得是那样的突出和不凡。
县领导马上表态:“全县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现场会就在这里开!”
刘书记马上表态说:“好,我们准备。”
刘书记和村主任就围绕怎么开这个现场会开始忙了起来。
三天后,来了二百多人到耿德旺老汉的田里,县里四大班子领导,各乡镇党政一把手全部到齐。公路边停了一溜乌黑发亮的小车,村里是前所未有的热闹。耿德旺老汉很是风光。
一个人手持喇叭开始介绍:“我县产业结构现场会开始。……”
接下来,喇叭递给了乡文书,乡文书就给大家介绍,这块田如果种田大概收入多少,现在改种藕预计可以收入多少,等等。县电视台摄像在忙前忙后的拍摄,时而摄领导,时而摄藕田。
接下来,村主任就喊耿德旺老汉下田挖第一根藕。
耿德旺老汉就下田,摄像记者立马跟上。
耿德旺老汉在田里抠啊抠的,都把眼光聚在他的手上,抠了很久,才双手抬出一节藕。这藕太大太长了,足有人胳脖粗,用水一冲,白白的放着光。全场立时响起热烈的掌声。
村主任马上指挥安排好的帮工下田采藕。立时,田里一派繁忙,采藕的,传藕的笑声一片。县委书记拿着喇叭讲话了,他丢开了秘书事先准备好的讲稿,即席讲了起来:“同志们,啊,知道我现在最想干什么吗?”
没人回答,也无须人回答。各乡镇一把手都掏出一个小本本记着什么。
“我现在啊,最想吃一口这白生生的藕啊!”县委书记继续说,“我们乡镇干部老叫唤没有让农民致富的门路,真没有吗?关键是我们的干部思路没打开,思想没解放。我们思想着不是搞了这么一块试验田吗?大家为什么不借鉴学习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