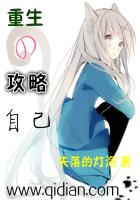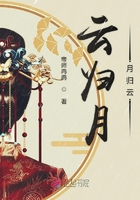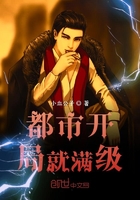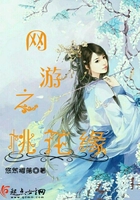我突然就想拉二胡了。
那时候,我是一个意气风发的青年,一个充满无限憧景的幻想主义者,我不知道我除了自己可以教书外,还有什么潜力,特别是艺术方面的潜力,没有一点目标,也没有想当什么作家、美术家、音乐家的想法,由着性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年轻真好!
这之前,我在吹口琴。读师范毕业的那一年,我买了一把口琴,花了七元五角钱。我爸妈给我的零花钱很有限。班上城里的几个学生下课后,就在体育场周围的草地上坐着吹口琴,先是吹得嗡嗡的响,后来,就吹成曲了,什么《敖包相会》《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垄上行》啊,听着特别舒服,我就偷偷的去买了一把。到了手才知道,二指宽的口琴,双排眼,看似简单,其实,无从下口。
在学校里,我不敢和他们一样在大操场吹,我就跑在学校外面一座山上去吹。把口琴藏在口袋里,像做贼一样溜出校门,装着若无其事的散步,然后,来到山上,找个没人的地方,把口琴拿出来,放在手里把玩一番,两手在裤子上使劲擦了擦,平端着口琴,鼓足气,使劲一吹,口琴就响了。我就这样卖力地吹了十分钟,吹得口干舌燥,还是不成调。我就拿着口琴使劲甩,把口琴里面的口水擦干,又用衣服把口琴反复的揩擦,放进口袋,回学校去。后来,我实习,再后来,我就分配到了响水公社石涧大队小学教书。那把口琴,在师范校只吹了三次。
石涧大队小学在华蓥山脚。三个班,四个教师,学生都是山里的孩子,每天走很远的路来学校,上课的时候,学校还算热闹,可是下午一放学,学校就寂寞得如空无一人般,有两个老师就是石涧大队的,放学就回家了,就剩下我和一个代课老师,代课老师又和大队会计的女儿在耍朋友,放学就去大队会计家干农活了。剩下我一个人在学校不知道怎么过这漫漫长夜。我就翻出了那把口琴,一个人坐在教室里吹起来,对口琴知识我仍然一点不懂,凭着感觉在那里摸索,吹口渴了,我喝一杯水,又接着来。
说实话,我感觉最简单的乐器伴奏除了吹口哨,就是吹口琴了,我在口琴上找感觉,把自己能唱的歌就在口琴上试,不出一周,我就能吹出歌来了,我也只识一点简谱,要吹出曲调来,凭感觉就完全可以了。上音乐课的时候,我说:“同学们,我们现在来唱《学习雷锋好榜样》!”我让大家先听我独奏。全班同学都看着我,这些山里孩子,从来没见过什么乐器,见我掏出一把口琴,都静静地盯着看,我就先奏了一遍《学习雷锋好榜样》。全班寂静无声,这在大队小学用乐器伴奏,还是第一次,同学们带着虔诚的心看着我,看我怎么和他们合作演奏。
我说:“我左手向下一打,你们就开始唱,明白了吗?”
都说:“明白了!”
我就右手拿口琴,对好嘴。大手向下一打。
同学们大声唱了起来:“学习雷锋好榜样!”
我猛然停止了吹奏,手在空中一挥,同学们都不再唱,看着我。
我发现了问题。他们憋着一口气,看见我左手往下一打,就高声大唱,声音起高了,我的口琴跟不上。我说:“我打下去的时候,你们的声音不要太高,跟着我吹的调子唱,不要唱跑了!”
这次他们明白了,不再那样紧张,我们教室里就飘出了和谐的声音。放学了,其他教室的学生都围在我的教室外面看稀奇。我说:“同学们,我们再唱最后一遍好吗?”都异口同声地回答:“好!”
从此,石涧大队小学的四个班,每次的音乐课就由我用口琴伴奏了。石涧大队的学生就对音乐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口琴吹到这个分上,我对自己的艺术天赋自信了。对着镜子,我用手指着里面的自己:“你小子,真能干!”又拿开镜子,我摇着头回答:“哪里,哪里,要学的还有很多!”
我又开始做作家梦了。我们石涧大队小学周围有几块农田,每当夏天,夜深人静的时候,各种鸟啊、虫啊就开始鸣叫,我就坐在操场坝里,望着天上的圆月,听着蛙鸣,我就突然来了灵感:写诗!
先在心里反复吟唱后,我就马上跑回寝室摊开作业本,认真地写了起来:
夏 夜
远处的山啊,漆嘛黑
近处的蛙啊,叫不歇
我问山你为什么这么黑
我问蛙为什么叫不歇
山说,天黑我就黑
蛙说,不叫过不得
这是我创作的处女作,一首自鸣得意的诗歌。我用正楷字体抄了几份,分别寄给了《诗刊》《星星诗刊》以及我们的县报。我盼啊盼,几个月了还没有发表,也没收到编辑部的回信,我就怀疑,自己可能不是当作家的料了。
这期间,电视里正在播放《霍元甲》。我们学校没有电视,每天晚上,大队长家里就坐满了人。全大队只有大队长家有一台黑白的电视。我吃了晚饭后,就去大队长家看电视,大队长每天晚上都给我留了一个好位置,让我和他坐在正中,这电视连续剧确实好看,里面的打斗场面,简直太神了。里面的人飞来飞去的,还会钻土,打得尘土飞扬,看得惊心动魄。不但打得热闹,音乐也特别美。
我就不再只看画面了,而是用心欣赏音乐。我在仔细听,是否有口琴的声音,可惜没有,最多的是二胡的声音。听得人柔肠寸断,把我的心突然猛击了一下。我没有想到,二胡的魅力这么大。
回到学校后,我就下了决心,一心来学习拉二胡。
可是,要找到一把二胡却很不容易。大山脚下,读了中学的人很少,爱好音乐的人更少,要找到一种乐器真如大海捞针。公社就那么两条街,是没有二胡卖的,只有县城才有二胡卖。我实在控制不住的想拉二胡,于是,我就死马当成活马医,发动学生。
上课的时候,我就问:“同学们,《霍元甲》好不好看?”学生异口同声地说:“好看!”一谈到《霍元甲》每个学生都激情澎湃,课间的时候,男学生都学着霍元甲、陈真等英雄人物,在操场追来追去的练习武打。
我继续说:“你们只看见武打的精彩场面,而忽视了音乐。你们想想,那音乐是用什么奏出来的?”
都沉默了。很久,才有一个女学生站了起来,怯怯地回答:“老师,是不是口琴?”
我说:“不是,是二胡。”
全班哄堂大笑。
女学生叫蔡小芬,一个平时少言寡语,学习成绩很好的一个学生,她被大家这样一笑,脸马上就红了。
我叫大家不要笑。于是,我就讲了什么是二胡:“二胡由琴筒、琴皮、琴杆、琴头、琴轴、千斤、琴马、弓子和琴弦等部分组成,另外还有松香等附属物。”
怕学生听不懂,我就在黑板上画一把二胡,指着告诉他们,哪里是哪里,叫什么,学生们全都哑然了。没想到蔡小芬又站了起来:“老师,我知道二胡,我们家就有!”
都望她。她的脸更红了:“我二爸在县里读书买回来的!”
我说:“蔡小芬,如果家里有,借来老师给大家拉一拉!”
放学的时候,蔡小芬站在了我的面前,她穿得十分的破旧,衣服上面打满了补丁,脚上是一双大人穿过的烂凉鞋。我曾经作过了解,蔡小芬的妈妈两年前已病故,她爸爸一辈子务农,她二爸在县城读高中,因为大嫂死后,也辍学回家务农了。这一家的生活真够苦的。也可以想象,如果蔡小芬的妈妈不病故,这个家应该还是比较过得去的,试想,农村家里哪个能够买上二胡?
这是一个很乖巧的女孩。我从三年级把她教到了现在的五年级,给我的印象就是沉默寡言,上课很少主动回答问题,也不爱和同学们相处。有时候,来上学还背着一个背篼,有时我问她:“蔡小芬,你怎么上学还背个背篼?”她说:“老师,我放学后,可以边回家边割猪草!”我的心就颤了一下。
我在她头上爱怜地摸了一下:“蔡小芬,给你二爸说说,把二胡借来老师用一下!”
蔡小芬“嗯”了一声,看了我一眼,就回家了。
第二天,她果然把二胡拿来了,二胡是装在背篼里背来的。除了上面的调音把以外,下面用五颜六色的烂布条缠裹着,能够看出来,二胡的主人是很爱惜这把二胡的,对它加以了保护,以免在路上碰伤二胡,尽管如此,还用一根绳子把二胡固定在了背篼里。蔡小芬背着这把二胡,小心翼翼地翻过了一座山,才送到我面前。蔡小芬说:“我二爸说,柳老师,这把二胡他送给你了!”
一放学,我就迫不急待的在寝室拉了起来。窗外围了我班上的很多学生,他们有的伸头向屋内望,有的在窗外蹦跶起来看我怎么拉的,我有种特别神圣的感觉。
一拉,我就发觉要拉好二胡的艰难了。我只在师范学习了一点简谱,对吹口琴,是按着自己熟悉的歌在口琴上找每个音节,然后再移动嘴来掌握快慢速度,凭感觉就可以完全熟能生巧。而二胡就不一样,有两根弦,内、外各一根。我把二胡放到腿上,左手握住,右手就开始拉。
“叽、叽……”二胡发出了令人脊背发麻的声音。
门外却异常的兴奋:“柳老师拉响了!柳老师拉响了!”
我走出门,把学生们赶走,不能再拉下去了,全校学生都围了过来,还有的学生不断往里挤。
我的心突然颤了一下:要是有一架师范学校那样的脚踏风琴该多好啊!我在读师范的时候,上音乐课,学生们都可以用那架脚踏风琴。坐在那里,两脚踏在踏板上,不断地上下踩动,不停地打气,来维持风琴运转。刚来石涧大队小学的时候,我给学生们讲过。他们都很好奇地问了很多天真的问题。比如:“脚踏风琴是用脚踩出的歌吗?”我就同样在黑板上画了一架脚踏风琴,特别介绍了它的构造,并指出它属于键盘乐器。“最好的键盘乐器应该是钢琴!”
下午放学后,我就独自来到操场,端了一条凳子,拉开架式,显然一副二胡大师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