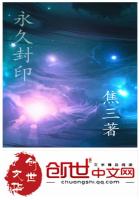夜半。黑漆的空间里,何大伟已注意到东西两边大宅的南面窗口,透着灯光。
他夫妇同孔希文住在十八号宅院B座。前面的A座住着杜泰荣父子和孔希伦。
前天,老爷爷已找过他,郑重地说了孔希伦接任总裁的事。鉴于三个姐妹,他不便开口。但这也是势所必行的了。孔希文的无根浮萍的国籍交易说,老爷爷认为是最没出息的败类。无论如何,唐山是根。有了这根,你爱长些什么奇花异草都可以。树焉能无根,人岂可无宗。
他有点为聪明的孔希文惋惜,历史赐予她的毕竟太残酷了。
他双手交叉在胸前,默默地凝望着稀落的星空。
“你在替希伦操心?”妻子问。她倚着他的肩膀。
“她太重感情,情绪化了点。”他答道。他似乎已预感到风雨一场了。
这是一个风云变幻飘渺奠测的世纪。
今天,何大伟一心撇开了公司的事务,陪妻子过一个自己的假日,他俩的结婚日。结婚几年了,他没好好地陪妻子玩过。贤淑的孔希蒲只是抿着嘴笑。她文静内向,淡泊温和,在三姐妹中最漂亮。在哈佛大学,她选修建筑设计纯粹是兴趣,拿了个硕士学位就算了。她很容易满足,拥有何大伟组成这个小家庭已如愿以偿了。可她的设计思想却出奇的新鲜,标新立异,从不满足。从她居室的印象派的抽象摆设装饰中,可以看出主人的艺术修养。然而,这一切似乎只留给自己的丈夫欣赏。有时,她那与世无争的淡泊,使何大伟感到一种难言的惊羡。一个人竟可以把自己的智慧、才能、学识和美丽,都悄然地藏起来。他不止一次当着面为她的才华褪色感到惋惜。她能说什么呢?有一回,他搂着她戏谑道:“你的生日蛋糕快长霉了。”她莞尔一笑道:“真的吗?我没瞧见呢!”不久,美国的一本建筑杂志刊出了一篇署名何.孔希蒲的文章《建筑的立面欣赏》。文章视角的新颖,观点的奇特,内涵的深邃,使人叹为观止。他捧着文章,端详着美丽的妻子好一会儿,笑道:“我算是认识了我的爱妻。”
平日,她很少有自己的主意,一直顺从丈夫,去哪儿都好。今早,他说坐游艇去大屿山逛。她摇摇头,要去维多利亚公园。难得她有兴致,他当然满口答应了。
公园,只不过闹市中临海的一大块绿茵。绿,显得静,静就显得难能可贵了。香港人很喜欢找个静处,让紧绷兴奋的神经稍微松弛下来。她默默地挽着丈夫的手臂,踏着青草,轻盈信步。晨风迎面拂来,格外清新怡人。走到靠近小径弯处的一张木长椅前,她停下步,望了他一眼,就坐了下来。
她倚着他,闭上双眼,面前仿佛飘荡着一片片记忆的绿叶。他搂着她,紧紧地搂抱一下便又松开了手。他当然清楚,当年,他就在这个地方遇上她的。不过,这几年忙于事业,都没来过。坐下来,往事宛如潮水一样涌上心头,潮起潮落,人去人留,上上下下,又几多欢喜几多忧愁!
“我该感谢你,我们家该感谢你。”她由衷地说,“我们是在这块地方开始呢!”
他忙用手捂住她那圆润的双唇,说:“要说感谢的应该是我。”
内地红海洋涨潮那年,何大伟就读北京清华大学,修化学工程。他家是铁路工人,列红五类。后来听说有一个未见过面的表舅父在香港,才又被打入另册,但不算黑五类。既然不被信任,他便乐得逍遥去了。他早晨参加习武训练,枪击搏斗摔交擒拿都实地实战。他身体矫健、身手不凡,又是足球队员出身,加上无所事事,学得用心,居然也研究起少林武当峨嵋三大派的拳脚棍刀功夫。晚上,偷偷钻进图书馆里,工程建筑历史文学哲学,三教九流,儒道佛……什么乱七八糟的都过目。他同老馆长关系颇好,处处保护这个老头。深交叙谈后,他才明白什么是国宝。才明白这个革文化命的红色风暴愚昧野蛮透顶,实在是个历史大悲剧。他也没想到,这场混乱倒造就成他文武兼备。见他武功不凡,部队教头非常欣赏,让他同去谒见教头的师父少林衡山大师。他同大师,一见如故,便在少林寺住了好几个月。也读了几本佛经,略知轮回之术和禅宗修行。入禅,才真正明白这逍遥派的出世的通透,他也就更逍遥飘逸了。
后来,见他逍遥得出奇,兵团司令部便起疑心,拟对他下手。三十六着走为上着。他有一班兄弟,几个同学分成四个组,每组两人,分头南下广东。他祖籍南粤且一身功夫,便由他当头。在广州住了两周,熟悉地图地形偷渡路线,实习一下山地脚力,尤其是长泳三千米的耐力,非达到标准不可。结果,有两位体质较弱的同学只好回京师去了。
他同陈夕芝一个组。陈夕芝是建筑系的,身材一流,矫健性感,是校泳队主力。她在习武中爱上了何大伟。既然走就同归于逃好了。况且她有位姑姑在香港,也可说是有个立足之点了。
他们的队伍由省城到惠州,至镇隆圩上山,沿着山路日伏夜行,出横岗过梧桐山,就到达边境线了。从山上看去,海对岸朦朦胧胧的高楼群,呈现在眼前。为了避免边防军及军犬的搜捕,他们选择海距较远的盐田下海,这就得凭那三千米长泳的耐力,对南汎潮向的持久占战。
天微微亮,他们正要藏身草丛隐蔽,忽然民兵搜山来了。他们各自逃命,四散隐遁。他俩一直朝山顶上爬去。在一个茅草过人的山窝里藏了下来。这窝儿上面竟是个平台,还有户人家。
入夜,南风轻吹。他俩下山,到了海边便串着鼓涨的红色篮球内胆,踏着星光悄悄地下水去了。与风浪作了长达四个小时的搏斗,他几乎沉了下去,靠着陈夕芝的拖托才勉强瘫在沙滩上。他俩疲惫地伏在沙滩上喘息了好一会儿,待爬起来没走上几步,就被蛇头接去了。
第二天正午,说是陈夕芝姑姑来电话,已交足了两万元赎金要把她接走。临别她给何大伟留下了姑姑家的电话,讲明白一定想办法赎他出去。
可是,已经是第四天,一点动静也没见。他表舅父也没见有个回音。他焦虑了。
蛇头大眼四,见他榨不出油水,养着也不是路,便网开一面,容许他立个借据,欠债两万元,出去后清还。
出来之后,按着电话号码拨,竟是个空号,怎么也找不到陈夕芝。
后来,他终于找到表舅家人。表舅夫妇去了加拿大,还留下一间小制衣厂没人管,就委托他代管,并让他住在厂里。他总算有个归宿,然而陈夕芝在哪里呢?无论如何,他不相信她会丢下他不管的。人海茫茫啊!同行的另外几个同学,音信杳无,恐已葬身鱼腹。想到这里,禁不住毛骨悚然。
他没想到香港地寸土寸金,厂房住屋十分拥挤。晚上他同工厂看更的老头一块儿唾。老头话多,天南地北都谈到了。从老头嘴里,他才知道表舅到加拿大坐“移民监”,等候绿卡去了。
出来捞世界难呀!比在北京读书不知烦多少倍。工厂资金周转不过来,眼见着本月工资又发不出去。工人不满意,有的要离厂,有的怠工,有的哀求先发点钱维持生活。问题还在于倘不能如期交货,工厂真要倒闭。表舅父好像早知如此,几次电话也只是答声想办法。他人地生疏,当然只能同工人一起商量,将就着先把货赶出来才有活路。然而,布料款又早过期未付,即使卖出货,银行也会给扣个干净的。要不给工人付一半工资,也很难将就得过来。
事到如今,唯有听天由命。天黑关上厂门,他口袋里装着三十元钱上街,今晚吃饱一餐,明天要怎么死就怎么去死好了。走上骆克道。
“先生,你留步。”街边看相的站起来拉住他说。
“好,我坐下。”
“你有难,大难困身,焦头烂额,无处藏身,碰上一难又一难。”相士望着他愁云满布的黑脸说。
“今晚饱餐一顿,明晨上吊。”
“痛快。”相士凝视他的印堂好一会儿,“先生,且慢。山谷中透出一股英气,命硬,榕树多叶,竹树多根,大难不死。你会遇上贵人,化灾化难。”
“承你贵愿!”
“三天之内,必遇贵人。”相士说。
“如此肯定?”
“必遇无误。”
“多谢了。”他奉上相金十元。
“先生留着,三天后应验了未迟,请记住陆机相士。过了此难,先生定将大富大贵。不怪陆某言之过早。”
“这很不好意思。”他为难地说。
“我陆某人岂能乘人之难,三分天下而去其一乎?”
“我何某折服相士。”他敬重地行个佛礼。
离开相士,他步履轻快地走进一间酒吧,独自喝了两罐啤 酒,灌了一个全餐。
乘月色。坐在维多利亚公园小径僻静弯处的长木椅上,仰天长望。真神,三分天下其一。他伸手入裤袋里摸摸那三张十元纸币中还剩下的一张,似乎相信了陆相士的天机洩露。
他带着点醉意,身轻如燕。
天黑了,晚风清凉。这小径弯道游人稀落。
面前走过来一对青年男女,香气扑鼻。那男的看上去似美国人,一口美国式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