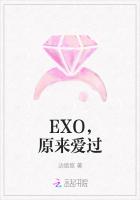六月栖栖,与木荷、卷丹、合欢的芳香作伴,侍香居为夏月暑日的各项宫务,而预置备办着。
红姑姑把一簸箕的金叶女贞,甩到落珠脸上,狠狠啐骂:“你娘生你没生给你眼睛鼻子,看花儿闻香儿看闻成这样儿,狗都比你强百倍!这些鬼物什,留着孝敬你娘在外头给你找的野老爹!”
落珠的秀眸,红肿似新剩的桃种,她咽忍酸泪,咬牙攒拳,屈膝跪向钉板,浅粉色的裙裾,瞬时血红冉冉。
“哼!”红姑姑扭摆蛇腰,转身暗骂:教你这小蹄子能扛,没人儿是铁打的,再能扛也有扛不住的时候,等到那儿时候,看你还顺不顺着本姑奶奶。
训罚完落珠,红姑姑来至脂粉堂,监查宫女们制腌胭脂妆粉。正查试搀兑珍珠粉的手膏,红姑姑突听小宫女进传:“禀告姑姑,内侍监贾总管有事请见。”
红姑姑怒火攻心,急点莲花步,到堂室会谒贾公公。
有心腹在堂室外把风儿,贾公公肆无忌惮,抱住红姑姑心肝宝贝地乱叫,被红姑姑推个趔趄。
“死骟驴!甭以为我不知道,你把外头的相姑扮成宫匠,混进宫抢我侍香居的生意,惹火儿老娘,信不信老娘敢舍脑瓜子,把咱俩做的勾当通通说出去!”
吓得贾公公压紧嗓子“唉哟”一声,待魂儿溜一圈附回,他陪笑哄劝道:“我的心肝儿,你可别做傻子才做的事,我不过给那群图乐子的阉爷儿换换鲜,好让他们与咱两人更亲实,这一来生意岂不做得更红火?”
红姑姑将贾公公递上的一对红白两色翡翠镯,麻利地套于腕上,并拿起床帚猛打他两下,骂道:“少跟姑奶奶我耍这把戏!你肚子里那点儿坏水,我看得门清儿,想占大便宜没那么容易:我可告诉你,咱两个是绑在一条线上的蚂蚱,谁也别想逃掉,你若对我不仁,休怪老娘不义!”
“咱俩是老相好,有我的就有你的,我对谁藏心思也不能对你藏心思。”
贾公公费好大劲儿,才教红姑姑消气。结子解了,贾公公掏出缝藏在内衫的勉子铃,抱拥红姑姑滚进床榻……
草草狎嬉,红姑姑扣合亵衣,话冷气热。“哟,头一次这么快,是不是嫌我老了,不如丫头们水灵。”
“哪里的话,酒越陈越香道,我还有理挑捡你不成?大公主怀着胎,随太妃娘娘进宫为沈驸马求情,皇上碍面只得答应,但心里极不自在,皇后娘娘便提见去绮霞宫看小皇子,二位主上万一问起修工召匠,我岂能不应付?”
红姑姑冷哼一声,拿起枕边的紫铜篦梳捋发鬓。
待穿整衣衫,贾公公系戴束巾,说道:“今晚上那两丫头别过去了,潘公公已传人说退食。”
红姑姑理好银朱撒花薄缎长裙,撇嘴冷笑:“他也有退食的时候,退食也好,我的丫头差点没被他折腾死。”
贾公公涎着脸嘻嘻笑道:“潘公公在皇上眼皮低下伺候,龙床动几回,他也跟随动几回,比敬事房那帮人还难熬,能折腾也是人之常情,只要不短好处,把人折腾死也无妨。”
“敢情不是你的人干这勾当,”红姑姑火儿道,“若真死了人闹出事,你我两个还要不要命?”
贾公公伸伸腰,呼喘口气儿。“我说笑罢了,把心搁肚子里,潘有金混到如今的地步,绝不是蠢类,他肯必会惦量轻重,不弄出大事。”
“你千万拽住这位紫微城里的县官爷,潘有金深得皇上宠信,万一咱俩事露,好用他在皇上面前为咱俩挡掩。”
贾公公对红姑姑的警诫,左耳进右耳出,轻慢地说:“潘有金淌进这浑水,跟咱们坐一条贼船,焉会不帮顾咱们?你犯不着为此忧心,何况这事还没走露出风声。”
红姑姑褶折眉头,心起迷云而唏嘘:“尼姑佛不知恁的讨好皇后娘娘,近段日子老叫尚仪局的人在各处转悠,尤其侍香居这里,盯得比惠班馆、绣房、浣衣局厉害,我估度她是不是晓了什么了?”
贾公公握持拂尘,不将此话放在心上:“素姑姑向来与你不对付,她不过借讨皇后娘娘的好,顺道儿找你麻烦。你别吓得生出差子,露出马脚,让外人捞得讨上的彩头,那样儿的话,咱俩算真完了。”
“你说的有道理,”红姑姑仔细思忖,“但愿我多心罢。”
贾公公从枕套取出一个掌大的香袋,放在鼻下嗅了嗅,不是好笑地道:“你的手艺真绝了,连皇上他老人家用的,都没这个好哩。”
红姑姑咂嘴咬舌,谑笑道:“坐到侍香居尚宫的位子,谁不是明活暗活全会?撇开咱俩的生意不讲,单仗宫里头的娘娘主子,老娘就得好些进益。”
贾公公将禁香用油纸包好,卷按进拂尘的空柄,之后提嘱红姑姑:“依例,只允四位妃子伴驾随往行宫,皇上已旨命琴主子和迎主子,皇后娘娘又谏晴妃娘娘从行,剩的那一额,各宫的主子还不得争破头闹伤脸?帮哪位落哪位,得罪哪位都吃亏,不如哪位主子也不甭帮,随她们争去;再是,皇后娘娘对关乎避暑的诸事严查,你别弄出事端让皇后娘娘知觉,把咱们的事顺出来坏事。”
红姑姑应允说:“你放心,陪圣避暑的活计一个也没接,凝露宫的皊主子怎地寻我事,我都按住不动。我心里有数呢,不会为捡芝麻粒子,反掉扔西瓜。”
贾公公搂她亲道:“我的心肝,你如今知哪条鱼大,哪条鱼小,会舍小取大咧。”
红姑姑抬手,扇贾公公一巴掌,呸道:“完事儿收回心,老娘虽不领钱,可不是那些丫头任你胡为——少装忘性,前遭盘芸的劳金,你还没给老娘。”
“两翡翠镯子还不够,这可是内务府杨公公私扣的好货。”贾公公撩戏红姑姑的腰身胳膊,滑摸至红白两色翡翠镯,被红姑姑拽回镯子躲开。
“一事论一事,别想混搅一块白吃,镯子是你为私办贼活儿,给我赔的不是;劳金是你狎盘芸的欠赊,管你是哪个,老娘的丫头绝不让人白玩儿,今儿个你要不给,休想走出这间屋子!”
“嘘,姑奶奶,你小点声,”贾公公探头伸脖儿,往门口紧瞅,“若叫外面的小子听见,他们必借机索好处,我可不能揩刮自个儿,给那几个兔崽子油水。”
红姑姑看他这乌龟样,白眼冷笑:“堂堂三大管事之一,正四品的总管,小气到犒奖手下都不舍得犒奖,只会拿蜜话儿耍忽人,等着罢,天底下没白吃的饭,也没白用的工,你早晚摔在人心得失上。”
贾公公用一方沉甸甸的金条,打住红姑姑说嘴。“不就是个丫头的身子钱,咱家还能给不起?犯得着你这恶娘咒诅。我爬到内侍监领头儿的位子,吃多少苦头长多少本事,还能叫下面的狗东西绊踩?也忒小看人了。”
红姑姑歪着身子,抱胳膊言道“贾大总管可别跟我动气儿呀,奴婢只是醒一醒你的驴脑子,怕你步了典公公的后尘。”
贾公公走近门口,头不回轻蔑道:“放心,我手下可没易束吾那样儿的狼猴。”
步出堂室,贾公公令小太监们把侍香居新掐的花瓣,按优次扫合进各色纱囊,再装到挡阳的蓬车,预备给上头配用。
贾公公瞧装运妥当,向统管禄贵发话道:“你回去跟甄公公说,给上头配花儿的活让他干,咱家还得到绮霞宫,侍候皇上和皇后娘娘的宝驾。”
禄贵遵令,带一行人拖推蓬车,回往内侍监。
朱舆外,繁花碧水间,旋萦着雀啼蝉鸣,皇上看得心烦意燥,撇撂穿引天山凉玉的杏黄丝帘。
“皇上,还在为沈驸马的事烦心?”
皇上紧握承抚慰藉的素手,对皇后愤懑言道:“如不看在姐姐拖带身子为他说情,朕必将沈致秋千刀万剐!”
昨日早朝,沈致秋上呈一封密笺,称其是行宫督造丁以恒,掌悉南山王谋反的书凭。因南山王与沈致秋皆为国亲,皇上怕皇亲外戚不谐,下朝后方睹阅密笺。谁料想,密笺中除一张半字未有的白纸,再无他物。
“沈致秋身为朝臣帝戚,竟做出‘无字密折’的荒唐事,欺君犯上,渎犯君威,亏他还是饱读圣书的三甲魁首,真乃斯文败类,无耻之徒,皇上不需对这种人动气,气伤龙体事大。”
皇上冷冷苦笑:“动气也无用,谁教沈致秋有母后帮衬,母后已下懿诏,命沈致秋和星异一样,随朕的御驾去往行宫。朕在宫里忍他,到外头依要忍他,求夙,你是不是觉的朕很窝囊无能,连一个姑戚言臣都治服不了?”
皇后殷挚劝说:“皇上万不可这般想,皇上是天下人所倚仰的九五之尊,君临天下理当霁月光风,忍不能忍之忍,沈致秋虽欺君渎威,说到底,不过是个榆木腐儒,出言行事皆是笑话,皇上犯不上折尊与他斗气。何况,太后娘娘费神,教沈致秋随驾避暑,明赐沈致秋荣乐,暗却为皇上出气:沈致秋循礼克身,但成也循礼克身,败也循礼克身,在行宫,他纵有千万谏奏,若未受皇上召见,是不许进内面圣,所以他只能空忧自思,反省悔改,再不敢烦扰皇上。”
皇上听皇后劝罢,解郁滋喜,欣然语道:“求夙劝谏的有理,朕既为君帝,应纳怀百川,凡不触本的隙事,大可忍忍罢。再说,沈致秋一介迂夫,也不值得朕费神对付。”
皇后微弯眉角,轻抿唇边,覆叠滚雪细纱螺纹袖,盈盈求问皇上:“那皇上还生不生太后娘娘的气?”
皇上搂住皇后,开颜说道:“母后为朕劳心,又顾念皇姐怀喜,想出这个绝妙法子,若不教求夙点破,朕还怨忿母后袒护自己的姨侄,不疼朕这个非亲骨肉。如今想来,朕因沈致秋而生母后的怨气,大是不孝,亦是不该。”
皇后偎靠皇上的肩端,静听舆轮行过宫道的滚滚碌碌。
前些日子,上官夫人进宫,说经武仁侯和嘉国公密查,南山王在神龙山确有动作,只是极为隐蔽,难寻逆证,虽难寻逆证,却证实了沈致秋上月所言——南山王意借避暑之机弒君谋反。
相较南山王,皇后更慴惧太后:出于旧日的情意,皇后请皇上准晴妃同往行宫,想与晴妃消解恩怨,反察太后,从对武仁,南山两家结亲的不咸不淡,到闻晓晴妃同往行宫的声色不改,皇后断定,太后亦知南山王谋反,甚知南山王要在神龙山弒君,且不言皇上被太后养育多年,单说晴妃和沈致秋是太后的连血至亲,晴妃更是在太后身边长大,太后竟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