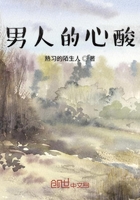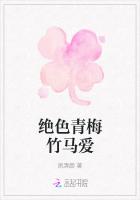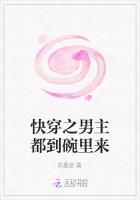一
顾准是伟大的思想家。对于顾准著作的流布情况,有所耳闻目睹。笔者认为,顾准著作的流布,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折射出中国改革开放、人民思想解放的艰辛进程。不忘这段历史,也算是以史为鉴吧。
众所周知,顾准是以研究会计成名的,早在十九岁,他就以一部《银行会计》(商务印书馆出版)得风气之先,从而独步学界。他是一位会计学家,但同时又是一个共产党人。从事会计事业,当时在他不过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和从事革命活动的职业掩护,并不是他的人生目的。他的人生目的是实现革命理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此目标,他不惜放弃优渥的生活和工作条件……
“反右”斗争中,顾准立马中箭。直到1961年11月,他被摘去“右派”分子帽子。在孙冶方的关心下,顾准于1962年5月,再度进入中科院经济研究所任研究员。他在重返经济所的两年多时间,并未将研究的范围局限于会计研究,还做了大量经济研究和翻译工作。他在此期间留下了会计研究方面的不少著述,囿于当时的条件,并未公开出版。
当时,顾准到上海、东北调查研究,写出《会计原理》和《社会主义会计的几个理论问题》两部著作。于此可见他对会计事业在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要性的重视。顾准的《会计原理》是一部残卷。顾准逝世后留下的编写大纲表明:原计划欲写七篇,这只是其中的第一篇。1965年顾准被第二次错误地戴上右派帽子(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三次受到不公正、不应有的错误的打击),接踵而来的是震天撼地史无前例的“文革”,他连工作权利也被剥夺了,自然不可能续其成。1974年12月,顾准在北京病逝,他的弟弟陈敏之在整理他的遗稿时,发现了《会计原理》的手稿和《社会主义会计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打印稿。
对于胞兄的这两部会计学遗著,陈敏之当然要尽力争取早日出版。然而在那个荒诞岁月,陈敏之的努力终归无效,一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主义会计的几个理论问题》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82年5月出版,发行了两万七千册。
然而《会计原理》的出版却充满艰辛,用陈敏之的话说,真是往事不堪回首。事情还得从1976年说起:那年人怨天怒,中国北方大闹地震,孙冶方夫妇到沪暂住在老朋友陈修良寓中,陈敏之闻之晤面。不久,“四人帮”垮台。孙冶方听说顾准有一部《会计原理》还未出版,就热情地相托于姚鼐(孙冶方建国后担任上海财经学院首任院长时,后者为其副手),姚鼐受托后找到洪泽(当时在上海市宣传口工作),洪泽则把顾准的《会计原理》手稿交给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编辑欧阳仲华承办。说起来欧阳仲华与顾准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同为立信校友,只不过顾准早就离开立信,叱咤风云于疆场时,欧阳大概还少不更事。即便他孤陋寡闻,对顾准的名字终有耳食吧?话说欧阳拿到手稿后,精心拜读,一读再读,时间就在他的仔细阅读下无声无息地流淌着,他的“水磨”功夫着实堪称一绝。别人不着急不要紧,作为顾准兄弟的陈敏之摒挡一切,欲向欧阳求教。欧阳其时不知出任何官职,他对求教者打起了“官腔”,意谓顾准的书内容陈旧,词汇与现时不相称云云……所谓“话不投机半句多”,陈敏之当即取回书稿,拂袖而走。
尽管碰壁多多,陈敏之还是于心不甘,在他负责的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所里,有一位同事名叫吴逸,与时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的许毅(他也是立信老校友,与顾准在华东局财政局财委曾共过事。笔者曾采访过他)比较熟悉。一次乘许毅来沪出差的机会,陈敏之就由吴逸引见许毅,拜访是在位于外滩的新城饭店进行的,会见虽然是礼节性的,气氛显然是热烈的,两人相见恨晚。说起顾准的《会计原理》一书,许毅拍着胸脯,打包票地答应,由他带回去联系出版社在京出版。陈敏之当然感激不尽,心想终于遇到了知音。约莫过了年把光景,顾准的《会计原理》确实于1983年由北京一家出版社出版(这是当时唯一隶属于财政部的中央级出版社)。
此书邮寄到陈敏之手中时,他感到一头雾水,很是纳闷,以为拿到了一本“非法出版物”,因为这本小32开的书籍表面看来颇为“舒朗简洁”:既无出版社署名,也无版权页,当然也不会有书号、定价之类的东西。其原因是什么,陈敏之一直也没弄明白,他也不敢妄自揣测,不过他“仍然很感谢一切曾经为出版此书做过努力的朋友”。此书当时只印了一千册,其中两百册由陈敏之分赠亲朋好友,余下的八百册,蒙出版社的美意,通知让他自行出售,书款抵充稿费。陈敏之因当时工作较忙,无暇顾及此事,只好委托他的老朋友、时任上海会计学会秘书长陆修渊(原立信校友)代为办理,售书所得八百元请他悉数汇交中国财经出版社。事后,陈敏之曾几次写信给许毅,打听原委。许毅也有一肚子的苦水,他回答说,经向财政部副部长陈如龙同志请示,顾准的《会计原理》的出版,只能做到这个分上。
后来经过再三努力,《会计原理》编入《新编立信会计丛书》,于1984年由上海的知识出版社(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的前身)正式公开出版,第一版印数达三万一千册。出版社决定的印数如此巨大,当然不会是随意的。其时已届耄耋的潘序伦先生在为此书写的序言中作出了如下肯定的评价:“这篇遗著虽属残卷,仍可独立成篇,编写方法也与众不同,以他一贯的严谨学风,运用马列主义观点,层层剖析,逐步深入,独创一格而不拘泥于习俗。例如:主张利息不应列入成本,应从利润中支出;用数理矩阵方式,来说明复式簿记恒等原理;对借贷记账法和收付记账法问题,提出新的见解……许多有关会计理论和实务问题,均具有其独到的识见。”
这位中国现代会计的泰斗,还满怀深情地说:“我看了顾准同志的这篇遗著,一则以喜,一则以悲,又引起了我对他的怀念和无限惋惜之情。顾准同志在现代会计界中,可称为一个难得的人才。”“但他‘志不在此’,于1940年毅然抛弃优厚的待遇和都市生活,离开上海奔赴解放区,为祖国革命事业作出卓越的贡献……”
1986年《立信会计选辑》第四辑(知识出版社出版)以《读顾准同志遗著〈会计原理〉的启示和体会》为题,辑录了我国部分知名的会计学家对此书的评价。他们认为:“书中许多观点、名词、提法,都具有科学性。如复式记账法是一种纯粹数学方法,方法本身并不包含什么阶级性的因素在内”;“对于会计学的性质、主体、客体(对象)、作用、任务、方法和组织,进行了全面和正确的阐述。尤其书中有不少地方,冲破了当时苏联教材的束缚,密切结合我国的实际,提出了精辟的见解”(管锦康);“这本遗作确有独特创见、独特风格”,“例如会计主体这个词就是一般书籍中所未见过的,用数学中的矩阵来解释复式记账法,也是独创的”(王文彬);“顾准同志也颇重视研究苏联的会计理论和方法,但决不生搬硬套”(梅汝和);“如果我国的一些会计学者或会计工作者,对此(按:指复式记账原理)早有足够理解的话,那么,近二十年来我国会计界有关记账方法的争论,就应迎刃而解了”;“复式记账法是一种数学方法,复式记账法的记账规则就是矩阵规则,不仅解决了长期纠缠不清的问题,也开创了我国以数学方法来解决会计问题(包括理论与实务)的先导”(徐之河、黄履申);“这本著作不仅是一般初学者的良好读物,也是我们专业理论工作者的学习榜样”(李鸿寿)。
二
如果说顾准遗著《会计原理》的出版,历经戏剧性的磨难,那么他的另一部专著《希腊城邦制度》的问世则显得“平淡无奇”了。根据顾准的遗嘱,陈敏之将这份遗稿检出送给他的知己吴敬琏保存,吴敬琏与顾准谊在亦师亦友,顾准将这份文稿托付给吴敬琏是寄予无限的期望。
这份笔记,在顾准生前,陈敏之还没有读过,很想读一遍,乃商得吴敬琏的同意,拿到了文稿,读了一遍。读后深感自己虽然学力不逮,但整理重抄了一份,这样既可供自己今后继续学习西方史时随时翻阅,同时又为后世多保存了一份抄本。陈敏之认为:“希腊史研究,不过是五哥十年研究计划中的一部分,一个开端。他曾对我说到过,打算用十年时间,通盘比较彻底地研究(先是)西方,(然后是)中国的历史,并在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达成他对历史未来的‘探索’。如果天假以余年,可以期望十年之后,会能得到某种成果。可是,谁能意料得到,‘横逆’的袭击,竟来自他自己身上的不治之症的肺癌,使他的这个研究计划还在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夭折了!然而,幸运的是他还给我们留下了这份笔记,虽然连这份笔记也还是一份未完稿。”
陈敏之读了顾准的《希腊城邦制度》以后,无时无刻不在惦记着它的命运,在顾准逝世的第二年(1975年)他就说过这样的话——
这份笔记今后的命运怎样,我无法预测和断定。也许它会像历史上并不鲜见的许多先人和他们的著作一样,湮没在历史的洪流中;也许它可能在某种历史条件下面,居然还能被人所重视。但是,重要的不是他已经开始的这种历史研究是否有人继续下去(我当然衷心期望能有人继续下去),因为,五哥从事这种历史研究,他的本来的目的并不在研究历史。我瞩目于未来……
对这部极富创见的著作,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的吴敬琏,则交给院内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该社的国际问题编辑室收到书稿后,二话没说,立即投入精兵强将抓紧出版。期间编辑依据手稿对照陈敏之的整理稿作了精心校勘,将稿中的旁注、另页,也酌情编入正文或注释中;对稿中大量的外文人名、地名、专用名词和中文引文,竭尽所能进行了校核……1982年,该书顺利问世。出版后,好评如潮,被认为是研究古希腊历史的拓荒性著作。
在此前后,顾准翻译的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和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的《经济学论文集》,分别在1979年与198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不过,前者署名为“绛枫”,这是顾准早年曾用过的一个笔名。
三
顾准一生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当推《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这部著作从整理成书到出版问世,历时十八个春秋,其间经历了几多波折和艰辛,最后仍未能首先在大陆出版。
顾准生前根本没有想到过要出版这本书,也没有想到过会出版这本书,因为他写该书各篇时,纯粹为了满足弟弟陈敏之个人的要求,或者是答复弟弟的提问,如关于西方史、骑士文明等篇;或者是和弟弟讨论甚至争论某一问题,如关于民主问题的各篇以及关于哲学问题;或者是对弟弟的笔记所写的读后感,如关于老子、孔子、韩非各篇。其中只有《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一篇,是应20世纪30年代的一位老朋友李少甫(立信同人,进社成员)之请所写。这些看似随手写来的笔记、读后感,绝不是信手拈来之物,而是作者多少年来的积累,凝结着作者多年来思考、探索、研究的辛勤劳动。有谁能随手写出这样的笔记?
从1977年开始,陈敏之把顾准寄来的那些笔记,稍加整理分类,重新抄写了一遍,装订成册。这些笔记,用的是当时廉价的极薄的信笺纸,字又写得很小,取其轻而容量大,然而经不起翻阅。重新抄写一份,一方面是为了借此可以多保存一份,一方面也是为了自己翻阅的方便,原没有存什么出版的奢望。
1980年年初,在北京举行顾准和他妻子汪璧的追悼会之后,一些老朋友曾经议论过为他出一本集子,以志纪念。然而因为事非容易,一时难以实现,也就搁了下来。
根据陈敏之回忆,顾准的这部文稿不会晚于1984年年底以前,通过30年代的一位老朋友(即在文化部系统工作的周静)之手,交到了享有盛誉的三联书店手里。负责审读的编者读了以后,写道:“深感作者知识渊博,很有识见。也许是因为兄弟之间的探讨问题,直抒胸臆,不讳权威……此文写于那种不讲学术、不讲科学的时代,实乃不凡之作。”当时这家出版社的负责人是小有名气的沈昌文先生。沈先生也认为该出版社“今后固然要力求系列,成套等等,但对于各色各种的单本儿的‘奇书’始终要给予支持。……顾准之作,我想是属于‘奇书’之列的”。话虽如此,不久之后,顾准之作仍通过周静这位老朋友,无声地退给了陈敏之。这已是1986年上半年的事。
沈昌文此公颇有自知之明的风范,十多年弹指一挥,他在最近风靡知识界的《阁楼人语》一书坦承:“……我是一个怯懦者,想到而大多不能做到。我当年在编发顾准前辈的文章时,就有过应当允许‘跪着造反’这念头,但临了还是扣了一些不敢发,更不用说别的稿件了(感谢后来有同行把《顾准文集》印成书了)。所以,对于在《读书》工作这些年。我所惭愧的只是,许多事没有按列宁的教导认真去做。”需要补充的是,当年《读书》刊登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之一《科学与民主》。同时《读书》在1984年第7期发表了陈敏之的《顾准与会计学》一文。
1987年12月,一位年轻的朋友陈申申(系原上海市政协副主席陈同生之子,陈同生同志与顾准在新四军根据地共事,建国后又一起在上海市任职)找到陈敏之,他在读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原稿以后,非常热忱地向上海人民出版社写信推荐这本书。他在信中写道:“顾准同志,作为老一辈共产党员中的理论家,他所留下的文字虽然不多,但是他深刻的思想所给予我们这一代人的启示却是很少人能与之相比的。他的理论贡献是历史性的。他是在那些理论上最重要、同时又是最会混淆不清的地方,给我们留下了极可宝贵的意见。若不是得益于他的学问,他的精辟的见解,他的清晰明快的语言,我们至今对许多重大理论问题还会在迷雾之中。”
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在认真审读这部文稿以后,反应也是十分积极的,1988年6月,编者提出了以下意见:“全稿文字凝练晓畅,笔锋犀利,激荡人心,读来爱不释手。”认为“作者忠于革命,热爱人民,他写的文稿出于忧国忧民之心,具有严肃的科学态度,从观点到语言都不超出学术范围”,因此可以出版。认为“作者竟能在‘文化革命’万马齐喑的年代,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这一系列真知灼见,他的智慧和勇气实在令人钦佩”,云云。不久,文稿的出版已成定局,是年8月陈敏之为此书写了一篇序言。1988年年底、1989年年初,校读了清样,满以为不需多久,就可以看到样书。然而,谁能意料得到,这本书终于还是流产。这一搁,又是整整三个年头。
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大体上体现了该书各篇蕴涵着的主要精神和思想。不仅如此,也可以认为它概括和如实地描绘了顾准一生走过来的路。其实,也不光是他一个人是如此。所有和他同时代的人,不是都从“30—40年代的战争与革命,某种远大的理想——超过抗日的理想,以及由于这种理想而引起的狂热,宗教式的狂热”(顾准语)走过来的吗?不是都经历过50年代“一天等于二十年”那狂飙式的革命浪漫主义吗?不是都需要从理想主义转到经验主义吗?所不同的是,作者较早地就“痛苦地感到,人,如果从这种想象力出发,固然可以完成历史的奇迹,却不能解决‘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因而,早在将近二十年以前就提出,现在需要的是“清醒地看到问题所在,知道我们已经解决了什么,哪些没有解决,哪些是走过了头,实事求是,而不是教条主义地对待客观实际”(顾准语)。
《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通过陈昕的关系,转给香港三联书店,作为“思想者文丛”之一,于1992年正式出版。出于某些原因,港版抽下了《民主与“终极目的”》和《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的篇目。不过,陈敏之仍然感慨万分:“现在,历经艰辛,终于见到了天日。鲁迅在为《白莽作〈孩儿塔〉序》中曾说过:‘一个人如果还有友情,那么,收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常更觉得寝食不安,给它企图流布的。’这些年来,我手里捏着的不是一团火,而是一团熊熊烈火。现在,当我手里捧着这本装帧朴素的遗著,终于见到了先兄的遗墨,因此而能得以流布,心里感到的欣慰是难以言喻的;先兄若地下有知,可能会稍稍感到意外吧,因为他根本没有想到他为我写的这些‘笔记’,居然还会出版……”
四
1980年2月,为顾准、汪璧召开追悼会以后,陈敏之和一些老同志,曾经有过为顾准出一本书(文集或纪念集)以资纪念的设想,他们为此一直在努力着。
陈敏之编辑的《顾准文集》有顾准与其弟在1973—1974两年中的通信,它曾经以《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为书名出版过单行本的部分。然而有两个不足:一是因为在香港出版,书价既贵,大陆难买到,看到此书的也不会太多;二是该书出版时,抽掉了两篇文章,因而不是全貌。因为存在着这样的不足,因此总想寻找机会予以补足。不过,更重要的是陈敏之认为,这些通信虽然是顾准写给他个人的,但是,通信中所蕴涵的这些学术思想不应当为他个人专有,应当是属于社会,因此有责任把它贡献给这个社会,这个时代。
1993年12月陈敏之自北京回沪,除了赶写出序言、编定目录、整理文稿和办理一些必要的编务上的事情外,着重的是要联系一家出版机构,以便能够如预期的赶在顾准去世二十周年(1994年12月)和八十岁诞辰(1995年)以前出版。
陈敏之以自费出版形式联系上了学林出版社,虽说不上有什么关系,不过,谈起来彼此也还不是十分生疏;有关出版的问题,没有费多少唇舌,很快就签了协议,并且按协议陈敏之支付了第一次款项。
事情办得比陈敏之预料的还要顺利,他当然十分高兴。就在《顾准文集》书稿发排前夕,责任编辑欧阳文彬(这位资深编辑曾与陈敏之一起编过《韬奋选集》)突然给陈敏之打来电话,说以前在香港出版时抽掉的两篇文章,这次也不能放进去。这是陈敏之没有想到的,因为在签出版协议、交付书稿时,他是交代清楚的。现在,既然有了异议,只能再磋商,看看能不能再取得一致。
于是陈敏之强支病体,赶到当时位于文庙的出版社。磋商中,时任出版社负责人的雷群明坚持这两篇文章一定不能放进去,并表示希望陈敏之能谅解云云。话说到这个份儿上,陈敏之除了表示能理解之外,复能何言。不过,这一折腾,几个月过去了,他为出版社能否赶在1994年12月顾准去世二十周年之前出版而犯愁。
皇天不负有心人。具有侠义心肠的朋友,任何朝代、任何社会里都有。顾准的战友、知己王元化一直帮忙联系出版社,在他的牵线搭桥下,贵州人民出版社允诺出版《顾准文集》。这次几乎没有费一点周折,出版社马上签了协议,并落实了责任编辑杨建国。一如陈敏之所预期的,在1994年12月以前看到了样书。原来陈敏之以为,在上海的出版社,许多事就近磋商、解决比较方便,因此,总不太愿意找外地的,更不说远在几千里之外、交通还不能说很方便的贵州了。可是,事实纠正了他不符实际的观念,真正的理解是可以超越重重关山的阻隔的。
虽然这本历经磨难的著作当时的征订数据说全国只有八册,但是首版三千册被迅速抢购一空,再版时仅北京万圣书店就订购了四千册。
1995年3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为顾准诞生八十周年和《顾准文集》的出版召开了纪念座谈会,对顾准和他的学术思想作出了应有的评价。顾准生前对自己的荣辱毁誉,都已经完全置之度外,更不必说在他死后了。他只认定一条,为了追求真理,锲而不舍。
顾准生前素有记日记的习惯,他去世后,遗留下的日记大部分保存在陈敏之手里,小部分则在顾准的儿子高梁(顾南九)那里。
《顾准文集》出版后,许多人都慨叹,作为思想家的顾准,生前留下的文字材料太少。许多文稿,都在那个严酷的年代被销毁了。也有人想到了一个问题,这位不寻常的思想家,是否还留下了一些未曾发表过的文字?
1997年元月,陈敏之来北京后,丁东就这个问题讨教了他,并问及他在文章中提到的日记。陈敏之告诉丁东,顾准留下的日记有三本,一本于1959年10月至1960年1月写于河南商城;一本于1969年11月至1971年9月写于河南息县东岳和明港;一本于1972年10月13日至1974年10月15日写于北京,从此他一病不起,直到1974年12月3日与世长辞。于是,丁东就产生了一个念头,应当争取让顾准遗留下来的日记与广大读者见面。
当年3月,丁东遇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编审黄德志女士。她正经营着该社所属的一家书店。她问丁东有什么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俱佳的书稿?丁东当时便谈到《顾准日记》。她对顾准的道德文章十分钦佩。于是当下说定,由丁东找陈敏之先生联系书稿,由她联系出版发行事宜。陈敏之很快就把日记的复印件寄给了丁东。黄德志这边却不顺利。这下子使丁东十分为难。这时,《百年潮》的副主编郑海天先生又问丁东有什么好稿,就向他推荐了《顾准日记》,他们选发了三千多字。《天涯》的主编蒋子丹也问丁东有什么好稿,又为她选了一万字。当时《天涯》的社长韩少功有意选发四五万字,丁东没敢答应。他怕选得太多,书就没有市场了。这时,丁东只好继续与别的出版社联系,其间的坎坷一言难尽。最后,终于找到了经济日报出版社。
与出版的艰难相比,编辑过程则几乎是一路绿灯。李慎之先生中风住院,仍然抱病作序,忙了十几天。王元化先生欣然命笔,题写了书名,他还建议,要把顾准女儿的文章收入书中。陈敏之年事已高,他与丁东一起,捧着清样,连着校了四天。书刚出来,他却检查出胃癌,经施行手术,安然无恙。
《顾准日记》出版后,虽然反响很好,但仍不是完璧。留存在高梁那里的是顾准写于1956年的中央党校日记。承蒙高梁的美意,他把这本饱经沧桑的日记簿交给笔者,让笔者写作《顾准传》时参考。后来笔者复制了一套,编辑《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时,选编了其中几篇,也算是首度问世。
《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是笔者应中国青年出版社之约选遍的一本顾准文选,它简明扼要,基本上把顾准各个时期的代表作,都囊括进来。当时笔者的复旦同学、中国青年出版社副总编辑李师东听说笔者正在创作《顾准传》,对顾准的情况多少有些了解,而他正在策划《野百合花丛书》,于是他就约请笔者选遍一本顾准文选,笔者选了十几篇顾准的文章,并撰写了五万多字的《顾准的生平及其学术思想》,作为导读,书名定为《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于1999年1月出版。
又过了数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再次独具胆识,于2002年1月编辑出版了由陈敏之和顾南九(即高梁)选编的《顾准文存》,该书一套四卷,包括《顾准文稿》、《顾准自述》、《顾准日记》、《顾准笔记》等,这是目前最为完整的顾准文集。对于出版社领导的远见卓识,我想编者和读者都心存感激。
顾准的思想可能会过时,顾准的精神永远不会过时!但愿顾准精神能够薪火相传,伴随千千万万的中国知识分子迈向新的进程。
2009年2月17日五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