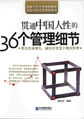转眼又到了中秋之际,京城的街道上飘满了桂花香,西山的落日给大地披上了一层温暖的金黄色。
太后华诞又至,宫中人皆喜气洋洋,忙里忙外,礼部原定了七七四十九日的宴席,被太后骂了一顿后,缩减为八天八夜,分批宴请文武百官,其中最重要的要数太后诞辰当日的皇室家宴。太后一向最疼爱孩子们,子子孙孙也算孝顺,封地的藩王多有奏请回京拜寿的,太后颇为欢喜地答应了。
在这举国欢庆之时,却有人不识时务,鼓动一批新进后学,在慈宁宫外跪请皇帝上朝亲政之事。
此刻太后正在殿内与刚刚回朝的征西将军密谈,作陪的是胞弟忠烈王、内阁首辅杨清。太后知道后依旧谈笑自若,面上并没有任何表示,好似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事。
其他人却坐不住了,忠烈王忙立起身道:“太后,让臣弟去喝退这些狗腿子。”
太后笑道:“这种小事何须费心,哀家倒要看看这些人能在宫门外撑多久。”
征西将军冷哼道:“黄毛小儿,也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话锋一转,问道:“首辅大人可知是什么人如此不长眼吗?”
杨清已是三朝老臣,朝廷中附庸后生极多,年纪又比在座的都大,竟跪到太后脚边,稽首再拜道:“少帝年幼,若不得太后扶持,只怕寸步难行。望太后恕罪,老臣有句话,今日不得不说。”
这话说得旁边的两个人都变了脸色,但太后却笑着让人拉起他来,道:“您坐着说。”
杨清推开来拉他的宫人们,依旧跪在地上道:“臣以为:有太后您在,才有王朝的安定与繁荣。臣斗胆恳请太后为百姓计效仿大唐武氏,在其治下,乃是昌明盛世啊。”
旁边的两个听到一半,也忙忙跪在太后面前,连连附议。
太后笑着扶起他们,归坐之后缓缓说道:“本宫从未有此想法,一则本宫不愿受着拘束,二则本宫若有此意,皇室族人、各地的封王们怕是会群起而攻。”
太后还没说完,忠烈王就抢着说道:“太后何必为此担忧?内有臣弟保您万事无忧,外有将军保您边疆安宁。就算不得已打一仗,也是为了肃清朝廷。”
太后闭着眼睛说道:“你也把朱氏看得太轻了,如今大伙儿给哀家面子,倒也是因为他们把哀家看成半个朱家人。我们又何必为了一个虚名,干戈迭起,让百姓颠沛流离,让我们的子孙流血伤亡呢。”
屋子里的人各有各的心思,忽听到外面有些喧闹,旁边的莲香对太后说道:“皇上来了,在外面跪着呢”。
原来文正听到消息后马上赶到慈宁宫,虽气急却也不敢对着大臣们发怒,只是好言好语地让他们回去,儒臣听也不是,不听也不是,唯有一言不发,仍旧坚持跪在原地。
文正无法,只得也跪在慈宁宫门口,又要显示与那些儒臣不是一帮,隔了一些距离,口内反复陈情:“儿臣驽钝,莽撞无行,蒙母后规训之德,不敢说有所长进,只求少犯了些错。朕负了老师的教育之恩,全无进益,还需好好闭门攻读圣贤之书……。”
如此絮絮叨叨,并没有什么重点,也不知屋子里的人听不听得见。
忠烈王道:“臣弟真替太后不值,如此无才无德!简直是扶不起的阿斗。更可气的是如今翅膀都没硬,就在这里播弄是非。”
太后道:“无才无德?”像是在问自己。又笑道:“不过这件事,哀家还是相信他的,哼,他还没有这样的本事。”
忠烈王疑惑道:“太后的意思是有人……”
太后叹道:“已经有人不服气啦。”
忠烈王道:“那,会是什么人?”
太后看了他一眼道:“也许这两天就知道了。”
几人品着这句话,只道这天下说不定又要有些变化,将军道:“太后,这次老臣回来还带了几千精兵,屯在城外,随时听候您的差遣。”
忠烈王笑道:“将军这就过虑了,这京城之中,还不需您来挂心”。
太后笑道:“这就是你蠢了,分什么京城京外,都是哀家的左膀右臂。一说倒想起来镇南将军,这些年也不曾回朝。”
屋内的人辗转定乾坤,屋外的文正在慈宁宫门长跪不起,委屈又绝望。太后既没见他,也没说什么,就把他给打发走了。
两日来文正也不曾被召见,皇宫内熙来攘往,一切都与他无关。虽然每日仍旧去佛堂诵经,却从来不曾耳根清净,心内一直有种不祥的预感,不管撺掇这件事的人是谁,自己怕是逃不过一劫了。如果是太后,她是铁了心要废了自己,不过这捞什子皇帝做的真没有什么意思,只是如果自己有事,不知飞儿又会怎样?如果背后是势力强大的藩王,只怕自己还是第一个献祭的牺牲品。
这天巳时,文正照常与柔嘉一起在殿内小院的清心亭读书写字。四面是砖红瓦墙,墙外是红叶蓝天,微风轻拂,两人的衣衫飘动,红色的木凳木桌,一个面西,一个朝东。
太傅教完了书,留下功课就走了。柔嘉撑着头在翻书,可是眼睛却一直盯着皱着眉头写字的文正,她想逗他开心,故意道:“皇上,您闻到了吗?秋天就是一股桂花味,我们去摘些来,酿一坛桂花酒怎么样?”
文正放下了手中的笔,笑道:“你有这兴趣,好啊。等午时休息了再去吧。”
柔嘉往前凑了凑,拉拉他的袖子道:“师傅走啦,又不用担心。”
文正往远处看了一眼,殿墙外一簇簇金黄正映着蓝天,颇有一番宁静的美,回过头看着她满是期待的眼睛,伸出手抚了抚她的额头道:“还是再等一会,把这写完了再去不迟。”
柔嘉嘟着嘴道:“可是午时我得在太后那儿……”
文正道:“朕中午给你摘好了,洗出来,下午再一起埋在桂花树下,还免得脏了你的手,不好吗?”
柔嘉坐回去,勉强点点头。
文正用手敲了敲桌子,道:“过来到这边坐,看着朕写字。你说你女孩子家的,非要来跟着学这些诗呀文呀,有什么用处呢?”
柔嘉走过去,站在他的身边,低头瞪了他一眼,道:“用处大着呢”,然后假装气呼呼地开始研磨。
文正却坏笑地看着她,跟了一句:“是啊,用处大着呢!”
到了用膳的时候柔嘉念念不舍地走了,文正匆匆吃了些饭,带着宫人们一起去摘桂花,宫人们在树上玩的不亦乐乎,他也颇想爬到树上去,却只是扯了一把刚刚够得着的桂花,拿在手中把玩。
忽听得背后一声断喝:“没规矩的东西,你们干什么呢?”
把文正唬了个心惊肉跳,忙转身前去作揖行礼道:“王爷,是朕今天想自酿些桂花酒……”
忠烈王眼睛一翻,哼了一声,道:“朕,朕,狗脚朕。真是不知分寸!”
文正愣在当前,不知如何应答,手中的桂花抖得扑簌簌地往下掉。
忠烈王气盛地问道:“昨日教的兵书背会了没有?“
文正木然地摇了摇头。
忠烈王道:”不务正业,玩物丧志的东西。那今日也别学了,滚回去给我在门口跪两个时辰去,好好反思反思。”
文正只得低下头唯唯答应,忠烈王骂骂咧咧地离开了。
等忠烈王走远,宫人们一个个垂头丧气地,直呼“倒霉,倒霉”,扔掉手中的桂花,就要往回走。
文正道:“把桂花都拿回去。”
其中一个宫女心疼道:“您何必还拿回去呢?这不是找晦气吗?”
文正平静地道:“没事,你们先回去把酒酿了”。说完先转身走了,后面的宫人默默地捡起地上的一把把桂花,一行人回到了殿内。文正将手中落得没几粒花的树枝递给了宫人,就掀起了袍子,直直地跪在了宫殿门口。
宫人们扑通扑通一个个跟着在门外跪了一地,心里都委屈,却谁也不吱声。文正把他们看了一圈,道:“你们忙去吧,洗干净了,清理好了放在坛子里。”
宫人们忙起身,一个个弯着腰从他两侧鱼贯而入,自去忙碌,准备桂花酒。
秋天的太阳并不毒,相反很温柔,也不让人晕眩。宫殿的阴影一点点的没过文正的身子,他也渐渐感受不到膝盖上的疼痛了。
柔嘉伺候完太后,未时才喜滋滋地带着宫女往文正这边赶来,远远看见在斜阳底下,文正跪在着凹凸不平的地砖上,心里莫名心疼,眼泪就漫上来了。
柔嘉道:“哪个师傅这么狠心?您又何必这么十二分地服从呢?”
文正苦笑一声,道:“你哭做什么?那不是把朕再责罚一遍?快扶朕起来,赶快去埋酒”。
柔嘉忙擦了一把眼泪,和宫女一左一右,扶着文正摇摇晃晃地起来,柔嘉道:“皇上您先去休息一会吧。”
文正却着急道:“朕一点事都没有,这酒不现在装好埋下去,就不新鲜了。”
两人将宫人们选好洗好的桂花一层层地装入黑色坛子里,又倒入纯酿的糯米酒,密封好后两人来到殿后的一颗楸树旁,两人跪在地上,用小铲子铲了半天才挖出个不大不小的坑。
文正放下铲子,道:“来,和朕一起把它放进去吧。你说放三年还是五年?”
柔嘉扑哧一笑,道:“三个月就能喝了,放那么久做什么?”
文正道:“越久越香啊。”
柔嘉摇头笑道:“那是要拿来喝的,放那么久早忘了。”
文正道:“怎么会忘呢?三五年后朕和你都长大了,在某一天,应该是个特殊的日子,一起挖出这坛酒,岂不是更妙吗?”
柔嘉扭头看向他,觉得他这话别有深意,但文正只是默默地用土把坛子埋起来,她在想是什么特殊的日子呢?想着她就红了脸,也低下了头,将挖出来的土一点点往回填埋。
第二天是太后生辰最重要的日子,文正一大早就去佛堂为太后诵经祈福,竟然看到了蒲团上跪着个小小的人,竟是有段时间未曾见面的映雪,忙上前问道:“你身体好些了吗?这大夏天你也没来几次,怎么反倒是这深秋时节来了?”
映雪点点头,笑道:“我早好了,以后想去哪就去哪,今年冬天我一定要去雪地里打滚。”
文正道:“你这名字可不是这个意思呀?静悄悄地赏雪不就行了吗?”
映雪哈哈地笑道:“皇上您陪着我一起去打滚,不行吗?”
文正笑着摇摇头,扶着她坐在蒲团上,自己也坐好了,又问道:”托王妃带给你的书,都看了吗?可还喜欢?“
映雪点头道:”真是多亏皇上了,您知道爹娘常常连房门都不让我出去,每天丢给我的又都是佛经,要多无聊有多无聊。只是您说给我的书,他们总不好拒绝的。“
文正开玩笑道:”你这么喜欢看书,将来是要嫁一个文状元吗?“
映雪也不觉得这问题难为情,大声答道:“我要嫁给一个大侠,像我爹一样的大侠”。
皇上听闻过一些王爷以前的事,仍旧问道:“为什么?”
映雪道:“每次我娘讲起他们以前的生活眼睛都亮的像珍珠一样,到处去游山玩水,关键还能救很多很多人呢。”
皇上笑道:“关键还是到处玩?你的心思就在只这上面。”
映雪笑道:“才没有,您不知道他们的生活的多么有趣呢!”
文正本是十分开心,听了这些话,有些郁郁地说道:“映雪,朕也多想离开这个地方啊,像你说的那样,去很多地方,过有趣的生活,救很多人,可是事情却都不在掌握之中。”
映雪笑道:“做皇上岂不是更厉害?天下都是您的,您所做的事情可是是拯救全天下的百姓呀。”
文正道:“可是朕很多时候无能为力,甚至……,自身难保。”
映雪道:“不管怎样,我和皇上您永远都是一条心。”
文正心里突然很暖很暖,欠起身来轻轻地抱了一下映雪,很快又松开了。
映雪愣了愣,反应了一会就站起来,走上前去抱住了文正,这一回倒是文正愣住了,他埋在她的脖颈间无声地笑了。
映雪放开了他,回到座位上道:“皇上您如果不开心呢,一定要跟我说啊,我不在的时候可以给我写信,因为这两年都是您给我的书和信在我一个人的时候陪着我,我不想您不开心。”
文正心里暖暖的,竟然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只是默默地点头。
从外面进来的南安王妃无意中听到了无忌的童言,一想到这些天听到的风声,对皇上的处境,也是有些感慨唏嘘,只能避重就轻地问道:“皇上,太后的生辰礼物可准备好了吗?”
文正突然发现王妃回来,忙忙见了礼,回答道:“嗯,不过并不算得珍贵,只是自己写的一幅百寿图。”
王妃道:“这不妨事,太后一向俭省,只要合了她老人家的意,总不会有什么大碍。”
正说着,宫女莲香来请皇上去见太后,王妃和映雪依旧留在佛堂。
文正有些不舍地看了映雪一眼后,跟着莲香去了。宫中缠绵了几日的笙乐依旧如酒浓烈,只不过连日听来不免有些乏味又嘈杂。
此刻戏台上正唱着《打金枝》,太后听得乏了,便在后面小殿中歇息。太后端坐正中,远道而来的藩王们也终于到齐了,在这最重要的日子里向太后表忠尽孝,敬献贺礼。
先是皇上献上了一副亲手写就的百寿图,祝词也是朴素:“儿臣恭祝母后寿比南山,福如东海。”
接着,柔嘉跪到太后膝下,道:“我会的不多,只是为姑母亲手缝制了一匹腰带,在里面放入了干姜、甘草、茯苓和白术的粉末,这样您逢下雨天就带着它,腰就不会那么疼了。”
太后温柔地搂过她,道:“你最有心了,哀家虽不爱闻那中药味,也要时刻系着了。”
柔嘉得意地笑道:“这个问题早想到了,所以绣娘教我将所用的布匹先浸入玫瑰花粉所泡的水中,再等晾干后用,所以姑母你闻闻看,是不是非常香?”
太后闻了一下,赞许地看着她,道:“嗯,很香,吾儿真是又孝顺又聪明。”
柔嘉道:“只要姑母喜欢,我还能做出更多的好东西来”。
其他养在宫中的王子皇孙们虽大了两岁,也都还未成年,又得应着太后节俭的要求,俱是送了些小玩意儿。
藩王们正相反,虽路途遥远,却是极尽奢华,所呈上的多是各地的珍奇宝物。
归德王上前道:“儿臣不能常常在母后跟前尽孝,于是想着做一个小物件伴在您身边,还望您常常想起儿臣。”
归德王乃太宗第四子,此前颇受太后恩宠,文帝病重时,朝廷中人多以为他会继承大统。
太后忽露出感伤之色,道:“哀家也多么希望你们都在身边啊。不过很多事都是身不由己,你们能来,哀家已经非常开心了。也不怕他们见怪,你是哀家最心疼的。看看你准备的东西,是不是比他们更懂哀家的心?”
归德王道:“儿臣准备的只是一支发簪。在儿臣的印象里,母后很喜欢自己的头发,而发饰除了常带的几样,却并不多。于是前年请了一个师傅在家中,打算做十二个发簪敬献给您。在观察师傅的过程中儿臣觉得这门手艺也颇有趣,于是也跟了学,斗胆自己也做了一枚,原本打算不过是送到宫中,现在因着今日生辰,还能亲自送来,交到您手里,也是了了儿臣一番心意。”
说完,归德王从袖中拿出一个狭长的盒子,取出簪子,远看颇有飞扬之姿,太后眼睛马上一亮,笑道:“你有心啊。”
归德王捧簪上前,令人呈了上去,银簪长约四寸,后两寸镂刻着一簇夭夭桃花,又有三颗绿宝石镶在尾端。
太后拿在手中把玩了一会,颇为喜爱,归德王上前道:“难得母后喜欢,让儿臣为您带上吧。”
太后点点头,归德王走到面前,将簪子拿到手中,突然殿中传来一声清脆悠长的哨声,大家都往哨音的方向望去。只见一群浓墨重彩的戏子挥着水袖施施然地进到殿中,分散在各个角落,依旧“咿咿呀呀”地唱着曲。大家正自纳罕,是谁安排了这样的节目,这些人怎么不经通传就来到殿中?
归德王面对着太后,并未去看背后的情景,趁此扰攘,握手成拳,银簪直取太后脖颈。
太后觉出了不对,推开左手边的柔嘉,本能地往后仰倒,大声惊呼道:“救命!”但这一声除了近处的人根本没人听得见,而太后身边不过就是几个未成年的孩子。
归德王冷笑一声,轻轻按动簪子顶端的绿宝石,一根长四寸的极细的针从金簪中射出。
这根金针被一只小手挡住了,扎在了拇指下方。
惊恐的救命声渐渐爆发,离太后不远的守卫终于也发现了行刺行为。忠烈王大声呵斥守卫们,而此刻分散在四周的伶人们也停止了吟唱,从水袖中取出利剑。殿内的守卫与优伶的数量差不多,但不多时就处在了劣势,殿中多是平日养尊处优又没什么本事的王公贵族,纷纷大叫逃窜,一时乱成一锅粥,而殿外也是杀伐声四起,万想不到气象万千的皇宫竟会有此血腥变故。
因为坐在右手边的文正伸手挡住金针,太后得空,连忙往左边钻去,口中直叫着大太监明魁的名字。归德王一击不中,伸出左手拉住太后,再次按动宝石,文正忍痛钻到太后前面,惊恐地面对着归德王,针刺入文正的左肩之中,几乎全部没入。
归德王怒极,啐道:“傀儡就是傀儡,我就先杀了你。”说完就举起银簪向文正心口刺去,文正用右手握住簪子,尽力阻止,但力量微小,簪子已经刺入肉里。
幸好远处的明魁击退“伶人”飞身赶来,一脚踢开归德王,护住太后往殿后退去。
而大殿之上,归德王已经占了先机,双方力量悬殊,虽然因着明魁,叛军近不了太后的身,但忠烈王已被生擒,殿内的王孙都被制服,缩在墙角处求饶。
归德王退到“伶人”的护卫圈中,指着忠烈王道:“母后,还不叫他们住手?这可是您最疼的弟弟。”又转头对着明魁道:“明魁,你武功这么好,又忠心护主,本王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你又何必守着这样一个的不能到头的主子呢?”
刘青也不答话,只警觉地看着周围。太后神色悲戚地说:“哀家一向最看重你,想不到你竟出此下策。”
归德王冷笑道:“母后真是会开玩笑呢,要看重本王,坐在这里就是本王了,又怎会有今日之事呢?不过您传的位恐怕只有他才能坐的下去吧,本王一向是不喜欢嗟来之食。”
这句话听在别人的耳中不知道是作何想,受伤倒在座椅上的文正痛苦的眨着眼睛,但这种情况下并没有人能够来救他。
太后凄凉地笑道:“今日实在有意料之中的事,也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哀家敢做这个位置,就料到会有的这一天,只不过从来不应该是你们这些乳臭未干的少年人。”
昌图王道:“要怪就怪母后自视甚高,非要逆天命而为。今天本王也不想大开杀戒,只要母后现在写一封诏书,我就放了忠烈王,还保二位后半生享不尽的福。”
太后道:“哪有享不尽的福?哀家写就是了。只是哀家有个疑问”,太后扫了这些“伶人”们一眼,问道:“他们是怎么进来的?”
昌图王笑道:“本王其实十分佩服母后,智识过人,只不过您有一个最大的弱点,就是太过信任您的亲弟弟了。您听听外面,打斗的声音多么大,好像是御林军在自相残杀,您猜猜外面进来的会是谁带领的军队?”
跪在地上的忠烈王忙问道:“你什么意思?你这个逆贼,忘恩负义!”
昌图王得意地说道:“不瞒您说,现在御林军中有一半都是我的人……”
太后制止了他,道:“你不用再说了,哀家现在就写诏书。”
变起仓促,不到一刻钟时间好像天地都掉了个个,外面的战斗之声渐渐小了,变成了军队整齐划一的步伐,往慈宁宫方向走来。
归德王将诏书拿在手中,看了又看,正自高兴,外面忽听的一声大喝:“保卫太后,捉拿反贼。”
只见征西将军带着军队昂扬地走进殿中,归德王不敢相信地望着他们,忙道:“快宣读诏书!”
身边的伶人拿起诏书,还未打开,就被将军一箭射中手臂,道:“大胆反贼,还不速速投降!”
说完,又是一声令下:“放箭!”
一时之间,殿内矢如雨下,那帮伶人虽见情况陡转之下,仍做困兽之斗,不多时,好几十名刺客已经倒在地上,归德王被生擒。
太后走上前去,道:“今日哀家再教你一课,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还有弹丸在其下也’,本宫早就料到今日有人要以身试险,你们的动作太过明显了,所有的野心全都写在脸上了。这么蠢,不好好地做王爷,还妄想去做皇帝?”
一切停当后,太后奖有功,罚有过,立即下旨封征西将军为勇武候,仍令忠烈王处理相关后事。
三人回到太后寝殿,也是颇为感叹,还好只是有惊无险。太后道:“勇武候何止勇武,宫中万象,本宫还不及您看得清楚,果然被您一语中的,虽然本宫宁愿你的计策不用派上用场真的有用。不管怎么说今日本宫欠你一个大大的人情,您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大国舅跪下磕头道:“一切都是太后的恩典,臣又怎么敢擅自领功?只是今日来去无踪的黑衣人,太后要好好查查到底是什么人?居然如此公然闯入宫中?
太后追问详情,原来在叛军与御林军正自打得难分难解之时,忽然从夜色中跃下一批批的黑衣人。具体多少人数,士兵的汇报并不一致,他们见人就杀,士兵们但求自保,也不管谁是谁非,绵延二三十里的喜庆之地,从乾清宫到御花园,转眼间成了一场三方混战。黑衣人明显是江湖人士,武功之高强远在这些吃粮饷的士兵至上,眼见士兵们渐渐不支。
但将军带着几千精兵浩浩荡荡地奔入宫中之时,只混战了一刻钟,但见一只响箭自太和殿内升起,在空中燃成一朵美丽的烟花,所有黑衣人且战且退,全都收手离开了。原先的御林军本已大大受挫,黑衣人离去后,征西将军很快就控制了叛军。
太后听完后沉吟不语,将军只得自己说道:“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人应该不是归德王的部下,只怕还有人……”
太后叹口气道:“其他的人都成不了气候,不管怎样,这也是一个知进退的人,今天的事哀家希望到此为止,不过多追究,哀家也有对付的方法。”
勇武候答道:“太后仁慈,还有一事,太后也需要好好计量,逆贼在宫中势如破竹,御林军的漏洞实在有点……“
太后点点头,沉思了一会,道:“所言极是,御林军如此虚弱,远超乎哀家的想象。只不过现在再假手他人只怕问题更多,还请勇武侯您多帮衬着,助忠烈王一臂之力。”
勇武侯道:“一切但凭太后安排,老臣自当尽力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