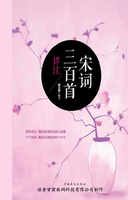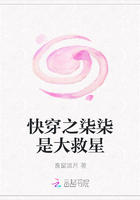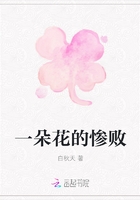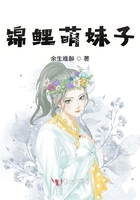南方妇女手巧,无论是刚从地上挖出来的毛烘烘的春笋,还是已经上样却被暴风折断的的笋脑稍,被她们一拨弄,准会整出百出的花样,百出的吃法。香甜如梨头,喷脆如萝卜,臭如豆腐酪,醇如花皮蛋,味道各异,简直怀疑不止一种原料了。
雨后春笋,外行的人总以为这是形容毛竹长势喜人。却不知道山冈上,山坡上,原野上,奇种异类的竹笋全淘气地露出头来,仿佛有人在拔节一样地生长。山冈土薄,小山笋细小如钢琴家的手指,瘦削玲珑,大家在挂满露水的荆棘丛里跋涉,才采到几束,所谓物以稀为贵,这是舍不得晒干的,趁嫩,炒着吃,做笋菜蛋,佐料有米醋、韭菜、蛋花、老酒。这碗小菜,你不贪吃不行,味道实在妙,贪吃也不行,筷子大把地夹,吃得鼻子沁出汗来。山坡上土厚,毛笋密密麻麻的,简直使你落不了脚,害怕不小心踩断了刚露头的笋脑勺,这些笋,除非大批量出售,否则我们不挖。我们挖土壤里深埋的笋,最好是碱性的黄泥地,我们叫黄泥头拱。白嫩,光滑,用来放咸菜汤,先清水落锅,煮炖时间长,去其涩辣麻,特鲜美。如果不放水,撒层盐,直接用文火煲,先是滋出大量的汁水,当锅底干燥,要防止它烧焦,熟时,外咸内甜又清口,大家喜欢淡吃,当作水果一般,吱嘎吱嘎地咀嚼。地头里的小竹笋,农家侍弄得好,今天挖完了,明天又密密麻麻地比赛着长,早邦的贵,妻子曾经化十几元,买一株,我说她笨,等不及了自家的笋啊,她还辩解,说是味道不一样。而迟邦的则比较便宜。
旺季时,竹笋的生长正在势头,采挖的笋太多,为了适宜于保藏,要晒成干货。而品质上乘的,要数小竹笋,如雷竹、箭竹,箬竹。每天采少量,整株的,剥皮后,用清水煮熟,用文火煨熬后,放在石板地上,用大块的硬石头压迫,直到榨干清水,一夜以后,在竹篾上晒干燥,条状如鱼干,颜色黄如粳糖,嫩笋皮薄,则近似透明,但是天气不好,也会发白,和毛笋差不多。市场上出售的毛笋干,细碎成片状,泚盐花,条丝分明,品位则不及于它了。
今年母亲送来橡皮笋,那是她特地从山上折来的野笋,如拇指粗细,仅仅三斤左右吧,据他说,用煤球风炉烤了一整天,软脆,青白,适宜冰箱里冷藏,要用的时候,用肉来烤,口味清淡,却沾油。听着这些话的时候,脑子里忽然闪过祖母的影子,在十年以前,自己刚买了房子,祖母为我过重的压力而神伤,上城里看我,带来瓶装的盐水笋,所谓“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可是作为山里头人,以为自己厌烦了这些东西,把藏在柜子里的盐水笋,全倒进了垃圾桶,祖母生气得直跺脚,骂我不懂事,看不起老人拾掇的,是嫌弃她老背,我还嘴硬,以为在祖母这里可以撒撒气,和她争论,惹得她真生气,一跺脚,回了老家,虽然小心翼翼地去向她赔罪道歉,她终于乐意接受我的孝顺。仔细想来实在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至今祖母已经永别,已经无法来尽孝道,而悔之不及。
去年,母亲腌制臭笋卤,据说味道是一流的,母亲总说:“好吃嘞,好吃嘞。”却不知道怎么个吃法,所以慌不及地拿了两大罐,留一罐自己,送一罐给潘。待开罐却不臭,麻涩无法入口,以为母亲做法错误,自己不能吃,当然无所谓,可是向潘无法交代,估计他是倒掉了,而自己房子大,不占地,瓶罐就放在角落里,几个月后,想起来要倒掉,打开瓶盖,那股臭味,才迅速蔓延开来,笋的纤维丝腐烂得如豆腐酪,粉质,暗白色,品尝一下,入口即化,爽滑如泥,味浓,醇厚方正。这时才知道,一样东西大凡需要出色,不仅需要制作的原料、手法,还需要时间,急不得。
小时候,因为山林属于大队,分到户的山笋并不多,所以大家制作菜笋几乎是精雕细琢了,常见的倒扑笋,煮得半熟,或者直接把生笋装在酒酲里,用黄泥封口,以尼龙布做衬,倒扑,放在水缸脚等湿地里,直到年关,打开封口,从水里撩起来,白胖,仿佛贵妃出浴,和红烧肉一起烧烤,滑腻,细嫩,爽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