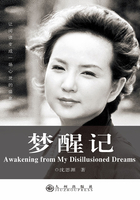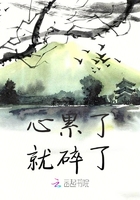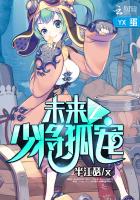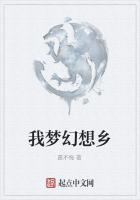自然,对于平庸的人来说,看书是指看闲书。
那年,在象山中学读书,夏谷鸣老师做班主任。由于习惯于自由散漫,在自修课,总要说几句废话,晚自修后也不按时就寝,钻进被窝里,满身裹着毯子,打着手电筒看书,被值周老师抓住,或者在十四个人一间的大寝室里,整天紧张的学习之后,禁不住地兴奋,也喜欢讨论一些热点事件,也可以归于说废话一类的事情。所以不时地被夏老师叫去训几句。
办公室里老师很多,训话是对自尊心的一种打击,是心理上的一种煎熬。去的次数多了,感觉特害羞。就主动向他发誓:“老师,你不要把我叫进办公室了。以后要么有事情,和你也合得来,可以谈心,反正我自己进来。绝对不能犯错误,再被你叫进来了。”
可是看书,总归熬不住。
那时看书,校内校外是截然两个天地。校内读的,除了教科书,还是教科书。学校虽然号称县内第一中学,但是没有课外的读本,更没有人来引导你来读课外书。可是校外却书潮滚滚,改革开放的早期,香港台湾的书籍已经很普遍地散开来,像个热点,同学们基本以读过这些书为荣。学校门口,有个租书店,书架上排列的,全部是言情小说、武侠小说、侦破小说。金庸、琼瑶、三毛最吸引人的。欧美的书籍,长篇的原著很少见,但是内容简介和内容缩写,在小杂志里看得见。记得在学校门口不远处有个售书店,我的饭钱大都买了《中学生阅读》,只是因为里面的名著解读,很吸引人。
这不,那天早自习,刚刚谈话不久,我又迷不住,看起了《窗外》,那种死去活来的感情描写,绝不仅仅代表流行和时髦,也不仅仅切合高中生的情感渴望,更比教材里干巴巴的几篇文字生动的多。周围书声琅琅,我独有自己的另一番天地。桌子上有两排屏障,靠前堆立着厚厚的教科书,眼前竖立着语文书,作为遮蔽,以为很安全,却因为读得专注,夏老师走进来管理纪律,并没有注意,书本太吸引人,也无法注意。
老师走到我身边,一声不响,就把书本拿了去,然后离开了教室。我也一声不响,交出了书本,头抬得老高,脖子伸得老长,眼睁睁地看着他离开了教室。
书被拿走了,可是书店里的租金却不能少。每天五分钱,一天要一天的租金。五分,不是个小数目。它可以混一餐中饭,买一碗红烧肉;它可以买一本《中学生阅读》;它可以乘车去一趟老家;它可以……心在滴血啊,那一天一个五分钱就被夏老师白白地丢在办公室里。为了节约下那个被惩罚的五分钱,在食堂里,我几乎餐餐喝油条酱油汤。
可是又放不下架子,是自己说的,自己决不能因为犯错误进办公室,于是僵持着。老师不知道心痛,浑然无事,好像忘记了似的。我是心急火燎,当然面子上也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过了一段时间,我估计自己要破产了。于是候在办公室门口,等待夏老师走过来,然后我走过去,假装是偶然碰到的,其实是希望他看见我,记起这件事情,叫我进办公室,然后教训一顿,然后把书还给我,再然后让我去把书还掉,让我解脱这一件负担。
可是见了面,他就是和我热情地招呼,和我淡然地笑,也说点家常的事情,就是不把我叫进办公室。教学楼前的树木葱葱茏茏,阳光从树缝里摇摇摆摆地撒下金钱斑,每天就在这个地方重复同样的故事。我傻呆了。
日子在静悄悄地流过,租金在一天天地累积。我焦急了,心急就莽撞,也不顾三七二十一,就算忘记自己发过的誓言,就算撕破脸皮,终于鼓起勇气,冲进了办公室,大叫起来:“老师,你看见没?书上那个出租公章?这个可是五分钱一天呐!”
办公室里还有政治史老师,她正在低头批改作业,吃惊地抬起头,用手抵了一下鼻梁上的眼镜框。三个人都笑起来。一定是夏老师说起过,他要用这种方法来治治我。夏老师笑起来,眯着眼睛,露出一对小虎牙,很和善,很有亲和力的,他从抽屉里拿出书本,寄给我,没有说什么话。
我连忙接过来,沿着下坡路,飞一样地跑出校外,到了书店,结算钞票。老板娘很客气,我说明情况以后,还给我减免了一大半。
似乎卸下一样沉重的负担,心情很轻松。高高兴兴地回校,忽然想起来,《窗外》这本书,我其实只看了没有几个字。于是不禁又懊恼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