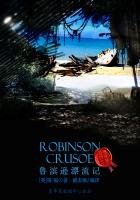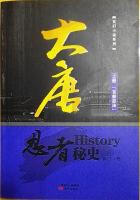很多时日以后,章第中回忆这天中午的经历还非常纳闷,他真的不明白自己是怎样从茫茫人海中“拣”出那张面孔的。第一次瞥见那面孔,他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可再审视一下,凝聚眼力审视一下,感觉实在没有错,才急急推了推身边的机头,“看,那不是鲁老师吗!”
人流像一条河,浩浩荡荡无始无终,鲁伟祺老师身穿一件严重褪色的灰黑棉衣——三年前给章第中当班主任的时候就穿过,无精打采或失魂落魄地在人流中挪动着双脚,满脸胡茬,神形憔悴。机头冲口便喊:“鲁伟祺!老同学!”
鲁老师充耳不闻,依然故我地挪动双脚。
“鲁伟祺,你耳聋了吗!”机头提高嗓门。
行人纷纷投来奇怪的目光,可鲁老师仍然没有听见。
章第中索性追了上去。
鲁老师更没料到与熟人相遇,“你们……在北京干啥?”
机头简要通报了情况,“你呢?你……咋这副模样啊?”
鲁老师不答,摇晃脑袋,连声叹气。
“到底咋了?该不是一鸣……”
鲁老师苦苦笑着,“一鸣大学念失败了。”
“真的?为啥呢?”
“他迷恋网络,功课挂了七八门……现在连人找不见了!”
“啊?这……”
鲁老师也是数月之前接到清华大学相关部门的电话,说儿子鲁一鸣沉迷网络游戏,渐渐荒废了学业……第二天,鲁老师便疯似的往北京跑——包括这次在内,鲁老师已经先后四赴千里迢迢的北京了。前三次,他侥幸都见到了儿子,谈心、悔过、痛哭、理解、勉励,是父子相见必有的情节和内容。可等到父亲缝补着百孔千疮的心情返回沉木,信誓旦旦的儿子便故态复萌,不仅无法如见面承诺的那般改掉恶习,反而变本加厉地依赖网络游戏了。最近由于补修的功课又出了问题,他更彻天彻夜泡在了网吧里,不回学校不进宿舍了。鲁老师急啊,欲哭无泪,寝食难安,恨不得将天戳一个窟窿,最后别无选择,又不得不放下工作四赴北京,然而这次来京都五天光景了,却连儿子的影子也没有找到。
“快求沉木老乡帮忙吧,咱人生地不熟的。”机头说。
“老乡能帮的都帮了,我该走的路也全走了。”鲁老师说。
“那学校呢?一鸣毕竟是清华的学生啊!”机头又说。
鲁老师摇头,“学校也束手无策啊,要不就不会兴师动众通知家长了;再说一鸣屡教不改毫无诚信的,我咋有脸再找学校呢!”
“可咱总是活人,得想法子拯救孩子呀!”机头说。
“我多次给一鸣发信息了——父子一场,别无他求,只想再能见上一面。”鲁老师仰天长叹,颧骨高耸,脸色铁青,结了痂的嘴唇血迹斑斑。
首都四通八达的街巷里,处处人满为患,个个行色匆匆。
“咋的会这样!咋的会这样呢!”机头也急得什么似的,紧皱眉头苦思良久,“从情理上讲,我最应该帮老同学了,可眼下带着两个学生,事关全局,责任重大,实在无法分身,等几天后考完试,再帮老同学找一鸣吧?”
“有你这句话就感激不尽了!”鲁老师眼含热泪。
“话咋能这样说!一鸣也是我的学生!”机头说。
鲁老师频频点头,“第中他们的前程比啥都重要,你们该干啥干啥去吧。”
“那也行,说说你的手机号码,咱随时联系吧——我手机新换不久,把你的号码弄丢了,”机头就要告别的样子。
“不。”一直沉默不语的章第中突然说,“现在就应该找一鸣哥!”
“啥?你……”其他人大吃一惊。
“我现在就跟鲁老师找一鸣哥!”章第中重复说。
“你马上要去熟悉北大考场呢!”机头首先否定。
“对,你专心把试考好吧。”鲁伟祺老师更不同意。
章第中想了一想,招手邀机头跟田园静移步,深深地向两人鞠一躬,拜托他们替自己去熟悉考场。他的声音早已哽咽了,“鲁一鸣跟我都是甜水乡的土街上长大的,鲁老师更是我初中三年的班主任,鲁一鸣爷爷又是我爸的恩人,如今他家遭遇了天大的困难,我说什么也应该尽力帮一把的。”
章第中心里翻涌起一种毫无理由的直觉:假如让鲁老师就此孤零零地离去,那么也许,也许会永远消失在北京的茫茫人海之中的。
机头仍然摇头,仍要坚持说什么;随后赶过来的鲁老师,也摆手示意要说什么。可田园静抢先表态了:“咱就按章第中意见做吧——反正离开考还有一天多,一切应该来得及的——相信肯定能找到要找的人!”
田园静的表情里,带有跟年龄不相配的成熟与严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