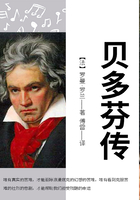温体仁官邸,毛云龙刚一走进,温体仁便满面笑容地迎了上去,问:“这几天朝中热闹吧?”
毛云龙兴奋地说道:“众口一词,切责首辅以妖术欺君,大有倾倒之势!”
“老夫早就说过,如果胃口不好,吃进去的东西还要吐出来的!”温体仁幸灾乐祸地一声冷笑,“万寿宫乌烟瘴气啊!”
“若把张真人淫乱之事,再捅出来,更有他周延儒好看啦!”毛云龙眯起一双色眼,津津乐道地,“据说这个张真人一夜能战九女,且夜夜不虚,竟诡称是采阴补阳。”
“好!咱就再告他个淫乱内宫,败坏人伦,那周延儒就吃不了得兜着走啦!”温体仁甚为得意。
毛云龙掏出一张纸来,递上:“学生已遵大人旨意,串联上疏,弹劾周延儒。”
温体仁接过一看,立刻沉下脸来:“怎么没把你那个宫女写上?”
张真人淫乱内宫之事,是与毛云龙相好的宫女告知他的,而且千叮咛万嘱咐,决不能将此事捅出去,而毛云龙为此还指天发誓地做了保证。如今温体仁不仅要将此事捅出去,还要在奏疏上将这宫女写明。这让毛云龙颇感为难……
温体仁听完毛云龙的陈述,颇不以为然:“那宫女是人证啊!不抬出她来,怎能扳倒首辅,置周延儒于死地呢?”
“只是这样一来,那宫女岂不被我出卖?而且她的名誉性命……”毛云龙深知这样做的后果,该宫女不仅将从此名誉扫地,而且性命也将难保。
温体仁铁青着脸,丝毫不为之所动:“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一个宫女的名誉性命和我等的宦途相比,孰重孰轻?切不可因小失大呀!”温体仁见毛云龙脸现不悦,便将语气相缓下来,上前拍了拍毛云龙的肩膀,笑笑说:“漂亮的女人还不有的是!事成之后,送你八名美妾!”
毛云龙依然担心地说:“宫女的名声肯定完了,只是她性命……”
温体仁一拍胸脯:“我温某保她不死!”
这时,门外一阵“笃笃”的敲门声,中断了他们的这场交易。
“有人来啦?”毛云龙提醒说。
温体仁稍停了一下,颇为自信地手捻胡须:“依老夫猜测,该他周延儒找我啦!”
果然,屋外传来家仆的声音:“老爷!周延儒周大人在客厅等候。”
“就来!”温体仁应声后,狡黠地看了一眼毛云龙。二人相视开怀大笑!
待安排好毛云龙后,温体仁收起了诡笑,缓步来到了客厅。
只见首辅大臣周延儒一改往日的潇洒与自负,正愁容满面地在客厅里踱来踱去。
“惭愧惭愧!让延儒兄久等了!”故意晚到了一会儿的温体仁一走进客厅,便连忙道歉,显得热情至极,“坐!延儒兄请坐!”
“唉!”周延儒没有心思体察温体仁的神情变化,而是一见面便首先发出了一声苦叹,“皇上龙颜大怒,朝中上疏不断,攻击老夫是故弄妖术,欺君乱政!真是墙倒众人推,破鼓烂人捶,四面楚歌啊!”
这一切本都是温体仁一手策划的,也是他最为企盼的结果。可温体仁却装出一副深表同情的模样,竭力抚慰:“延儒兄言过了!设坛祭天,本意是从公出发,不为大过嘛!”
周延儒一脸苦楚,双手作揖:“乞望体仁兄扶危济难,帮小弟渡过难关。”周延儒见温体仁颇能体谅自己的苦衷,大为感动。加之温体仁身为次辅,在朝中的地位仅次于自己,如今自己有难,只能乞望他能在此关健时刻拉自己一把。
“无须关照,理当鼎力相助!”温体仁拍着胸脯,真可谓义气千秋,义薄云天:“首辅次辅,本为一体,唇亡齿寒,荣辱与共!”说着还挤出几滴泪水道:“卑职恨不能替延儒兄代为受过!”
“体仁兄一片体恤之情,令小弟刻骨铭心,永志不忘!”若是平日,凭周延儒的机警和聪明,应很快会识破温体仁这过火表演背后的伪善和狡诈,可今日因大祸当头,自身不保,以致思维紊乱,一心只想着涉险过关,对温体仁不仅毫无提防,相反还大为感激。他从怀中掏出银票递上:“这是五万银票,一点棉薄之意……”
温体仁心中窃笑,想你周延儒这只铁公鸡,居然也会拔毛!他将银票一推,笑而婉拒:“这……就大可不必了吧!”
周延儒见此,将银票又推送过去,诚挚地说:“乞请在皇上面前春风美言,力助小弟安渡难关。
“你我一殿同僚,敬请延儒兄放心!”温体仁信誓旦旦,“温某不耻犬劳,当应效命,面跪皇上给大人求情宽宥!”
“容日后结草衔环,登门叩谢!”周延儒因过去与温体仁一向貌合神离、同床异梦,没想到温体仁今日竟如此仗义慷慨,这使周延儒大为感动,一再地施礼致意,“那就不再打扰了!”
“周大人请慢走。”
温体仁目视周延儒离去,伸手从桌上拿起银票,凝视一笑。
第二天,崇祯的御书房内,“吧”的一声,那张银票被狠狠摔在长案上!
崇祯盛怒不已:“本已欺君罔上,居然心怀叵测,又行贿次辅!”
站在堂下的温体仁极表愤怒,俨然一腔正气:“陛下!微臣虽然愚笨,岂能不是不非,为五万两白银所收买!”
“好!”崇祯对温体仁拒绝贿赂、深明大义的举措,大为欣赏。他目视着温体仁,备感欣慰道,“一些人别有用心,极尽蛊惑,言我大明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攻一点而不及其余。爱卿不徇私情,拒受贿赂,足见品格高尚,纯忠亮节!”
崇祯提笔在案上挥就“纯忠亮节”四个大字,他拿起字幅:“纯忠亮节,为先生品德写照,朕以这四个大字相赠爱卿!”
温体仁上前接过字幅,躬身—拜:“谢陛下恩赐!”
这时,王承恩走进禀报:“万岁爷,首辅周延儒前来求见陛下。”
崇祯—脸怒气:“宣他进来!”
王承恩刚一退下,周延儒便躬身走进,递上疏文,面带愧疚地跪地奏道:“陛下!微臣愚昧,偏信妖术,检讨罪责,甘心受罚,改正己过。”
崇祯接过疏文连看也没看,便狠狠地往桌上一撂,盛怒地斥责道:“本来祭祀一事,你请妖人作法,秽乱宫廷,闹得举国颠倒,本已可恶;而你身居首辅,理应为百官万民之表率,可你竟然带头徇私贿赂……”
周延儒不知温体仁从中作乱捣鬼,连忙分辩道:“启禀圣上,臣虽愚钝,但万不敢徇私行贿!”
崇祯轻蔑地用鼻子哼了—下,厉声道:“你真的不曾徇私行贿?”
“微臣如有营私,甘受重罚!”周延儒虽然看见温体仁站在一旁,但并未想到温体仁会出卖自己,相反还以为温体仁会帮自己美言开脱,所以他指天发誓,信誓旦旦。
崇祯本以为周延儒他会找理由解释开脱,没想到他竟如此狡赖,直气得崇祯猛地操起银票拍到了他的面前,戳指怒目地赫然斥问:“这是什么?”
周延儒上前盯视了一眼,认出是自家的银票,转回身看看温体仁,只见温体会正在得意地奸笑,他顿时明白:自己被这老家伙耍弄出卖了!但此时醒悟,一切都为时已晚,他狠狠地侧目瞪视了温体仁之后,唯有垂下头去,再无一言。
温体仁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但他并未以此而满足。他走近狼狈的周延儒,轻轻一笑道:“这不是首辅大人亲自送到卑职府中的吗?”
崇祯对周延儒是最为欣赏倚重的,因为他容貌后秀,又善体帝心。崇祯一直以自己能得此良才、识此良才而沾沾自得。由他出任首辅,安邦定国,以为这是社稷之福、大明之福,但谁知这周延儒竟也如此贪赃枉法、蛆附蝇聚、朋党成奸,这使崇祯大失所所望,气愤莫名,气涌如山!直气得崇祯不仅浑身抖颤,声音也为之抖颤起来:
“身为首辅,以妖术欺君,已是罪大恶极,朕本念你无意冲犯,予以宽恕,可你不思悔改,竟然知法犯法,行贿次辅,以罪掩罪,该当何罪?”
周延儒见事已至此,唯有伏跪在地连声说:“老臣死罪,死罪!”
崇祯目视周延儒,一声令下:“朕念你有犬马微劳,从轻发落,免除死罪,罢官撤职,致仕回乡!”
周延儒跪地叩首:“谢皇上不杀之恩!”
崇祯又一声令下:“由爱卿体仁继任首辅!”
终于如愿以偿的温体仁立即跪拜:“谢皇上隆恩!”
周延儒侧视着身旁这阴险诡诈、毒如蛇蝎的温体仁,从牙缝里迸出一句:“你这个王八蛋!”
山寨窑洞的晚上,一支蜡烛晃动着跳跃的火苗,烛花卷曲,烛光黯淡。一只女人的手在轻轻地抚摸着男人光溜溜的脊背。
这个女人,即是李自成新纳的妻子邢氏,而那个光背的男人则是李自成的爱将高杰。高杰是最早与李自成一道起事的弟兄,因其聪明伶俐、年龄又最小,一直颇受李自成的宠爱,视为心腹爱将。而邢氏夫人原本就是高迎祥从风月场中花钱买来的风尘女子,生性风骚,嫁给李自成后,本以为李自成虎背熊腰、高大伟岸,可以极尽床笫之欢,尽情淫乐。但谁知李自成这个伟丈夫,却一心只想金戈铁马,驰骋疆场,成就一番大事业,这无意中就冷落了邢氏。年少风流的邢氏,耐不住寂寞,便设法勾引英武帅气的高杰。
高杰正值青春涌动的年华,哪里抗得住邢氏一再挑逗!终于在李自成外出杀敌的一个夜晚,邢氏只穿一袭睡袍进入高杰的屋内,到了房中,邢氏将睡袍一脱,露出全裸的胴体。光洁的肉体,一下子都展现在高杰的眼前!这个从未接触过女人的壮汉,怎能受得了这般诱惑,当晚二人便勾搭成奸。自此以后,只要李自成一离开营寨,邢氏便趁机溜到高杰的住处。高杰对此虽感到愉悦,但时间一长,内心中总有些提心吊胆,惴惴不安,觉得对不起李自成大哥。
而今天,邢氏更是大胆,竟趁李自成睡熟之机,就跑了过来。高杰本来很喜欢抚摸邢氏的脊背,因为顺着这细如凝脂般光滑的脊背摸下去,总能给高杰一种无法抑制的冲动和快感。但今天,他虽任由邢氏抚摸挑逗,而他的手却刚一放上邢氏的脊背便骤然停止了。他翻身坐起,心有余悸说:“你……快走吧!”
邢氏躺在炕上,斜视了他一眼:“怎么,快活完了,心满意足了,就下起逐客令,撵走相好的心上人了?亏你说得出口,难道你就真的舍得?”
“哪能舍得你哩?只是让李大哥知道,咱俩就完了!”高杰说着穿上布褂,挑去灯花,窑洞里顿时亮了起来。
“现在怕了?可你色胆包天,让他戴上了绿帽子就不怕?”邢氏说着,竟忍不住啜泣起来,“这种日子我过够了!过怕了!每次都偷偷摸摸地藏着掖着,弄得人不是人,鬼不是鬼……”
正所谓情人的眼泪具有暴君的力量,男人最受不了这种眼泪。高杰见邢氏哭了起来,连忙凑身坐在炕边,替邢氏揩着泪水:“嫂子!……”
“现在喊嫂子,刚刚还心肝宝贝地喊不停呢!”邢氏嗔怒地说,她抬起泪眼,目视着高杰,又怜又爱,一头砸进高杰怀里,“你个讨债的!啥时候咱俩能光明正大过上夫妻啊!”
“我也想光明正大做夫妻啊!可现在怎么行呢?”高杰抱着邢氏劝慰着,“要是李大哥半夜醒来不见你,就会起疑忌,还是快回去吧!”
“放心吧!他上床就是打呼噜的死猪!哼,他根本就不是男人,嫁给他,我等于夜夜守活寡!”邢氏一手紧紧抱住高杰,而另一手则拿过自己带来的包裹,“妾身今生已跟定高爷,李自成的钱财尽在我手中,咱俩远走高飞,落个逍遥自在,走吧!逃吧!”
“逃?”高杰惊骇地手一松,睁大了眼睛望着她:“往哪儿逃?”
偏偏这时门外传来呼唤声:“高爷!高爷!”
声音虽轻,但高杰却万分惊恐,他顺手操起床头的腰刀,喝问:“谁?”
“是我,李二。闯将爷派人找你呢!出事了!”
邢氏一听,也惊恐地坐起身来:“啊?这怎么办?”
“这是我的马弁,没关系。”高杰轻声说着将衣服递给邢氏,“快到后面去!”
邢氏抱着衣服赤着脚,悄悄地躲到了屏风后面。
高杰迅速整理好被子后,方转身打开房门。他在门口一站,并没有让李二进屋的意思:“出什么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