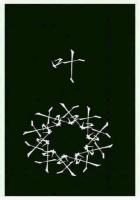又或者,别人的诱惑他或许可以阻挡,但是白月,白月的那样的女子,优雅纯洁到让人不忍心染指,只要是一个男人,都无法不心动吧?
她很想否定这些想法,她希望只是一场梦,等醒了一切都会恢复原样。
她没想到刘修祈会来看她。
已经好些日子不见了,自从那个惊雷乍现的夜晚,府上的那些传闻她不是没有听到,只是充耳不闻罢了,她要的是一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交代,她要听见他亲口说,说是不是爱上了白月。
这一刻是她既期待又恐惧的。
“夜莺。”耳畔响起长阳王一贯的清清冷冷的声音。
“是你。”明知是他,夜莺的心跳还是加快了一拍。
“伤好些了么?”
他知道她受伤了?夜莺心中冷笑,如今时隔一月,还不好的话岂不是真要残了?到这时才来问,不过是敷衍了事吧?
夜莺点点头。
也许是眼前景色太美好了吧,美好到有些不真实,夜莺无端的有些伤感起来,心中的委屈在这一刻一并而发,竟有眼泪在眼眶中打转儿。
“你知道我家以前有一只鸟儿唱歌很好听么?”刘修祈缓缓的说:“我以前一直不喜欢小动物什么的,直到在集市上看到那只鸟。它的羽毛很漂亮,不像一般的夜莺是灰褐色的,它周身都是黑色,黑得发亮的那种,在阳光下泛出紫色的光。我竟然将它买下来,当贵宾一般的养着。”
“你说过的,因为我的声音有点像那只鸟,才叫我夜莺。”
“是啊,后来我们一家都被流放了,我决定放了它,去那么远那么苦的地方,这鸟儿一定经受不住的。”
刘修祈的表情变得有点伤感:“但是它却不肯飞出笼子,无论我怎么赶它。”
“后来呢?”
“怕是过惯了养尊处优的日子吧,它已经忘记如何在没有荣华富贵的生存了。这样是不行的啊。”刘修祈叹息了一声:“我只好杀掉它了。”
夜莺的心募然一抖这话什么意思?
“你为什么不试着带它去呢?”
“去和我受苦吗?与我共赴那生死未卜的前程么?”刘修祈冷笑一声:“既然它不要自由,我也不想让它受苦。不如由我来为它做个了结吧。”
“你对我说这话什么意思?”他在暗示什么?难不成他今天也是来做什么了结?
“其实我很后悔呢,”长阳王换了一副近乎伤感的表情:“就像你说的,为什么不给它一个机会试试呢?在那了无人烟的地方是多么寂寞,多少个夜晚,我都梦见京城的繁华,我都梦见那美妙的歌声在耳旁萦绕。可惜,我再也听不到了,就算再买一百只鸟儿,也不能唱出与它相同的声音。”说最后一句的时候,有种近乎咬牙切齿的恨意一晃而过,快得让人以为是错觉。
“我不明白你到底想说什么。”夜莺一头雾水。她以为他的来意是关于白月的,但是没有。对于白月他竟只字未提。
“夜莺,你该明白,在我心中,你是无可取代的,就算再有一百个杀手替我杀掉所有我不想见到的人,但是那个人不是你又有什么用?相见的人不见了,不想见的都消失了又有什么用?”
夜莺听到自己的心跳急剧加速,他想说什么?接下去呼之欲出的是什么?是不是有可能是她等待多年的,一直一直期盼着祈祷着想听到的“你对我而言,绝不只是一个杀手那么简单。”长阳王意味深长道,但是这句话好像只说了一半,就像一首弹的好好的曲子,正是部分,却戛然而止……
“那我对你来说是……”夜莺还没来得及企口问,只觉得手腕间一凉,低头一看,一直晶莹剔透的白玉镯子套在手腕,上面还有刘修祈的余温。
“这,算什么?”
“忘了么?今天是你十九岁生日。”浅浅的笑挂在刘修祈唇边,少有的温柔。不愧是楚国第一美男,俊逸非凡的脸,浅柳色长衫衬得他那白皙的脸更是光华无限,微挑的剑眉显出几分慵懒不羁的风情,乌黑的发丝,随风一吹,轻拂面颊,风姿绝世。这一笑谁不为之倾倒?
夜莺当然不能抗拒眼前的男子。
从在西域的时候,她就誓死追随他,整整八年了,从一个懵懵懂懂的小女孩到现在处事不惊杀人不眨人令人闻风丧胆的刺客她,不后悔。
夜莺抚着手腕上的白玉镯子,好像凝视着自己的爱人。
其实她知道,那日长阳王过来不过是安抚她一下,好让她继续为他卖命,一切只不过是讨好她的,只不过想让她再去杀人,那就直说好了,何必绕这么大一个弯子,她早就决定余生为都他卖命,他要杀什么人她就杀什么人,每每踩在刀剑浪口,几次挣扎在生死边缘,何曾惧怕什么?又何曾怀疑过什么?
但是她没有想到的是白月竟然也会来看她。
那天的白月一身白色绸缎衣裳,而花园里海棠花开,纷然如火。衬得红的更红,白的更白。
虽然一同在长阳王府待了近两年,但是两人的交集并不多。夜莺有一半时间都出门在外,而白月原本住的潇湘阁离留芳阁离得甚远,就好像现在的雅风居和夙澜居一样。
琥珀色的眼,樱花般的唇,白月的确是美好得令人难以调转视线的女子。
她定定看着夜莺,开门见山道:“刘修祈不是你的良人。他……”
话未完只觉得脖间一凉,夜莺的弯刀已经架上她的颈脖,白月背靠着假山,整个身体被夜莺死死她抵着,稍一动弹便能见血。然而她竟然毫无畏惧,眼中淡然无波,夜莺从那琥珀色的瞳仁里看见自己的模样,这哪里是平时冷然的自己,这个表情写满了嫉妒的女子让自己感到陌生!
白月背靠着假山,白色的绸缎长裙上落了几瓣海棠花,要看起来如同血迹。而夜莺的黑色锦绣长裙上织出大幅蝶恋花,春意融融的一副好图案,穿在她身上只显得冷淡,这一黑一白的绝色勾勒出一副对比鲜明的色彩图画。
“我的事,不用你劳神。”夜莺冷冷道。
“他不过是在利用你。”白月的一针见血道:“所有的人都是他的棋子。”
夜莺怔了怔,缓缓道:“你懂什么?我认识他这么多年,其中的恩怨,不是三两耳语就能讲得清楚。”她松开手,微微扬起下巴,看着高远蓝天,轻轻笑了两声:“你可知道,人生本来不过就是场棋局罢了。”
“你真傻。就算当初他救了你,你为他卖命为他杀了那么多人,也报了恩了,为什么不离开?”
“离开?除了杀人,我到外面能做什么?”夜莺自嘲道。
白月微微眯眼,直视夜莺。那目光有一种穿透力,仿佛一直要看到人心深处。
她冷冷一笑道:“你不愿意离开,因为你喜欢刘修祈,对不对?”
夜莺不说话。
火红的海棠花丛中,两位绝色佳人就这样对持着,为了一个叫做刘修祈的男子。
而刘修祈不愧是刘修祈,在京城所有人都以为他这辈子再无翻身之日的时候,他竟然带着几千里的风尘仆仆,带着饱经大漠风沙却依然风神如玉的身姿,当然也带着藏匿在恭谦外表下的狼子野心回来了。
刘修祈原本就是天之骄子。
他是大楚太子刘启真的独子,少年才俊,文武双全,十二岁时刀术在同龄人中已是无人能及,“天下第一”的名衔迟早是他的囊中之物。
就是这一年,是他命中的劫数。
多少个夜晚,当他闭上眼,眼前都会浮现起那时的情景。
那是一个深秋,风卷着漫天的落叶,吹得天地间都是萧条之意。
太子居住的龙延宫灯火通明。
睡梦中的他被叫醒,说是有圣旨来了,当下一惊这深更半夜的来圣旨,他有种不好的预感。他急急忙忙穿好衣服,一路小跑到大殿接旨。
那是怎样一道圣旨?
“太子刘启真意图谋反,经查实证据确凿,实不能容,汝将严惩不贷。今日起削其太子位,贬为庶民,举家刺配西北马前关,终身不得返京。即时启程,不得有误。”夜晚的灯火照在宣旨的公公脸上,从他的角度看过去,半明半暗,尤为可怖。
每一个字都像针一样,深深扎在他心里。
马前关是什么地方,他听都没听过。
“还不快谢恩?”公公催促道。
“谢……”刘启真嘴唇颤抖,说不出谢字。
然圣命不可违,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
从那一刻起,楚国京城再没有当了三十年太子依然还是太子的刘启真,再也没有少年得志意气风发的刘修祈,他们全家人连夜离开,仿佛水汽一般人间蒸发。
不止如此,厄运还没结束。
那日残阳如血。
废太子刘启真离开京城已有几日,遣散了佣人,刘家大大小小还有几十口人,个个都被拷上了手链脚链,稀稀落落的无精打采的走着。
昔日华服如今灰尘扑扑,衬的脸上的表情更是灰败。皇室中人亡命天涯,真如丧家之犬。
押运的官差说得轻巧:“我看太子爷您就知足吧,没有杀头就不错啦!”
十二岁的刘修祈哪里受得了这般嘲弄,不待父亲有所反应,便怒声道:“你是什么东西,轮到你在这嚼舌根?你连给爹提鞋子都不配!”
“哈哈,怎么轮不到我?告诉你,现在我就是爷,我说什么就是什么!你以为自己还是京城的公子哥?我呸吧!”那官差竟然一口吐沫吐在刘修祈身上,他顿时火冒三丈,要拼个你死我活,但是无奈手脚受束缚,一身武功也没法施展。
“祁儿,算了。”身边响起温婉的女声。
那是记忆中母亲的样子,始终温暖如初。
母亲曾是楚国第一美人,足当得起“倾国又倾城”的赞誉,他最不能忍受的就是把这么美这么柔弱的女子牵扯进来。
他看了看母亲,狠狠咬了咬唇,双拳紧握,终于不说话。
夜晚,他和母亲共用一座小营帐,席地铺了被便睡着了。
迷蒙间,只觉有人轻拍着他,身上的被衾也被人往上提着,忙睁开眼时,母亲闭着眼,睫上有泪,依旧睡着,一双手却下意识地抚着他的背,为他盖被。
他抱住母亲,闻着她温暖中的气息,即使遭遇这样的磨难,也可以张开羽翼将他牢牢护着。只觉得眼眶渐渐湿润。
“我们一定会重见天日的。”他说,声音很小但是很坚定。
“祈儿,有些东西是命中注定的,是你的便是你的,不是你的就不要强求。”母亲语重心长道。
“命?”他哼了一声,颇为不屑:“什么是命?从天堂到地狱就是命么?我偏不信!”
母亲叹息一声,不说什么。
从来不曾经过颠沛流离,乍然过这样的日子,这种落差已然超过他的承受范围,忽然想起那个算命人的话:十二岁时会有劫难果真是一场劫难。
就在此时,营帐突然被掀开,是刘家的贴身护卫范易,只见平日冷静镇定的他现在面色惊慌,他心里一紧,知道出了事。
“快跟我走!”就这么四个字,已充分说明事情的严重性。
“启真在哪?”
“先别问,快走!”
没有片刻犹豫,他们匆匆忙忙的出了帐子,空气中有血腥味。他知道这是血光之灾,他竟然没有慌乱,而是出奇冷静的拉着母亲逃走。
范易驾了马车,长鞭一甩,马儿的嘶鸣划破长空,一路前行。
但是来不及了。
月明星稀,透过树影斑驳,一道道追逐的黑影,手中扬起一把把弯刀,刀锋在月光闪亮处,映成怪异的光芒。
那几个黑衣人显然都是一等一的高手,几人骑马簇拥了他们的车,团团包围。
范易手执了长矛,一边驾车,一边向挡过来的人影狠刺,硬生生向前破开一条血路。
刀影纷飞,星光缭乱。
范易誓死护主,最终还是落得身首异处。头颅飞出时,鲜血淋漓已溅上刘修祈一身,绽了大大小小的鲜红,如凌乱到不堪的春日残红泼墨画。
马车被迫停了下来。
平生第一次被那样强大的恐惧压迫者,他感到呼吸沉重。
如果他有武器,如果身边没有需要保护的母亲,他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但是没有如果。
今晚必死无疑。
“祈儿,你逃吧。”他听见母亲在耳边小声道,声若纳蚊。
“不。”他决定拼死一搏。尽管额上已是冷汗涔涔,但是他,绝不就此认命。
黑衣刺客毫不留情,弯刀叶片般袭来,他侧身躲过。
一次。
两次。
三次。
他很想护住母亲,但是力不从心,平身第一次这样软弱无助。
苍茫大地间,刀光起,血光落,月影惨淡,渐成迷蒙的淡红。
终究还是躲不过,一刀刀被割开的伤口,身体撕裂般的痛楚,他不得不单膝下跪支撑身体,抬头想看清母亲的模样,看到的只是一晃而过的苍白笑容。
雪白霜刃,在清冷的月光里带出一道最后冰寒凛冽的光芒,深深地深深地剜入他的心口。
世界在这一刻安静的可怕,没有一丝活的气息。
“都不重要了……”
很清晰地,他听见一个声音,却不知来自何处。
他左手摸索着胸口,好像有什么东西几乎割裂了身体,疼的快炸开。
他用力拔出胸口的弯刀,鲜血簌然喷出。
胸前一片湿湿热热的,他的心沉了下去。
命运是什么?是金枝玉叶般的出生?是少年得志?是一朝被贬不得翻身?是在路上就被赶尽杀绝?这就是他的宿命吗?这场劫难注定是他逃也逃不掉的吗?那么温柔的母亲,就这样离他而去了吗?凶险的宿命啊,什么时候会消失?
都不重要了。
他想闭上眼睛,安安静静地等待一切的结束。
但,他无法。
他有些不放心。
也不甘心。
被无辜夺去的生命,不能就这么算了。
“刘修祈怎么能死在这帮黑衣人手上?”
他紧紧握住的拳头,仿佛听见骨节爆碎的声音。
一滴泪,在脸颊,滑出。
眼泪滑出。
滑出。
然后落下。
落下。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
废太子刘启真一家人被来路不明的刺客杀光了,只剩刘修祈一个人。虽然差点死了,但是终归还剩一口气,只要还有一口气,他就绝不会放弃报仇。
那些刺客是受谁人指使呢?
以刘修祈的头脑不难猜到,为了巩固自己的羽翼未丰的皇权,有一个人必须要斩草除根。
那个人是刘启明,刘启真的同父异母的哥哥。
其实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要要追溯到两代以前的楚国。
其实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要要追溯到两代以前的楚国。这时候楚国建国不久,开国之君楚怀王颇有治世之才。在位四十年,使得楚国由一个小小的诸侯国日益强大,傲居这乱世三大强国之一。
唯独缺憾的是,在立储这件事上楚王总是犹豫不决。
老楚王一生风流,膝下子嗣良多,儿子就有十四个,除去早夭和病死的,也还有十二位皇子。虽然按照规矩应当立长子为储,可是他心里比较中意的是四子,也就是刘梓宣的父亲刘启明,因为是自己最宠爱的妃子所生,刘启明也算争气,至少在老楚王看来,他是天资聪颖,能成大事之人。
但是迫于政治压力,最终还是立了长子,也就是刘修祈的父亲刘启真做了太子。
刘启真这太子一做就是三十年。
三十年,真的是很久的时间,很多人都说他是真的心急了,去谋反去宫,但是刘修祈很清楚父亲绝不是这样的人,他一直对老楚王佩服得五体投地,连顶撞一句老楚王的话都不敢讲,就算再当三十年太子,就算这个头衔当到死,他都不可能会做这样的事。
然而现在人都死了,谁也无法还他清白。
总之一纸皇令,刘启真一家被贬谪到西北蛮荒之地,包括十二岁的刘修祈。
于是一切终于从了老楚王最初的心意,刘启明不久就被册封为太子,次年老楚王驾鹤西去,刘启明登上帝位,是为楚宣王。
即位的楚宣王毫无悬念的将儿子刘梓宣立为太子,待他百年之后,世袭君位。
这一年,刘修祈在西北受苦受难,而刘梓宣在京城意气风发,十四岁就成了楚国未来的新皇一切看起来简单,但是刘梓宣真正实至名归的当上皇帝却不是那么一帆风顺了。
除了被废的太子刘启真以外,刘梓宣还有十个叔叔伯伯以及他们的一帮子女眼馋着皇位,刘梓宣想太天平平的活到登基绝不是件容易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