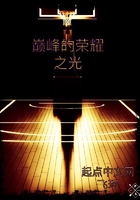猴氏双雄一见宝典,两眼放光,急跃向前便来争夺宝典。玉面书生费书清一急,拨动铁骨扇机关,“嗤嗤”两声,两支毒针射入猴氏双雄的后背要穴。那猴氏双雄怒目圆睁,一个“你”字刚说得一半,便已气绝身亡。玉面书生正自得意,不曾想泰山派的吴道长更是出手如电,玉面书生还没来得及笑出声来,吴道长的长剑已是穿胸而过,玉面书生倒卧于地,一脸似笑非笑的怪异表情。
吴道长杀了玉面书生,更是一刻不停,身若旋风快似闪电,将萎缩在庵内墙角的后辈弟子,尽皆斩杀干净。吴道长提了长剑向薛振缓步走来,出言道:
“少侠休怪贫道手辣,此事机密重大,贫道也是万不得已,留你不得。”
“阿弥陀佛!”
忽听得半空中有人口喧佛号,庵内院中已然多出了一位宽袍博袖的老僧,一部白须在夜风中当胸飘展。那老僧双手合十道:“吴道长也是泰山派的名宿,做事如何这般狠辣,今日也须留你不得。”吴道长也不答话,挺剑便向那老僧刺去,那老僧两掌一合,便将吴道长的长剑粘在一对肉掌之中。吴道长用力抽送长剑,长剑却像长在那对肉掌中一般,动弹不得。只听得老僧一声清喝,劲风到处长剑顷刻断成数段。吴道长一怔,那老僧手起掌落,一掌拍在吴道长的头顶命门,吴道长闷哼一声,倒地殒命。
那老僧双手合十口喧佛号道:“阿弥陀佛!贫僧一念不净造此杀孽,罪过!罪过!贫僧回寺,自当面壁三年,每日颂佛三千,超度道长。”
那老僧捡起锦缎卷轴递于薛振,说道:“还好薛少侠无恙,这‘元阳神功’宝典闵施主既已授于少侠,便是薛少侠的因缘福报,将来薛少侠练就神功造福武林,也是一段佳话,阿弥陀佛。”
薛振接过锦缎卷轴,匍匐于地,给那老僧叩首行礼道:“晚辈薛振,感念圣僧再生之德,还望赐告佛号法名。”那老僧哈哈笑道:“薛少侠不必多礼,贫僧少林寺慧聪和尚,来此已久,本不想管这江湖恩怨,一来感念少侠心存忠义,二来那道士太过狠毒,方才出手相助,少侠日后多存善念,便是大和尚的福报,贫僧这就别过,阿弥陀佛!”
“多谢老前辈教诲!”
薛振抬起头来,那慧聪和尚已是去得无影无踪,想那和尚宽厚仁慈的长者之风,心下不禁怅然。回头再看闵婆婆,已是身死多时,薛振打来一盆清水,擦净婆婆身上血迹,背往庵后山上埋葬。
葬完婆婆已是天色微明,薛振心想在江湖上行走,带着“元阳神功”宝典恐至有失,一旦露眼,还有杀身之祸,不如将宝典记诵明白,就地将锦缎卷轴埋于闵婆婆坟头。主意一定,薛振便坐在闵婆婆坟头,打开卷轴仔细诵读,直到反反复复背诵无误,方才放下卷轴。
薛振在闵婆婆坟头挖了个深坑,在庵内找来一个小巧的神龛做成木盒,将锦缎卷轴用油布包好置于盒内,旁边撒了些木炭石灰,方才将木盒放于深坑之内。掩埋好木盒,已是辰时将尽,薛振整顿衣冠,这才骑了快马离开月华庵。
道路两旁春色依旧,而薛振的心境却已完全不同,经过昨晚的一场血腥搏杀,让他看到了江湖的险恶,人心的险恶。现在,和那个刚出大名府意气风发的少年相比,此时的薛振已是判若两人,他看上去更加沉稳,更愿意去想一些问题了。
神功秘籍已然记诵在心,薛振心下却不着急练习,他想等见着师傅之后,征得他老人家同意再练不迟,这也是为人弟子的本分。
和师傅这才别了两天,薛振已从鬼门关里走了一遭回来,人生在世真是祸福难料。
经历了昨晚的一场大凶险,薛振此时特别的想念师傅,此次师傅赴燕京诛杀叛徒胡天德,一定也是路途艰险,风波险恶。有心上燕京寻找师傅,又恐自己武艺低微徒增师傅的负担。和师傅相约的时间尚早,薛振决定先回栾川看望母亲和姐姐,顺便请师祖爷和窦师姑指点武艺,潜心练武,眼下练好武功才是最重要。
薛振骑马上了官道,沿着官道一直往汴京开封府而去,他要在开封府的黄河码头搭乘去栾川的船只。
不日,薛振便到了开封府的黄河码头,投在了码头边的一家骡马店里,把马寄养在骡马店,便到码头上打听去栾川的船只,不想近几日却不得其便,只好在骡马店里要了间房,就近相侯。一晃已是多日,薛振整日在骡马店房里打坐,练内丹真气,天不亮便到黄河边滩涂上练拳掌剑法,不想几日下来内功剑法尽皆精进,似有一日千里之势,这让薛振惊喜异常。
原来薛振将“元阳神功”宝典背诵得滚瓜烂熟,而宝典开篇的总纲,便是天下武功要诀的总揽,练气练剑更是有独得之密,薛振在练气练剑之时不自觉地将这些高深的法门用于其中,事半而功倍。薛振每日行完功,练完剑,便觉神清气爽,步履轻健,以前练功之苦已渐渐消失,练功之乐在逐日增加,而薛振并不知道,这正是神功宝典的巨大威力。
连日来,薛振心意畅达,神精气足,举手投足间更显英气勃勃,月华庵那场恶斗的阴影也已渐渐退去。
这一日,船老大到骡马店知会薛振,后日便有船去栾川,卯时三刻准时开船,要薛振早做准备。想着不日便可见着母亲、姐姐、师祖爷和窦姑姑,薛振心下十分的高兴。薛振和母亲、姐姐、师祖爷和窦姑姑已是许久不见,想着要给他们各备一份礼物,顺便也要逛逛昔日帝都的繁华街市。
薛振换了件交领长袍,腰间系了条玄色丝绦,脚蹬快靴,头顶一方逍遥巾,出了骡马店便往开封府的闹市上去。开封府的大街上,楼宇重重,雕梁画栋,各样的货栈、酒馆、茶肆鳞次栉比,门前旗幡精美,招牌锃亮。薛振几次和师傅来过开封,尽皆行色匆匆,不曾有闲心漫步街市,尽识昔日帝都的繁华喧闹。
薛振正自兴味盎然,忽见一身材瘦弱少年朝自己奔跑过来,后面紧跟着一个粗布短打的店小二,只听那店小二高声叫喊道:“快抓住那小贼!快抓住那小贼!”薛振待那少年跑到近前,一用力便捉住了少年的手臂,一抓之下便觉那少年筋骨酥软,再看那少年却是长得肤色白嫩,五官纤巧,俏皮的圆脸上故意抹了些灰土,乌溜溜的大眼睛里却已是泪光闪闪,娇羞之态楚楚动人。
薛振猛然惊觉,自己抓着一个姑娘的手臂,心似电蜇,赶忙放开手臂。
此时,那小二已追至跟前,举手便欲打那女扮男装的少年,薛振赶忙拦住道:“小二,这位小兄弟偷了你家什么物事?”小二道:“一个大馒头!”薛振从袖笼里掏出一小块碎银子道:“小二,这可够了?”那小二欢欢喜喜地接过银子,又点头,又哈腰,连声说道:“够了,够了,谢谢公子爷!”末了还朝那少年狠狠地瞪了一眼。就听得那姑娘都着嘴说道:
“就一个馒头,哪要那许多钱。”
仔细看那姑娘,虽是穿着一件宽大的男子袍服,经过她细心的拾掇,却也是合身合体,一块过大的裹巾子,多余部分也被她巧妙地藏在脑后黑发之中,浑身上下收拾得干净细致,还是位心灵手巧的姑娘。薛振向那姑娘瞧了瞧,摇了摇头便即转身离去。不想,那姑娘却是神情大急,出言喊道:“哎!你就这么走啦。”
薛振回头望时,见那姑娘面红唇朱,眼眸含羞,****着一条手臂,白皙的臂膀上印着五个通红的指印。只听那姑娘“哼”地一声,轻言道:“都快把人家的手都捏断了,你得赔。”
薛振看着这五个指印,心下为难,确实是太过用力,嘴上一连声说着对不住,拿起姑娘的手臂道:“我不是故意的,我给你揉一揉,过会便可好些个了。”才揉得一下,又觉完全不对,男女有别,大街上怎能拉着姑娘家的手臂。薛振赶紧又放下,顿时便觉面红过耳,手足无措,两只手掌在衣襟上不停地搓揉,嘴里更是不停地说着“对不住”。
那姑娘低着头“扑哧”一声笑出声来,轻声说道:“公子爷要说多少声对不住啊?”
薛振听到姑娘笑出了声,这才缓过神来,抓抓后脑勺,也憨憨地笑了起来,见姑娘相问,想要说点什么,却鬼使神差的问道:“姑娘,看你也不像是穷苦人家的儿女,为何偷拿店家的馒头?”
“我身无分文,不拿馒头,难道把自己饿死不成。”那姑娘一撅嘴,一脸无辜的回道。
“哦,在下抓伤姑娘的手臂,该当认赔,你看我还忘了这事。”薛振呵呵笑着,掏出一锭银子放在姑娘手里,便即转身离去。
“你……这……”
那姑娘欲言又止,手捏银锭,旋即转眸一笑,见薛振走得远了,便紧走几步跟随在薛振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