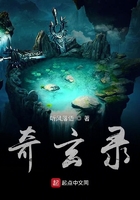这个时刻我等待了7年,期间我想了一千种感情,但唯独没有想到会这么失望。站在家门口,呆呆的杵在那里,脸上的泪再次流了下来。四合院倒是还在,门上的锁锈迹斑斑,门环也一层铜锈。门是古时的那种木门,两个合页,然后上面有两个门环。这个宅子是爷爷住过的,当时门环是用的两个狮子头,应该是镇邪用的。普通人家的门上有环是两个圆圈,大部分是铁的,有钱人家的用铜的。像以前商人或者做官的宅子才会用狮子头或者龙头,这更让我觉得愧对爷爷。想如果我爷爷还在世,凭着他的身份和脑筋,会让我们这个家落的如此荒凉吗?
家门口原本有两个石狮子摆在左右,现在也找不到了,恐怕是叫人给顺走了。去旁边找了块趁手的石头,对着铜锁敲了一下,哗啦一下跌落在地上。双手推开门,随着“吱”的声音,院内的视线出现在我的眼前。高高的杂草,都能达到我的腰部,房间门口的遮雨粱上布满了蜘蛛网,窗户上的纸都有大小不等的窟窿,岂是“荒凉”所能形容的。院子里有一个压水井,是我记忆中玩的最多的“玩具。”我记得当时父亲和邻居们挖井的场景,还记得打出井水的那种甘甜的滋味,我在妈妈的怀里撒娇。压水井大家见过吗?全部都是铁的,就是上水的地方算是个密封圈吧,一个长长的杆子也满是铁锈。我记得走的时候盖上了一个席子,现在却破烂的躺在一边,不知道是风吹走了还是有人动过。压水井我试了一下,我稍微一用力就是“嘎吱嘎吱”的响,估计也坏了。
四合院的样式和老北京城里的差不多,不过和他们的比起来小的多,但也有偏方客厅和卧房的。我拿进来行李,也不多,其实就几件衣服和棉被,还有叔和婶们送的土特产。回来的时候也是秋天,上午摆放了行李,下午去了公社报道,领取了粮票。那个时代,下乡回来的知青都有补助的,根据时间不同有各自的优待。我放下行李就跑到了我以前打工的京剧院,搁现在说离着天桥不远的地方,等我到那里时也傻眼了。原本平房的街道盖起来一座座的小楼,坑坑洼洼的路面也修的更整。
连梨园的房子都没有了,我还去哪里打听师傅们的下落啊。我估摸着旧址,问那些新搬来的户主们,有人知道梨园那些人的去向吗?大家都是摇头摆手,甚至有些人都不愿意搭理我这个胡须满腮的青年,那刻我瘫坐在地上,任寒风吹打我的脸面,只想冷静下来。我在下乡期间唯一挂念的人就是剧院里的大师傅们,现在人去房空,那刻我体会到“孤单”那种撕心裂肺的滋味,苦不堪言。我都不记得我怎么回来的,躺在床上,迷迷糊糊的昏睡了过去...似乎只有在梦境中,陪伴我的父母和师傅们才会出现我的身边,我要的幸福就那么简单。
醒来的时候已是第二天的上午了,头有些晕,似乎有点感冒了,不过还能挺的过去。简单的吃了几个地瓜就去了郊外,看看我家的坟地还是当初的模样吗?赶了一个时辰,远远的望见父母鼓起的坟墓的时候我心里终于舒了一口大气。并作几步赶了过去,跪倒在父亲的坟前,眼前的场景让我更加的心寒。坟前的石头桌子歪倒在旁边,旁边的草不矮于院子里的杂草,爷爷选的地方幸亏偏僻,我真怕别人推平变成了田地。先休整了一番,坟顶也找个土块压在上面,总算有个样子了。之后我又哭哭啼啼的和父母说了这几年的遭遇,希望泉下有知,能原谅儿子的不孝。就在我忙完准备回去的时候,我感觉身后有双眼睛,感觉乖乖的,荒山野岭的不知道干什么的。我想我一穷二白的人,打劫的人见我都得躲着,不用管了,又徒步赶了回去。路上我悲喜交加,感觉这些年的事一言难尽,只能自己憋在心里默默的承受...
到家之后去邻居家串了几个门,认识的人也没有几个了,不是搬走就是去世了,短短的7年到底发生了多少我不知道的事情呢?邻居们几度怀疑我是当年的何三生,也难怪他们了,当初走的时候我算是稚嫩的小生,而现在呢!满脸的胡子,黝黑的皮肤,一口浓厚的山东口音,和北京城的人们显的格格不入。擦了擦桌子,修了修压水井,忙完的时候才感觉腰酸背疼,躺在炕上拿出来那本《点穴风水》,抚摸着它我就有种亲情的安慰,现在想起来我们终于平安的回来了。突然想起来我家的族谱还是柜子后面藏着呢,我也顾不得休息赶紧起身去找了起来。
印象当中的书柜我费了很大的力才能挪开,如今我只用稍微用力就移动到了一边,看来我是长大了。后面的画还挂在那里,我摘了下来卷在了一边,里面的小木盒也安静的躺在那里,应该没有人动过。我赶忙伸手取了出来,掀开盒盖,油皮纸的族谱还是崭新的感觉,我连画都拿到了炕上,想重温下当初的记忆。没等我打开族谱,当我瞟了一眼画的时候,惊讶的张开了嘴巴,情不自禁的“啊”了一声。手里的族谱也掉落在炕上,我的眼睛死死的钉在了画上,什么情况?画中人一直有熟悉的感觉,那满腮的胡子,那浓厚的眉毛,脖子上的那个伤疤,那不就是我吗?不可能啊,为什么我现在的相貌会出现在一张几十年的画上?这也太恐怖了吧....
挺神奇的一件事情,但也非常的恐怖。我现在26岁,这幅画最少是我父亲挂上去的,还不确定这幅画的年龄,但这幅画肯定超过我的年龄。在我没有出生的时候,难道就有人知道我的样子,然后画了一副我的肖像挂在我的家里?第一次看见它的时候在大约十年前,那时候我看见画中人非常的熟悉,但就是想不起来是谁,终于知道原因了。不可能吧,我的样子我自己都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会有什么人能预算出二十多年后的我呢?太离谱了,难道是神仙的安排?难道世界上真的有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吗?
我考虑了半天,唯一的解释就是我和我的爷爷长的很像,这幅画里的人物是我爷爷。家里遗传,子随父母长相相近的人很多,那个时代照相机属于稀罕东西,慈禧老佛爷都没用过几次呢。大部分人物留像都是找画工描绘一副黑白的,或者彩绘的肖像。我爷爷的时候没有这个条件,画了一副自己的肖像想留给我们个纪念,而赶巧的是我和他长的非常相像,以至于我分不清彼此,有些混乱。哎,我想起来了,我在下乡的时候脖子上有过一个烫疤。那时在冬天,大家围着屋里的路子烤火,一群知青又是对诗又是划拳的好不热闹。最后大家闹的比较欢,一块烧的很旺的木炭飞奔我面部而来,我躲闪不及,最后掉在了我的褂子上。
衣服领子因为高温迅速的卷在了一起,火炭也沾在了我的脖子上,等众人合力取下来的时候,我已经疼的昏过去了。最后包了几层纱布养着,等好的时候拆开一看,一条比较长的伤疤留在了脖子上,看起来很是别扭。等以后照镜子的次数多了,我也就习惯了,但是那道疤是很显眼。我在画上细看了一眼,再次让我惊呆,画里的人脖子上的地方竟然也有些彩色,虽然模糊,但看那位置应该是画的我脖子上的伤疤。没那么巧吧,我和我爷爷长的相似,然后我爷爷也曾经被东西烫过?而后留下了和我一个位置的伤疤?这万分之一的可能也没有吧!我此刻需要的是冷静,坐在了坑上,努力的回想一切,思考一切。
半天了,我绞尽脑汁苦思冥想还是不明白这画是为何而来。这次我把画卷了起来,细心的收藏了起来,等以后的时候再说吧。翻开族谱我又看了几遍,家族的名字都是千奇百怪,认起来很是别扭,勉强的记住了几位,最后觉得没意思就放了回去。《点穴风水》我也倒背如流了,和族谱一起包了起来,再次放了青砖的后面。画我没给挂上,而是安放在柜子里面,爬再给老鼠咬了。在家里闲的时间长了反而全身酸疼,,我准备出去谋份差事,掩上了门就奔着市区走去。门我没有上锁,也没有锁用了,那个锈的不成样子,早叫我一石头给砸了。不过我想家里都已经这样了,不会有哪个没长眼的贼挂念了吧。我也放心的走了,也遇到了一位“神人”!
在路上我闲着没事溜达,等我回神抬头一看,已经到了潘家园了。得,打小我就没来过,现在看爷爷的书里面也屡次提起过这里,今天就进来看看吧!这里有些乱,也可以说是非常热闹,路边都是古玩店,路上也都是摆地摊的,原本能跑汽车的公路现在骑个自行车都费劲。似乎这里寸土是金,凡是有空地的地方都有摊位占住了,熙熙攘攘的,争吵声此起彼伏。没等我迈开几步,一个尖嘴猴腮的人就跑到我的面前,从怀里小心翼翼的掏出一个白玉的印章,问我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