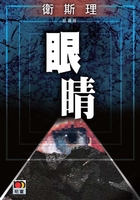呷萨活佛今年整整85岁了。还是第四十九代更达土司在位的时候(这是他的亲表侄。如果丢开佛位不说,四十九代土司应当称呼呷萨为姑父。)他已经被接进更达寺了。12岁,到扎什伦布寺扎什伦布寺——在后藏日喀则。学经。从这时起,在七十多年漫长的岁月中,在孤单的平淡无奇的生活磨炼中,使他除了经文之外对于一切一切都失掉了需要的感觉。他并且发现,经文不只能使自己真切地识见神明,详尽地了解西藏古史,而且,其中也确乎有很多是对于世人大有益处的学问。比如,他就不知反复多少遍研究过“墨纳”“墨纳”一一药神经。和“泽珠”“泽珠”——延寿经。。他常常在自己左腕上试验诊脉,甚至在山里收集过许多种什么草根、木皮。也托人到印度去购买过什么珠宝粉末。当然,在人们看来这是大可不必的。因为,他身上就有许多除魔治病的灵丹,如头发、指甲等等。人们得到这些,都会如获至宝,情愿付出极高贵的代价。但是,呷萨活佛还是专心一意,不知疲倦地诵读和研究“墨纳”“泽珠”。虽然由于慎重,他还没有用自己的配方医治过一个病人,但他越来越相信自己会成为一个手到病去的“门巴”门巴——医生。。
不过,近几月来,呷萨活佛对自己的埋头钻研是否具有什么重大意义产生了不可克服的疑问。工委会在农业站旁边开办了一个卫生院。这个免费诊疗院的一切设备,都还处于临时性的简陋不堪的状态。从院部到病室,只占有5个帆布帐篷和一所当地人的两层土房。内外科只有3个大夫和5个女护士。而应诊的人却日夜川流不息——由于饥饱不定而消化不良者,身受刀伤的械斗者,难产的妇人,眼圈肿烂的烧火娃子,沾染淋病的青年商人等等——但,卫生院好像没有怎么费力就使所有这些人得到了万分满意的救治,以致使他们牵着整头的羊子前往敬谢。当然,这也并没有降低寺庙的威望。因为,当病人们在庆幸自己痊愈的时候,不能不首先感激寺庙打卦的准确性——山民们无论采取什么方式医治自己的疾病,总要先去求卦。实际上,等于在寺庙里挂号而到卫生院去治病。这种情势,呷萨活佛了解得很清楚。作为神明,最重要的应当是诚实;他不愿意欺瞒别人,更不愿意欺瞒自己。所以,最近他对任何一个求卦者的回答总是不假思索的,千篇一律的——到卫生院去治。
当呷萨活佛刻苦地、然而却是陶醉地开始诵读第一经文的时候,他仿佛觉得自己已经步人无人相扰的、幽静而奇特的境地。他甚至完全忘掉了自己的存在。但,突然间一阵女人的笑声惊动了他。他立刻重新意识到自己仍旧没有脱离这可厌的、很可厌的人世。
活佛诵经的平台背后,正冲着俄马登登家的林卡林卡——公园之意。。每天傍晚,涅巴的妻子们像犯人放风似的,在这范围不大的围墙以内闲散。她们既不歌,也不舞。而且,彼此之间也很少答话。只是无所事事地来回走走。其实,这不过是多年来所养成的一种习惯而已。她们对林卡没有任何兴趣。这里只有两排长得枝枝杈杈的宽叶柳,几盆白菊虽然置放在玻璃顶温室里,但却早已枯萎了。
俄马登登的妻子当中,最年长的一个和他同岁,49。最年少的一个比他的女儿茨顿伊贞小两岁。而所有的妻子们,不管谁,论起容貌全赶不上茨顿伊贞。也许这和穿着很有些关系吧!她们当中,有的是根本懒于装扮的。有的则头上堆满了金银首饰,胸前挂满了珍珠项圈,连衣钮儿也都用了碧玉宝石,而且又尽力挑选各种鲜艳的绸缎来给自己制作衣裙,看起来,刺目耀眼,极不协调。茨顿伊贞却与众不同。她很懂得,服饰悦目不在于华丽而全在色质的素静和雅致。就看她现在穿着的一身吧!像羽纱一样薄薄的宽袖衬衫是鸭蛋青色。罩在上面的紧身绒坎肩是墨绿色料。而直遮到脚面的长裙,还是用鸭蛋青和墨绿两色呢料剪成窄条拼在一起的。系在耳上的四五勺长的耳坠,也是用淡色芙蓉石镶嵌的。她不梳成几十根细辫拖到腰间,而是用一个像牙发夹把乌黑的长发收成一束,散披在肩后。这样,就使她的头部和面孔显出一种特别娇嫩的媚态。并且,她对于香粉、口红的应用,也不像别人那样过分,能够做到适可而止。
刚才一阵笑声,就是茨顿伊贞发出的:她由侧门出来,走进林卡,便瞧见了察柯多吉“相子”相子——一种职位。低于涅巴,专门经管财务。。他正坐在高出围墙的石台上,向远处,更确切地说是向正有一头铁狮在奔驰着的草原上了望着,凝视着。她蹑手蹑脚走上石台,撩起长裙,猛然蒙住了他的脑袋。他霍地往起一站,把她扯带得仰面朝天栽倒了,他随即又俯下身去,在她的脖子里搔痒。于是她尖声地格格大笑起来,像一条刚放进煎锅里的活鱼一样在地下翻滚着。这时候,一个佣人规规矩矩立在台阶上禀报说:
“来了一个骑马的人,说是给相子送信的!”
茨顿伊贞不耐烦地说:“你把信要过来,放到相子屋里去不就完了?”
“不行!他说一定要当面见相子。”佣人莫可奈何地说。
“一个骑马人?”察柯多吉思索了一下,忽然省悟道,“唔!唔!不!不要!我屋子的门锁了,我就去!就去!”他说着,撒开茨顿伊贞的手。显然因为过于性急,噗通一声,跳下了台阶,匆匆忙忙跑走了。
呷萨活佛窥视着这一切,心中又涌起一阵嫌恶之感,他从来就不喜欢察柯多吉。虽然,这个未曾上年纪的人,相貌堂堂,举止文雅,对人又是一味地和气可亲,但呷萨活佛还是不喜欢他,简直可以说十分嫉恨他。这主要是由于他破坏了历代常规,而在更达家取得了相子的地位。这是绝不能容忍的!相子,应当由世袭的贵人当中选定。而他是什么人呢?认真说,他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浪荡汉。要是有家,为什么他到这里来已经4年了从来也没有提起要回家!由于这,呷萨活佛不仅不喜欢察柯多吉,甚至对他不信任起来。他为什么竟会那样有钱呢?初来的时候,他毫不吝惜地献给寺庙成包的黄金,送给土司和涅巴成箱子的白洋。一个无依无靠的单身人,如果不去打家劫舍,绝不会如此富有的呀!但呷萨马上就对自己解释得明明白白的了。并且,他不得不暗自钦佩察柯多吉的精明才干。听说从前他曾在一个大喇嘛寺里做过“会手”会手——专管生意、帐目的人。,现在,他带领一支五六匹马的商队,去山里山外收销大宗的虫草、麝香和鹿茸。而看起来却还轻松得很呢!随即,呷萨活佛把他的满腔厌恶一转而至俄马登登身上去了。他对这位涅巴早已有一种固定的印像,觉得他活在人世不为别的,只是为了储积一箱一箱雪白的银圆。如果能够的话,他甚至会把神都出卖掉去换银圆呢!为什么,察柯多吉来了不久他就百折不挠地在格桑拉姆面前推举他做相子?为什么呢!连娃子们也没有一个不知道,俄马大涅巴和外来的相子合伙经营生意呢!不过,他只管按期提取红利,不曾在资金当中加进过自己的一个小铜子儿。
天色已经暗得看不清字了,呷萨活佛合起经本准备回屋去,心里仍然在气愤着俄马登登。没想到俄马登登正立在他身后。
俄马登登已经在呷萨身后站了很久。他不声不响,像发现了奇迹似的,出神地注视着捧在活佛双手上的经文。一定是什么突如其来的念头在激荡他,竟使他忘掉礼节,抢先说话了:
“唔!经书已经旧成这样了!”他感叹道,“瞧!你瞧,这几张全都破了呢!”
“是啊!”活佛冷冷地说,“旧了,也破了!”
“重印吧!印新的。”
“重印!钱呢?”
“钱?花吧!横竖这样的经文不重印是不行的!”
“不!”活佛仍旧淡漠地说,“要印,不只我这里的240部,全更达,大大小小17个寺庙,各庙子里都有几百本经,都旧了,都破了!”
“那就全都重印啊!”俄马登登用慷慨的态度说,“有多少本旧的就印多少本新的。好吧!这桩事我亲自来办理。印!要印!”
虽然,在活佛面前是绝不敢空有允诺的,但呷萨依然不对这件事抱什么认真的希望。所以,他未做任何表示,便慢步向佛殿走去。这并没有使俄马登登扫兴。相反,当这件为神效力的事情一经决定之后,他显然是异常轻快的。
“唉!看看吧!这成什么话!”涅巴继续感叹说,“经本全都旧了,破了!可是没有人照料!”
当他走到楼梯口时,才恍然大悟自己原是为女土司打卦来的。于是急忙转身回去,详尽地对活佛叙述了格桑拉姆的病症。不过,他一面说,一面已经替对方预备好了这一卦的答案——到卫生院去!
但,全然出乎所料。活佛耐心地听完了求卦呈词之后,一言未发,只是叹息了一声,轻轻摇着头,便回身向佛殿妁角落里隐去了。这使俄马登登感觉到,他仿佛在说:
“她的病,神明也无能为力!”
3
“伶俐的布谷啊!
除了你,再也没有我心爱的鸟。
如果你不相信我说的话,
就请飞遍那高高低低的石崖,
在崖顶上你偷偷去听,
是真是假你自会知道!
威武的骑手啊!
除了你,再也没有我心爱的人。
如果你不相信我说的话,
就请走遍那大大小小的村庄,
在村子里你细细去问,
是真是假你自会知道!”
姑娘们唱着。天一黑,他们就带着黄昏的醉意唱了起来。
但,今晚她们忽然离开坝子,迁移到朱汉才和叶海住的土窑门旁去了。那一块高低不平的场子实在过于窄小,对于十多人来说,舞步是展不开的。不过,姑娘们还是迁移到这里来了。
每支歌差不多总是由秋枝引头的。可是,当大家随起应和的时候,她便不再作声了,好像是在对大家指名她要听哪一支歌子。她轻轻摇动着身子,踏着琐碎的舞步,而通过人们肩头的空隙向朱汉才、叶海的土窑凝望着。往常,在黑夜,总是可以从自家屋顶上远远望见这个小小的透亮的窗户。现在,月亮刚上来,为什么窗户已经黑洞洞了呢?该睡了!他们驾着“狮子”劳累了整整一天,该睡了。不!他们一定没有睡。许是吹灭蜡烛,坐在黑黑的土窑里听着呢!他们在听呀!她于是骤然唱起来,嘹亮动听的嗓音突出在众人之上,宛如一股格外清澈洁净的泉水,虽已流人大河,却没有被混淆和淹没。
其实,那个土窑中空无一人。
农业站主要人员都被召集到站长家里去了。因为这口窑比较宽畅,便义不容辞,兼做了会议室。而李月湘,也就自然而然地担当了招待之责。她给每个人倒了水,便扭身坐到最背的角落去,一面编织毛衣,一面用显然属于局外人的态度在倾听人们发言。
因为大家都有不移的主见,而且,都在焦躁地三番五次地重申自己的理由,所以,会议的秩序——大家没有注意。
“喂!喂!不要嚷!不要嚷啊!”陈子璜抬起双手不停地从空中向下按捺,“这是开会,不是赶集!一个说了一个再说嘛,反正谁都有发言权!好吧!现在……”他忽然觉得完全不需要再作什么争执,他脑子里已经有了断然的结论,所以,没有给别人留下一点插嘴的空隙,就紧接上说,“现在,大家也都很清楚,四外这些庄子的人,都开始看中了步犁,都想要我们用步犁去替他们耕地。往后只怕更会忙得叫苦连天呢!可我自己很高兴,我想,大家心里也一定觉得很畅快。不过我也真有点犯愁。我们一共30部七寸犁,可是,能抽出手来去掌犁的,就光是生产队的人,还不到20个。这怎么能行呢?无论如何是不行的。我看哪!就这么办吧!全体!我自个当然也不例外。从明天起,每人一部犁,哪个庄子要,就到哪个庄子去。有求必应!我想,用不着我多絮叨。明摆着的事,非这样不可!这是首要任务;至于别的,就先缓缓,以后再说吧!像机耕工作、畜牧工作、气象工作,还有,农业技术员的……”
“对!站长的意见我赞成!”
“不同意!我不同意!”
“也只有这么办!反正人就是这么多。你不……”
“报告!我反对!”雷文竹刷地站了起来,“说得难听些。这有点像赶羊。我认为,绝不能因为某一项工作重要,就不分男女老幼一拥而上。凡事总应当照前顾后。比方说,我,我不能老像前两天那样,整天到地里去掌犁。我需要,我迫切需要考虑实验地的试种区划,考虑施肥计划。比方说,朱汉才和叶海,除非拖拉机需要加水之外,根本不能停手的。想想看!农业站没有自己的大田,连块实验地也没有,凭什么去指导人家?再比方说,林媛的事,这是不消说的,怎么可以搁起来呢?气象工作啊!至于畜牧技师,同样的,我想,她……”雷文竹忽然截住了自己的话,迅速向和他相距不远的倪慧聪望了一眼,“当然,她可以表示一下自己的意见。不过,据我想,畜牧方面有很多工作也同样是非常紧迫的……”
倪慧聪是唯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发言的人。她坐在靠墙的矮凳上,仰着脸,凝望着雷文竹,倾听着他的议论。从她那在灯光下闪烁的眼睛里,雷文竹看出了被掩饰着的微微的激动和显明的赞同、信赖。他脑子里立刻映过一个对自己很满意的念头。
从各处,七嘴八舌向雷文竹提出了疑问、质问:
“就这么各顾各?只管自己的事?”
“应当服从首要任务啊!要不,光让我们生产队这几个人去掌犁,那……”
“要知道,人手不够啊!”
“正是因为人手不够才不能那么硬拼!”农业技术员觉得他已经得到有力的支持,更加从容地反斥道,“同志们明白,我们又不是来给本地人打短工的,怎么能挨户上门去替人耕地呢?好吧!就算能够这么做,那充其量也只能使出去30部犁呗!30部犁又挡什么事?我提议,”他差不多完全冲着站长说,“由生产队负责,到各庄去开办农具训练班。先把种地有经验的人找来,或者是请来,就在田里套上牲口当场教。然后,他们自然会转教别人。步犁可以统统出借,不够的话,号召各庄子凑钱,我们代购。”
这意见,立刻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热烈拥护,有两位事后高明的人还互相表白说:
“我早就有这种想法!”
“刚才我就打算要这么发言的!”
不过也有人在摇头,他们坚持着相反的意见。
“这么想想当然是不错!”
“西藏人,哼哼!只怕不是那么容易学会哟!”
陈子璜开始摇摆在这两种意见之中了,因为,他在会议上往往比较冷静,而当他冷静的时候往往是拿不定主意的。
正在这时,从门外传来一阵马蹄声,随即,号角“呜呜——”地开始在山谷的夜空里嘶鸣起来。
这号角,会场上的每个人都很了解。用当地人的话说,这是从“上边”下来了“哼查”“哼查”——下属之意。担任送信、传达令旨等事。,有要事前来沿庄吩咐。他在马背上吹过一阵号角之后,便会扯起吓人的嗓门开始大呼小叫。所以大家不再作声,想要听个究竟。
这号角,像快刀一样斩断了姑娘们的歌声。同时,除去完全耳聋的老人之外,庄子上所有的人,也都立刻停止了手头的活计,从窗口探出头来,带着惶恐不安的、等候宣判的神情,在倾听那简短的不容回话的通告。
月亮被忽然涌来的浓重的乌云所吞没,夜更深更暗了。
陈子璜抱着发冷的膀子,依在门框上,一面呆呆地望着全然望不见的草原,一面想起林媛上午送来的气象预报——明日拂晓,暴风雨。
李月湘不声不响把黄呢军用大衣拿给丈夫,便系起短短的北方女人的围腰,开始在火台边忙碌起来。陈子璜从地里回来太晚,一到家,人们已经陆续到会了,因此他没有来得及吃晚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