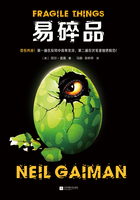“这不怕,你也可以做团员哪!”叶海释然地说。
“我?怕是不行吧!”
“怎么不行!”叶海站在对方的地位上信心十足地说。
“真的?”秋枝兴奋异常地问,“你真觉得我能行?”
“真的。能行!可是你知道不知道应当怎么样才算一个真正的团员?”叶海反问。
“这我知道!”
“知道?你说给我听听。”
“就像倪慧聪姐姐那样!”秋枝简短而中肯地回答。
“对!就像那样。不过,既然要做团员了,往后不要总是姐姐、姐姐的,应当称同志!”叶海严肃地说。
“喊姐姐不好吗?那我以后就喊同志。”秋枝说着,把垂在肩头的发辫扔在背后,随即又投靠在叶海的胸前,然后仰起脸来说,“叶海,你等我吧!过一些时候,我一定能当团员。我一做了团员就嫁给你,你等我,可好?”
“好!”叶海用力拥抱住她,“我等你!”
9
在田间劳累了一天,晚上又蹦闹了一夜,人们已经声哑力竭,一个个回到窑洞便跌入了梦境。
马车队长糜复生无论如何睡不着,虽然他努力合住眼,避开从窗格上透进来的雪亮的月光。这是由于酒的关系,不过,这并不是说他喝醉了,只是因为他喝得“差不多”了。酒徒们有这种体验:喝得“差不多”的人总是精神旺盛,并且会产生一种异常强烈的讲话的欲望。糜复生便是如此,现在他渴望有人跟他说笑。更主要的。他渴望能够说话,说什么都行,只要能说,滔滔不绝地说。可是跟谁说呢?队员们都呼噜呼噜地睡“死”了。于是,一种莫名其妙的烦恼紧紧抓住了糜复生。他仿佛觉得自己的手脚被绑起来了,并且他此刻是被抛在一间窄小闷热的牢房里。他觉得窑洞的土顶沉沉地压在他的胸口。他猛然撩开身上的棉被和大衣,但还是感到憋得难受,好像心中有一团火在燃烧,顺着喉咙冲上来,窒闷着他的呼吸。他想灌些冷水,把这团火扑灭。于是他霍然翻身站了起来——当他站起的时候,几乎栽倒在墙角里——他摸出窑洞,勉强保持住身体的平衡,向厨房走去。他用木瓢舀起一瓢冷水,可是忽然记起,醉酒的人喝冷水,肺就要炸的,他没有喝水,把木瓢扔在地下,走了出来。到哪里去呢?回窑洞去。不!他再也不愿意回到那间闷热的“牢房”里去了。他想在外边走走,因为寒冷的夜风对他很合适。可是,走起来感到吃力,于是,他想靠住停在窑门口的一辆马车,半躺半立地歪下去歇一会。但,当他意识到面前是一辆马车时,心中的烦恼骤然加剧起来,并且越发明确起来了。马车!马车!他用鼻孔哼了一下,又在胶皮轮上踢了一脚。我是什么人?马车队长,哼!听吧!多了不起,队长!实在一点说,赶车的!吆牲口的。可是,这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这样捉弄我呢?他愤愤不平起来。觉得满腹怨气无处发泄。糜复生想,到现在,他无论如何也不应当是一个吆牲口的,无论如何也不应当落到这步田地。
当站长陈子璜正式把5部马车交托给他时,糜复生心中涌上一阵自卑的绝望的感觉。仿佛他正在向高处爬去,突然间脚下的梯子折断了,把他从空中抛了下去,一直坠人深渊。他感到凄然无望,不可自救。他觉得事实上他已经不存在了,变成了一个空壳,一个再不能够产生任何欲念的、将完全被人们所遗忘的什么东西
何以至此呢?用糜复生的话来说:“怎么栽了这么大斤斗呢?”这全是因为女人!假如那个副官的女人不多嘴,一切不堪回首的事都不会发生的。女人!女人!糜复生痛恨地想。现在,女人这个概念在他意识中只是祸害的根源,以至于他忆及那副官老婆结实的富有弹性的身体时,都感到一阵厌恶。
正在这时,忽然有人在唤糜复生的名字,声音是轻微的,不太真切,像梦中常听到的。糜复生烦恼的回忆中断了。他用心辨别这声音,是一个女人在低低呼唤他。他立刻想要发作,因为这是女人。可是,他没有发作。这不是别人在唤他,是蛛玛。不过他也并没有应声,仿佛根本没有听见。
“糜复生!”蛛玛从她自己的窑洞里探出上身来,连声不断地呼唤,“糜复生,糜复生队长!”
“做什么!”糜复生终于回答了,闷声闷气。
“怎么黑天半夜在外边呆着?这么大的风!”蛛玛体贴地说,“到我棚子里来坐坐吧!”
“不!这儿很好。”
“要是不来坐……”蛛玛停了停说,“你来把你的衬衫拿回去吧,还有袜子。我都洗好了!来拿走吧……来呀!糜复生!你来呀!”
现在,蛛玛那里并没有糜复生的什么衬衫和袜子,这一点糜复生很明白。虽然他此刻的头脑不是百分之百地清醒,但他仍记得,前天她拿走一件衬衫和一双布袜去洗,昨天下午已经晒干送还了他。但,他却没有作什么说明,身子摇晃了几下,从马车上爬起来,向蛛玛的土窑走去,仿佛他也感到有取回自己衬衫和袜子的必要。在门口,糜复生忘了低头,额头被狠狠地碰了一下,不过他也并没有觉着痛,一猫腰推门进去了。
“你等等,我来给你找。”
蛛玛半仰半卧地倒在铺上,开始在一堆洗晒过的衣物中翻寻。油灯放在铺头一个木垫上,灯光正照着她姣美的脸,照着因为胸襟斜散而裸露着的白净丰满的颈项。蓬松的长发由肩头拖下,直拖到铺草上。显然,她没有想从哪一堆衣物中找到什么,只是懒散地一遍又一遍翻寻着。现在,蛛玛开始紧张,并且是恐怖起来了,因为她在翻寻衣物时发觉,或者说是感觉到了,站在铺边的糜复生是用那样饥饿的、可怕的目光在凝视着她。忽然,糜复生一抬脚,将油灯踢翻。接着,蛛玛在昏暗中看见糜复生倒扑下来……由于胸部受到沉重的挤压,她顿时感到无法呼吸了。应该说,这对她不完全是意外。然而,少女的防卫的本能使她立即展开了凶猛的反抗。但,随即她觉得自己的身子无力了,瘫软了。于是,她放弃了所有抗争的手段,失去了最后的一点主动……
糜复生从蛛玛的土窑里出来,一时弄不清要往哪里去。过后他才想起来应当回家了,于是他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向马车队寝室走去。当他刚到门口时,正巧遇见了从旁边走来的朱汉才。
“老糜!你看见叶海了没有?”朱汉才问。
“谁?叶海,唔!”糜复生扭回头,以突然的、兴高采烈的语调说,“看见了!看见了!”
“在哪儿?我得找他回来,该休息了,明天一早还得下地呢!”
“在林子里。”糜复生向远处指指,但随着又意味深长地说,“不过,该休息你就休息你自己的吧!不用找他,找也没用。我想,只要他还有一小点力气,他是不会回来休息的。”
“怎么?”朱汉才不解。
“傻瓜!他不是一个人在林子里,是两人!你没见?晚会一散场,秋枝扯住叶海的袖子就跑,跑到林子里去了。”
“唔!”朱汉才微微一笑,“好的!我就先休息吧!”说着便要转身走去。
“你不去找他了?”糜复生问。
“不找了!让他玩吧!今天是过节呀!明早上我先起来发动机子,让他多睡一阵儿就行了!”
“去吧!你还是找去吧!就在林子里,很容易找到。”糜复生凑近朱汉才,压低了声音醉洋洋地说,“讲实在的,老斯朗翁堆的那个姑娘可不坏呀!”
“你这是什么话!”朱汉才骤然严厉起来,“酒坛子,你又喝多了!”
“怎么什么话?”糜复生认真辩解说,“一开头,秋枝也不是单找叶海一个人的呀!也有你。没说的,你也去吧!都有份儿!”他说着,裂开嘴笑了起来,笑着又接二连三打了几个喷嚏。
“住嘴!”朱汉才喝道,“你哪点儿像一个人!是一只狗!一只公狗!”
“公狗?呵哈!不错!公狗!”糜复生显然由于挨骂也突然气恼了,“不过公狗也没有那么蠢,它总还知道找母狗去呢!可你……当然喽!你不喜欢占别人便宜,这很好。可这算得了什么!你当是叶海真心想娶一个藏姑娘做老婆吗?我看不见得。他不过暂且……”
糜复生正还要说下去,没防备一记重重的、响亮的耳光已经落在脸上。
“怎么?打人哪!”马车队长应声用双手捂住热辣辣的左颊,得理地说,“还是党员呢!开口骂人,动手打人。没见过你这样的党员!”
“没见过!我这就叫你见一见!”朱汉才说着便到马车跟前去抓一根木棒。
糜复生虽然个头高大,但他自知对付这个极端愤怒了的拖拉机手是有困难的。同时,经受了朱汉才的巴掌光顾,他忽然醒悟到自己的话也未免过于缺乏保留了。于是,他一边推门钻进土窑,一边咕噜道:
“打人,好吧!咱们明天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