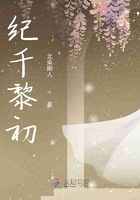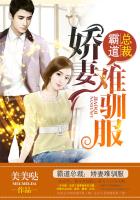打上最后一个句号,清华园已是冬去春来,春回大地。追寻中华民族消逝在远古的童年时光,文字的流淌与内心的波涛互为激荡。不知不觉,我已是热泪盈眶。这本书十易其稿,倾注了我多年对中华文化的研究和四年多假期特别是春节假期的艰辛笔耕。尽管才四十出头,但已是满头白发。
我自幼喜欢读历史,“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中国从20世纪初的百年变迁在我普通家庭中得到映衬。我的祖辈来自山东,“一闯关东”,首先来到辽宁,康熙皇帝允许满汉通婚,我爷爷家是汉族,奶奶家是满族正蓝旗。后来爷爷奶奶从辽宁“二闯关东”,来到哈尔滨,父亲出生在哈尔滨。可爷爷被日本侵略军抓去当劳工,屈死在劳工营里,给家庭带来沉重灾难。父母是新中国成立后读的书,20世纪60年代初的大学生,在毕业前两年“**********”爆发了,毕业后参加了西北的“三线建设”直到退休。我出生在宁夏贺兰山脚下,成长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求学于东南大学和清华大学。1995年末出国的时候就想有朝一日学成回来建设祖国,于是就抓紧时间看世界。在英国苦读5年,在美国工作5年,其间去过欧洲、拉丁美洲、非洲、东亚的一些国家。2003年中央实施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2005年我又回到当年爷爷奶奶闯关东的终点哈尔滨,为东北振兴做一点儿力所能及的工作,2010年到人民银行工作,做了一名光荣的央行人。“闯关东”、“满汉通婚”、日本入侵、新中国建立、“**********”、“三线建设”、改革开放、东北振兴和人民币国际化这些重大历史事件都在中国一个普通家庭史上起了决定性作用。个人小时代从属于他的大时代,与民族的前途命运休戚与共,谁也不能超脱。
作为一名经济工作者,并且出生在这个历史上最好的年代,我感到十分幸运。中华民族伟大经济复兴的机遇是千年等一回。经济复兴已经进入中后期,文化复兴的端倪已露。
生长在文化断层中的我,冒失闯入文化领域,是完全没有想到的。读钱穆的《中华文化史导论》一书,深刻地感受到钱穆对于中华文化的自信,对中国历史的“温情与敬意”。为了返古开新,着名文化学者孙皓晖就从中国古老的原生文明着手,历时十六年创作惶惶巨着《大秦帝国》。1993年秋天,孙皓晖动笔写《大秦帝国》。1998年春天,孙皓晖带着妻子,在海口一个僻静的小区居住下来。2008年春天,当孙皓晖敲下小说《大秦帝国》的最后一个句号时,他满头黑发已经灰白。从43岁到59岁,他人生中最美好、最年富力强的16年,都义无反顾地献给了《大秦帝国》。2012年伊始,他又完成《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越过两千年,对接中华文明青春期。孙皓晖的故事让我想起一句话,“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在人民银行文联的鼓励和指导下,我努力学习文化前辈们的崇高品质,在平时工作非常繁忙之余,利用几乎所有休假,将勤奋程度发挥到了个人极限,虽银发满头仍踯躅前行,努力返古开新。历时近四年,才有今天奉献给读者的拙书。
一个人生命中最大的幸运,是能得到诸多老师指导和朋友们的鼓励,才有毅力在快四十岁时才开始对“梅花与牡丹”的领悟做进一步深入研究,于是不经意碰上人类学。通过与师友反复讨论,感觉梅花与牡丹不仅仅可能代表民族精神,而且可能成为人类社会的时代精神。我提出中国史前史新框架,包括同源变异说的中华文明起源新说,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经济学的理论及对中华文化的合理推论,也有一定程度的想象。我的责任感,大于我对自身被“拍砖”的担心。但我所做的,不过是精卫所衔的一枝微木。我真诚期待考古学界和人类学家对我这个临时跨界的经济学工作者批评指正。
“梅花与牡丹”为我们理解中华文化提供了一个起点和路标。换句话说,是“开胃菜”,然而,起点、方向标与地图自身并不是中华文化,不是“主菜”。换句话说,“梅花与牡丹”可以用于理解与解释中华文化的一些深层次性问题,但由于这种理解与解释的视角具有超越历史与地域的特征,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就此可以理解中华文化。要深入理解现代中华文化,读者还要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
我也关心身后的评价,在意中国慎终追远的传统。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我的中国梦就是做一只经济复兴的小蜜蜂和文化复兴的萤火虫。如果我能获得“他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家和文化学者”这一句话互联网墓志铭,则心满意足了。
我要感谢我的家人,妻子王佳平和女儿姚庆蕾。妻子和女儿无条件支持是我度过每一个艰苦创作之夜的不竭动力。前人民银行文联主席初本德和现任人民银行文联主席张汉平阅读了每一个初稿,提出了宝贵的修改建议。感谢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50人论坛的大力支持与帮助,特别感谢洪崎理事长和贾康院长的悉心指导。感谢人民银行宁波中心支行行长、人民银行文联副主席宋汉光为本书题字,感谢人民银行文联理事、莆田市中心支行洪祖杰行长倾情做画。
本书蒙张汉平,戴兵,王广宇,魏革军,黄剑辉赐序,深表谢意。多位书友特别是宋立洪、谭海鸣、陆杨、王翔、赵宪刚、王晨、张艺、孙大海、李波、潘晓江、路约兵、刘洁等的帮助审改,刘丰、赵炳阳和姚余梁都仔细阅读了每一稿,给我很多重要的修改意见。感谢给予评论的朋友:宋军,郑五福,王庆,孙鹏,陈晓伟,马续田,蒋国荣,谢继军,白伟群,王道南,李波,楚艳,彭子瑄,张继中,鞠瑾,周健男,林竹,白秋晨,龚牧龙,邝霞,黄黎明,楚云舒,李达,王晨,沈丽,肖冬雪,李白云。我感谢金融出版社魏革军社长和张蕾编辑,金融时报王沪鸣书记和唐小慧首席记者,蓝狮子吴晓波老师和王留全主编的鼓励。蓝狮子的康晓明副主编是位有文化底蕴的严谨编辑,为此书付梓做了大量工作。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