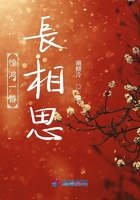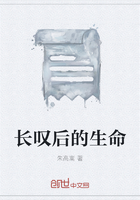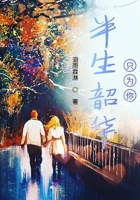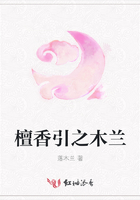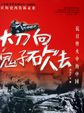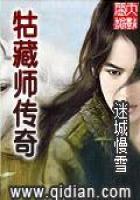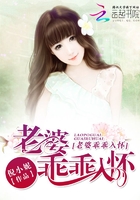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土地,大致可以算作1000万平方公里。根据宾福德的研究,在植物采集时代,每100平方公里大约可以承担10个人,也即约10平方公里承担1人生活。不过,虽然远古中国很多地方的生态植被条件要远远好于现在,但仍有很多沙漠、荒原等不毛之地,因此,在采集时代,乐观估计中国的总人口最多约有100万,而实际上应该比这个数字更低,比如50万人。
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是以氏族方式存在的。离开了群体,离开了适合生存的环境,就意味着死亡。对狩猎采集者的群体而言,人类学家发现一个魔术数字,即一般来说,每个群体的人数在25个人到50个人左右,大约由4~6个家庭组成。
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种姓”(Gene)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都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要使“种姓”得到优质的繁衍,生育行为以及相关的制度成为首要影响因素。在人类学角度,除个别制度外,婚姻制度成为种姓繁衍的普遍形式。姓氏一个重要文化功能是避免氏族内通婚。在这一时期,萌芽了姓、氏。据《说文解字》,人们的姓是标志所由出生的血缘关系,这种血缘关系最初是从女性来确定的。所以,一些出现较早的姓,如姬、姜、嬴等等,大都从女。这正是母系氏族的痕迹。
中国共有多少姓氏?大约20000个左右。现代人编着的《中国姓氏大全》录姓氏5720多个,《中国姓氏汇编》收录5730个,《中国姓符》收录6363个,《姓氏辞典》收录8000多个,《中华姓氏大辞典》收入11969个,《中华古今姓氏大辞典》收录12000多个。由于姓氏本身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任何一种姓氏书都无法也不可能毫无遗漏地把我国所有的姓氏都收录进去。据专家估计,我国实际使用过的姓氏大约有20000个。四川省遂宁市档案馆职工陈历甫花了30年自费到各地收集的,约19989个。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袁义达副研究员经过多年的收集和研究,发现中国人古今姓氏已超过22000个。这22000个姓氏包括少数民族的汉译姓氏。比如蒙古族、满族、藏族以及彝族等少数民族的古今姓氏,这4个民族的汉译姓氏,总数至少在4000个以上。
如果按照当时中国可以承载100万人口来算的话,那么当时应该有2万~4万个采集群体,而这恰恰与中国的姓氏数量基本吻合,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华文明是人类唯一的“文明活化石”。中国姓氏数量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在采集经济时代氏族的数量。在每个氏族大约25人到50人的规模假设下,20000个氏族,对应采集经济所能承载的50万~100万人口,是比较合理的。
新石器时期农业经济所承载人口
新石器时代刚刚出现的农业,是刀耕火种阶段的农业。它是在强度采集的基础上,采取点穴种籽、广撒薄收的方式进行的最原始的生产活动。尽管已经比采集经济好得多,新石器时代的人口密度仍然非常低,每平方公里只有约一个人。不过,这符合农业经济比采集经济承载人口多一个数量级的规律。中国大致可以算作1000万平方公里,在新石器发生农业革命的早期,大约能承载1000万人。
农业革命与工业革命爆发一样,是人类文明的转折点。直到大约公元前11000年上一次冰期结束时,各个大陆上的各个族群仍然都是靠狩猎采集为生的人。从公元前11000年到公元1500年,不同大陆的不同发展速度,成为了导致公元1500年时技术、经济和政治差异的原因。虽然澳大利亚土着和美洲印第安人仍然靠狩猎采集为生,但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美洲和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许多地区,己逐步地发展起农业、畜牧、冶金技术和复杂的社会组织。欧亚大陆的一些地区和美洲的一些地区,还独立发明了文字。河南裴李岗文化据今约7000~8000年,处于全新世大暖期的初始阶段,气候温暖湿润。这种优越的环境、资源条件为人口规模的扩展提供了条件。
河南曾是大象的故乡,但被裴李岗人追杀,只好南迁。在人口压力下,从大型动物到小型动物都被逐级吃光,就只好另想办法,最后逼出了农业革命。
从世界范围来看,农业核心区在扩张过程后都出现了人口超过千万的初期国家,如公元前3500年的亚洲西南部、公元前2500年的印度河流域、公元前1500年的中亚美利加洲和公元前1000年的安第斯山脉。欧洲是农业扩散的结果已经有基本共识。新石器革命开始于11000年前的近东,此后独特的文化群体和他们的农业经济开始持续向西迁徙进入欧洲,包括驯化的动植物。但很遗憾,中国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还没有注意到中国农业扩散这个如此重要的问题。
目前我国现存的最早的人口统计数字是记载是《后汉书·郡国志》注引皇甫谧《帝王世纪》,大禹曾经“平水土,分九州,数万民”。所谓“数万民”就是统计人口。“今《禹贡》是也。是以其时九州之地,凡二千四百三十万八千二十四顷,定垦者九百三十万六千二十四顷,不垦者千五百万二千顷。民口千三百五十五万三千九百二十三人”。也就是说,九州之地的人口为1300万人左右。由于历史久远,大禹时代是否有全国性的人口调查,值得怀疑。但是,在没有文字的中国史前时代,由于要周期性治理黄河的原因,对数字可能是非常敏感的。
虽然上述有关人口的统计并不一定十分准确,但我们至少可以认为在农业革命发生后,中国应该有至少1000万的人口,也就是说,农业革命后单位土地承载人口数量至少是采集时代的10倍。事实上,人类进入农业社会后所引发的人口增长速度,可能要远远快于我们的预期。
史前人口大爆炸
在人类学中,把农业革命引发的人口爆炸称为“新石器人口转型”。新石器时代革命确实刺激了人口的增长,并且极大限度地提高了土地的承受能力。在太平洋的岛屿上,某些新石器时代社会每平方英里有30人或更多的人口。但是,北美印第安人部落已知的最大人口密度每平方英里还不足2人。新石器时代的农民应该聚居在稳定的村庄里,城市革命开始了,于是生活条件逐渐得到改善,人口较多地增长了。但人口增长打破了原来的生态平衡,又给生活带来了新的困难。人口的增长使得人均占有的提供生活资源的土地面积相对减少,人们面临着自然生活资源日益短缺的威胁,倒逼农业革命的发生。
偶然性也可以决定历史。在渡过了数万年狩猎采集经济之后,个别地区的人类偶然间在荒野上撒下种子,农业革命爆发了。随着气候变化,植物裸露出来。最初的中国人可能在秦岭或甘肃等地逐渐学会了辨认和培植可食植物,通过定期栽培收获这些植物来养活自己;中国人还学会了饲养家畜,驯化马和猪,不再集体追赶凶猛的猎物。考古发现,陕西蓝田人用简单而粗糙的方法打制石器,捕猎野兽,采集果实、种籽和块茎等为食物。这意味着,中华的祖先不用再过四海为家边走边吃的游牧生活,可以在一些永久性的地点安家落户,并在附近开垦土地种庄稼,过上粗放农耕的生活。同时群居生活开始被家庭所取代,由于父母可以确认自己所生的孩子了,父母投资孩子的预期回报增加了,于是孩子的素质逐渐提高了,人类的人力资本开始积累起来。就在这个时代,人类开始从事农业和畜牧,将植物的果实加以播种,并把野生动物驯服以供食用,人类不再只依赖大自然提供食物,因此其食物来源变得稳定。孟子心满意足地描绘了农耕生活,“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表明当时老百姓“有衣穿,有肉吃和有饭吃”的生活时尚及寿命可以达到“七十”的事实。
然而,由于地理位置差别,各大洲农业革命很不一样。澳大利亚土着和美洲印第安人很不幸运,失去农业革命先机,仍然靠狩猎采集为生,但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美洲和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许多地区,己逐步发展起农业、畜牧、冶金技术和复杂的社会组织。由于欧亚大陆在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和自然界动植物品种属性方面均得天独厚,欧亚大陆的居民通过野生动植物的驯化,较早进入农业经济。
在采集时代,即旧石器时代,我们已经通过推算表明,中国“巨型孤岛”所承载的人口约100万左右,每个族群约25到50人,约有20000个氏族。假设,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某个部落发生了农业技术的飞跃,这样该部落可以承养的人口将是之前的10~20倍,也即一个农业氏族部落将有250~500人。如果当时的平均年龄为30岁,每一代农业人口将翻一番,那么由于人口的增长,原来的部落将无法承载过多的人口,这样就必须再次迁徙。这样,一个部落重新分裂为两个部落。单位部落的人口没变,只是由于农业革命,农业部落开始呈几何级数的扩散。依此推算,如果每个部落有250人,将在16代约480年后,农业人口将达到约820万,再加上原100万的采集人口,也就将达到1000万的规模;如果每个部落有500人,将在15代约450年后,农业人口达到约820万,加上原100万的采集人口,总人口为1000万的规模。也就是说,在发生农业革命后,只需不到500年的时间,人口就可以增长10倍,农业革命所引发的人口爆炸速度要远远快于我们的想象。
当然,上述人口增长是根据马尔萨斯的几何增长速度来估算的,这可能会产生高估的问题。不过,如果人口以每年1%的指数速度增长计算的话,如果每个部落有500人,那么只要992年就将达到1000万;如果每个部落250人,那么也仅须1061年达到1000万,这一速度仅比几何增长速度慢了一倍,但仍然比我们想象得要快得多。由于农业技术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多,事实上每个部落的人口也会增加。如果以每个部落1000人计算的话,那么中国当时至少会有一万个部落,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万邦时代”。
2011年,西南民族大学王建华教授对黄河中下游地区史前人口规模做了系统研究。他分四个大的时代(裴李岗时代、仰韶时代、龙山时代、二里头时代)、每一时代内部又分成不同的期别来进行分析。在研究典型遗址的基础上,首先确定典型县市的地区人口分布密度以及区域内平均的人口分布密度,然后通过地区的总面积,就可以初步统计出各地区的人口规模。王建华估算结果:裴李岗时期河南为11万、陕西为4.5万,两地共15万;仰韶早期河南为24.9万、陕西为30.4万、山东为44.2万;仰韶中期河南为94.2万、陕西为129.3万、山东为44.2万;仰韶晚期河南为107.3万、陕西为48.5万、山东为48.6万。裴李岗时期河南和陕西总人口15万左右,这个数字与我估计的狩猎采集时代全中国总人口100万基本一致,表明仰韶时代人口规模呈现出上升趋势。到了仰韶时代晚期,河南、陕西和山东三地总人口高达200万左右,这基本上比裴李岗时期翻了10倍。龙山早期河南为169.4万、陕西为115.7万、山东为54万;龙山晚期河南为209.4万、陕西为275.5万、山东为161.4万,所以龙山晚期河南、陕西和山东三地总人口竟然多达650万左右!王建华估算与我从国际人类学比较推断的农业时代全中国人口至少1000万的估计基本一致,而且中原地带占当时中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二左右,此人口分布也符合史前耕地面积的分布。根据王建华研究,二里头时代(公元前1900年~公元前1500年,传说中的夏朝)中心区域的偃师市、临汾市和运城市的人口规模为99万人。夏都城可能相当于今天一个100万人口规模的中等城市,是中国第一个大城市。
资料来源:王建华,《黄河中下游地区史前人口研究》,2011年,科学出版社。
农业革命人口增长速度远远快于我们的想象,而这其实与工业革命后,全球人口的迅速增长是一样的道理。在19世纪初,全球仅有约10亿人口,但仅200年的时间,目前全球已达70亿人口。按照目前趋势,世界人口大约于21世纪中期超过90亿,并于21世纪末超过100亿。这样,工业革命人口增长10倍的时间,其实仅花了300年。相比之下,农业革命的500~1000年,应该还算比较合适的速度。
黄河农民的迁徙:风华绝代
农业扩展有两个模式,一个是沿着中心地区不断扩散,一个是其他部落向农业部落学习农业经济带来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