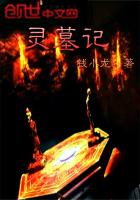那廖夫人却不是那么有眼色的样子,拨拉开李夫人拽她的手,就又神秘兮兮地说道:“相爷夫人啊,咱们可不是背后说大将军的不是,那大将军人品、样貌、才学可是样样都好,挑不出个不是。其实,说到底年岁上也不算个事,上下不差十岁,年岁大些还知道疼人呢。只是过去那事啊,殿下大约是不记得了,可相爷夫人应该记得,那姑娘不还跟您娘家沾亲带故么?当初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没了,到了都不知道是为个什么,一想起这事我这后脊梁可就直泛凉呢。若不是这样,锦荣硬是看上大将军,我怎么也是要帮她争的,可咱们这当娘的心,是疼着姑娘,不想她现在难过,可也怕她日后过的不好不是,谁知这大将军到底是克妻的命,还是有什么……。”廖夫人说到此处,还故意对萧延意眨了眨眼,似是等她问下去。
若是萧延意不曾从唤月嘴里听过魏不争之前的事,此时纵然听人这么说起魏不争会不快,但还是会几分的好奇。可是那不堪的事,她已经听唤月说起过,此时便连那点儿好奇也没有,任那廖夫人说的如何神采飞扬吊着听话人的胃口,她也不理,只当没听见似的,等那廖夫人径自鼓噪完了,她无事人般对着二位夫人清浅一笑道:“茶可是冷了?让人再续上些吧,这月份里还是喝些热的舒服。”
李夫人面上神色些许有些不自然,似是也不知该怎么接廖夫人的话,见萧延意岔开了话,便是赶紧回道:“还温热着呢,正是对口儿,臣妾多谢殿下。”
廖夫人兴致勃勃地起了话头,却是无人理睬,颜面上颇有些无光,便有几分急恼,见那俩人客套完,又赶紧插话进来,“相国夫人,正是说起这个,咱们还真是有点好奇了,当初将军那未过门的媳妇是您娘家的亲戚,想来您总是知道点什么吧?到底是得了什么病没的?”
李夫人皱眉看她一眼,只淡淡接口道:“也说不上什么病,那丫头自小身子骨就弱。”
廖夫人见总算有人理她的话了,眼里闪过一丝兴奋的光彩,便又假意四顾了下,压低声音道:“咱们前一阵子怎么听人说,她……她是难产而亡,一尸两命呢?这可是真的?”
这话一问,不光是萧延意面沉似水,连李夫人也是脸上一黑,匆匆应付道:“说这些不光彩的事干什么,早都过去了,人都没了。你不是来跟公主商量你家女婿的事么?哪就扯出这么多有影没影的。”
廖夫人没理会李夫人语气的不耐,却是抓了话柄兴奋道:“不光彩的事?那这么说是真的了?”
萧延意此时再也耐不住,重重把茶碗墩在桌上,起身道:“二位夫人难得进宫,多坐会儿再回去,只是本宫头有些疼,就不陪着了。”
李夫人自然看出萧延意变了脸色,赶紧起身道:“那公主殿下好生安歇,臣妾等就告退了。”
廖夫人也是慌里慌张站起来,嘴里却絮絮道:“殿下,那赐婚的事还没定呢……。”
萧延意原本便是身上不舒服,人有些烦躁,让那廖夫人这一通闲话说的,心中又有火,此前一直按捺着,这会儿见这廖夫人如此没有眼色,不禁一下子就恼了,忍不住冷笑着奚落道:“夫人原是还惦记着锦荣指婚的事呢?不想再聊会儿将军了?”
廖夫人此前约莫是只顾着自己亢奋着,没留意萧延意的面色,这会儿却是怎么也看出萧延意是生气了,可到底还是个没脑子的人儿,战战兢兢看着萧延意,却还是嗫嚅道:“殿下,其实咱们也是听了将军的一些传言,平日里没机会跟殿下说。今天正好说起来,李夫人知道的又比臣妾多,才是想跟殿下念叨几句。”
萧延意冷冷看着她,问道:“那现在念叨完了?”
廖夫人眼珠咕噜噜一转,瞥了眼李夫人,又看看萧延意,那李夫人眉眼低垂地肃立着却是理也不理她,半晌,她似是下了决心般说道:“还有个事,就是臣妾也做不得准,都是近日听来的,不知殿下听说过没?”
萧延意冷哼了一声,并未说别的,就只盯着她瞧。那廖夫人被萧延意盯的垂下头去,一双手已是绞得通红,嘴里却还是哼哼唧唧地说:“那,还听说将军……吐谷来犯那日……。”说完,抬眼飞快地扫了下萧延意,就又低了头继续道:“那日将军赶回皇城时,说是淑妃娘娘人都没了气息,可几个时辰后却说是诞下了皇儿。偏偏将军未过门的妻子传言那日又恰好难产而亡,难产而亡这事倒是不新鲜,可是谁听说过死人还能生子的?而且,后来伺候将军家未婚妻的所有人死的死,没得没,如今一个也找不见,到底也不知道是不是一尸两命,没准大人没了,孩子却还有,也是未可知的事……殿下,这事您不觉得透着蹊跷么?”
萧延意听着廖夫人云里雾里地说着,所有的事她也都从旁人嘴里听到过,并不觉太意外。她一边对这个饶舌的妇人恨得咬牙切齿,一边却也奇怪,这位尚书夫人为何执意跟自己说起将军这些过往,难道是听悉了她与魏不争之间的情愫,所以赶着说这些来让二人之间生了芥蒂,廖尚书与李景吾关系匪浅,自是他那一党,定然是不希望她亲近了将军。所以偏偏又要翻出将军之前订婚一事说给她听,给她添点堵心。
萧延意本不爱听这些,只是多少还拘着颜面,勉强没有当即拂袖而去,廖夫人说的话却并未仔细听端详,粗略一闻,便知左右不过还是嚼舌魏不争的那点不光彩的往事。
她只皱紧了眉头狠狠瞪着廖夫人,心中想着该如何应对。正是还没想出个对策的时候,李夫人却是用力一拉廖夫人的衣袖拽得廖夫人一个趔趄跟她一起跪倒在了地上,李夫人忙不迭地磕头道:“殿下恕罪,殿下恕罪,廖夫人有口无心,绝无对皇上不敬之意。”
萧延意一怔,“对皇上不敬?”这里如何牵扯了她那小皇弟?
然而,萧延意这疑虑只在心中停了片刻,之前廖夫人所言入耳却未及细想的话在心里一转,电光火石间猛然明白了她在说什么。须臾间萧延意惊得一身冷汗,僵立在当场几乎不能动弹,茫然抬步要往那二人身边去,脚下却是几乎有些不稳,下意识地伸手撑住了一边的桌子,又险些碰翻了桌上的茶碗。
她这时虽是浑身仍有些发软,对廖夫人要表达的事心中惊惧,却也有股火从心头腾地蹿了起来,饶是浑身发冷,脸却涨的火热,一时间有些控制不住地执起一边的茶碗,狠狠往廖夫人身上掼去,声音几乎有些颤抖地吼道:“混账东西,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你这条命是不想要了?廖尚书府上的几十口人,你也是要拉着作陪么?”
茶杯砸在廖夫人的肩头,又滚出去,哗啦碎了一地,一时间,殿内一片死寂。
廖夫人满头满脸的茶水和溅出的茶叶,惊惶而狼狈地看了眼勃然大怒地萧延意,一下子也傻了。
萧延意回朝以后,谁也没见她发过火,人人都说,如今的长公主最是温和可亲,所以她才有那胆子来这里嚼舌,她本不是什么聪明人,自己说了多要命的话她不知道,可萧延意说的话有多严重她可是知道的,这下再也顾不得说什么,只剩下一个劲儿地磕头,哭喊着殿下饶命,一边的李夫人便是也一起跟着磕头。
萧延意气得浑身发颤地走到那俩人跟前,一伸手拽起廖夫人的衣襟,把她拖了起来,咬牙道:“谁教你与本宫说的这些,往日里宫中的闲话是不是也是你传出来的?”
那廖夫人早就傻了,结巴道:“殿下,没……没谁教给臣妾,臣妾也未曾传过什么,只是,这几日里夫人们间偶尔会说起这些……臣妾……。”
廖夫人求救般地看了眼在匐在地上磕头的李夫人,见李夫人只顾磕头根本不管她,便回头又哭道:“殿下,臣妾无心之语啊,只是听夫人们说这些……这些事该让殿下知道才好,臣妾还以为是殿下想知道的。”
萧延意揪着廖夫人的手松了松,对着跪在一边的李夫人喝道:“李夫人,那你给本宫说说,你们之间说这些闲话到底是意欲何为?”
李夫人面色惊恐地抬头,只一个劲儿地摇脑袋道:“殿下,臣妾不知啊……臣妾不曾跟人说过任何陛下的闲话……廖夫人……廖夫人她们也是闲着无事,女人间总爱说些……。”话说到一半大约也知道开脱不了,便是又继续叩头道:“殿下恕罪,臣妾们再也不敢了,求殿下看在臣妾们夫君一直对陛下和朝廷忠心耿耿的份儿上,饶了臣妾们这一次吧。”
“忠心耿耿?”萧延意冷哼道,她这会儿几乎要气疯了,再也顾不得给谁留什么颜面,只厉声骂道:“忠心耿耿到怀疑皇上的身份?你们可真是咱们大宏的好臣子啊!”
萧延意还再要发火的时候,外边有人来报,说是尚悦娘娘来了,萧延意听了点头,对跪在地上那二人冷笑道:“好,本宫正是不知该怎么发落你们,就让姑母来处置吧。”
尚悦来萧延意处本也是从不拘着什么礼,这会儿才通传完,人便已经入了殿,边走边说:“芫芫啊,你下午是就在殿里歇着了吧?那祁老爷子让给你殿里燃些安神的香……。”
尚悦的话说到一半,已经看见跪在地上的二人和气得浑身发抖的萧延意,不禁愣怔住:“你……你们这唱的是哪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