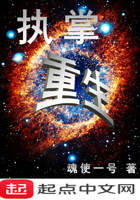天刚一亮,参谋长就将姐姐和我提了出去。“昨天你赢了一招,你很得意是吧?我告诉你,你别高兴得太早了,我这儿有的是人证和物证,有能耐你对簿公堂,你敢不敢?”
“我敢。”
“好,那我就看你的胆子有多大。来呀,传证人。”一句话刚说过,里边走出一个身穿洋车夫号坎的特务。姐姐一眼看出就是在宣武门跟踪我们的那个人。他一进来就呲着牙说:“小姐,您还认识我吗?您没想到我在这儿吧。”
“少费话,说正事。”参谋长说。
“是这样,那天上午我在宣武门里顶班,我正犯愣的时候,忽然看见她带着一个孩子从宣武门里走进来,当时,我一看她鬼鬼祟祟的样就知道她不是个好东西,我就在后边跟。她还挺精,她在西单路口下车混进人群就看不见影了。我当时很着急,她要是跑了我这一趟辛苦就白费了。后来她在西单路口跟一个男的接头的时候又被我看见了。后来她坐上洋车向北走,我就在后边跟踪,快到西四的时候她去了一趟馒头铺,也不知道去干什么。人家理都没理她,她又继续往北走,我继续跟踪她,同时给我的哥们打电话,让他们在西四截着。还真巧,在西四她下了车就往胡同里钻,我们当场就把她抓起来了。我说的都是实情,如有半句瞎话我甘愿受军法处治。”
“好,你说完了我说。当时西单有游行的,车过不去,你大概也看见了,就因为那儿过不去,我才在西单下的车。当时我根本就没跑,我下了车就在人群里看热闹。就在这时候过来一个人,他问我当时是几点,我告诉他是差五分九点,其它的什么也没说。再说我做事从来没背着别人,而你却在后边鬼鬼祟祟地跟踪盯梢,我倒看你像共产党。后来我去了一趟馒头铺,这一点不假。可我去馒头铺是去买馒头,别的什么话也没说,这有什么可疑的你说?我们一早晨还没吃饭难道我买个馒头都不许吗?”
“你胡说。我就不信你是去买馒头,这事你瞒别人行,瞒我你别打算!你说,你到底是干什么去了?”
“那我问你,我跟谁说了什么?你要是说得出来或是拿得出证据我就认了,你要是说不出来那你就是诬告。你说吧!”
“这个……”特务张口结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好,你实话实说,不用怕,一切有我顶着。他们接头时都说了些什么?”参谋长问。
“这这……我没听见,真的没听见。”特务摇头说。
“大胆!没听见你作什么证!你是诚心跟我捣乱是怎么的?”
“不不,不是。参谋长。那天晚上您不是开了一次会嘛,那回您说谁要是抓住了共党,赏黄金五百两,这可是您亲口说的。开会那天您可没说对什么证,我要是知道还要对证您借给我胆子我也不敢来。”
“那你凭什么说她是共产党?”
“您听我说呀,从那天起我就留了心,我就到处找摸。那几天我跟您说吧,我看谁都像共产党,又都不像。这下可难死我了,后来我跟我的哥们商量了一下,我说咱们三个一起找,找到了功劳算咱们三个人的,那五百两黄金咱们三一三十一我一分都不多要,就这样我们就定下来了。今个我抓住女共产党,这是出于我对党国的忠心,您怎么说我是捣乱?这是怎么说的!”
“好好,就算你是出于你的忠心。我问你一无证二无据你凭什么说她是共产党?”
“我凭我的感觉,我一看就知道她是共产党。我干这行十多年,我的眼力绝对没错。”
“你妈的混蛋!你还敢说没错?你给我带来多大的麻烦你!就因为你,全国都轰动了你知道吗?你让我坐了蜡你倒没事人似的,我告诉你坏事就坏在你身上。来人,把他拉下去军法从事。”
“别别别,参谋长,我下次再不敢了还不成。”特务忙跪地求饶。
“参谋长,您消消气。您看他好歹也跟您十多年了,十多年来他风风雨雨的没功劳还有苦劳呢,再说他家里也是妻儿老小一大帮也够难为的,算了,您就饶他这一次吧。”一个军人求情说。
“饶他?他跟了我十多年我承认,可他就这样给我办案谁受得了,甭客气,拖走!”“参谋长,您不能这样绝情啊,再怎么说他也跟了您十多年,您看在旧情上也应该饶他一次,再说您要是杀了他对得起咱们的老师长吗?”
“谁敢跟我这样说话?噢,是你呀。是啊,他是老师长的儿子,你是老师长的部下,你当然是向着他了。这里我还告诉你,你少拿老师长来压我。老师长又怎么样?要不是他黄公略还成不了气候呢。他死之后这支队伍就让黄公略把持着,你知道这支队伍当时是什么样?他妈的抽大烟的逛窑子的,流氓地痞驴球子马蛋子什么样的人都有,这也叫部队?整个一群败兵。还没打仗就这个德行,你说打起仗来能好得了吗?我要是不来这支队伍就送给共军了。再说老师长是怎么死的你大概还记得吧,他不是死在战场而是死在烟花巷,他是得梅毒大疮死的。从这儿说你就知道这个人要得要不得了。他的儿子怎么样你也不是不知道,他从小就好逸恶劳整天跟着一帮混混鬼混,我跟你说吧,连他算上,这个部队新人伍除外,老的我一个都不稀罕,我早就想给这个部队换换血了,你说我不杀他我杀谁?我还告诉你说,今天谁为他求情我就杀谁,我一个不饶。来人,把这两个求情的也给我带出去毙了!”
“姓张的你等着,老子我在地下等着你,我看你最后到底是什么下场。”
“参谋长,我下次再不敢了。”特务喊。
“下次,你下辈子吧!拖走!”小特务被架了出去,不一会儿外边传来了枪声。
参谋长总算出了一口恶气。他阴笑着说:“好啊刘小姐,这次算你胜了,不过我有的是证人,你就等着吧。来呀,带第二个证人。”他的话刚说完,一个浑身是血遍体鳞伤的人走了进来。“刘云,你睁开眼看看他是谁?”参谋长说,姐姐仔细打量了一下对方才看出来。那个人四十多岁,戴着手铐脚镣,浑身血肉模糊得已经面目全非了。
“看出来了吗?”参谋长问。
“看出来了,他就是那天跟我问时间的那个人。”姐姐答。
“好,有眼力。我且问你,你在西单路口跟他说的什么话?你和他到底是什么关系?从实招来!”
“那天上午我们看很多人过来,我们就站在一边看热闹,正看着,他走过来问:小姐,现在几点了?我说差五分九点。他说了声谢谢就走了。别的我什么也没说。此话句句是实,不信你问他。”
“费话,不用你说我也得问他。好,该你了。那天你跟她说什么来的?”
“那天我确确实实是跟她问时间来的。那天我们学校有事,要在九点准时集合,可巧我走着走着我的手表不动了,没办法我只好向路上的人去问,她就说了一句差五分九点,别的什么话没说。我说了声谢谢就走了。后来我就被你们抓起来了,这是实情。”
“她再跟没你说什么?”
“没有。”
“嘟!大胆。你昨天还交代说你们是在那儿接头,说你们的任务是什么的。为什么今天你就翻供了?”参谋长把惊堂木一拍说。
“回大老爷,那都是你们屈打成招招出来的。我自打进来的时候你们就施了重刑,我让你们折腾怕了。所以我想,得了,我招也是死不招也是死,反正是死,不如我招了算了。我招了就不受罪了。这样我就胡说了一顿,实际上根本没那回事。今天我又看见了这位女子,我看人家都没招出一个字,我打心眼里佩服,也深感自责。我想,我千不该万不该把人家裹进去,我乱咬人家毁了人家的清白我算什么人。所以我说实话,我和她根本不认识,那天我只不过是和她偶然相遇,这是实情。我知道你们还得用刑,还得问。大人,我看你不用再问了,要问你就问它吧!”男子用手指了指旁边的那根柱子,然后双脚跳起一头朝柱子撞去。
“不好!他要自杀,拦住他!”参谋长的话刚出口,那男子已经撞在柱子上倒地死了。那些人却一动不动地傻愣着。
“他妈的一帮废物!你们审了半天你们审什么了?你们审的犯人竟敢在大堂上翻供,你们说这不是自己坏自己的事吗?我问你们这是谁审的?”
“是我。”一个壮汉站出来说。
“推出去毙了!”参谋长气急败坏地喊。
“冤枉啊!”两个士兵哪管什么冤不冤,将壮汉拖了出去。
“把他拖回来!”参谋长忽然醒悟过来,忙下命令,然而门外早传来了清脆的枪声。
“报告,行刑完毕。”一个士兵回来交令。
“咳!他妈的这叫什么事!整个乱套了。”参谋长把桌子一拍垂头丧气地说。接着他又喊:“传下一个证人。”
“下一个证人上堂了。”喊话声才过去,两个特务走了进来。
“你看看,你们认识她吗?”参谋长问。
“认识。砸烂她的骨头我也能认出她来。”
“你们说说,你们为什么要抓她?说错了不要紧,我给你们担着。”
“我我,我们两个哪知道谁是共产党?我们从来就没干过这种事,这是李三的主谋,李三说谁是共产党我们就抓谁,现在李三都让您给毙了,您说我们问谁去?”
“笨蛋,我说的话你们全忘了。拖出去!”
“哎哎,参谋长!参谋长,饶命!”特务绝望地喊,可还是被人拖走了。
“退堂!”参谋长气得脸色发青,草草退了堂,手下的人也垂头丧气地散了。
“带女共党!”参谋长一拍惊堂木喊了一声,特务又将姐姐押上了大堂,第二堂审讯又开始了。参谋长走到姐姐跟前阴笑着说:“刘小姐,你挺得意是吧?你等着,我还有证人。来呀传证人。”只见从外边走进一个女人来,她的头发蓬松着,身上还留着一道道血痕。
“你是证人吗?”参谋长问。
“是。”
“那好,那你就大胆地说,不用顾虑,有什么事我给你顶着。我问你,你认识她吗?”
“认识。我跟她在一个牢里待过。”女人说。
“她跟你说了些什么?你大胆地说,在这儿她怎样不了你。”
“她跟我说她家住在什么地方,有几口人,她的父母叫什么,她说她有四个弟弟,说她是他们家老大,还说她的父亲死了,这次她是为领抚恤金才出来的。我们什么话都说,说得还挺投机。”
“哦!投机就好。我问你,她跟你说没说过她是共产党?或是她的哪个亲戚是共产党或是游击队,说没说过她的任务、接头地点、接头暗号什么的?”
“这个没有。”女犯人摇了摇头说。
“关于共产党的东西一点也没有吗?你尽管放大胆说。”
“没有,真的没有。”
“笨蛋,我是让你来卧底的,你给我卧出个蛋来,我白给你吃饭了,滚!”
“您不是说让我套她的话吗?您让我有什么就说什么,能问什么就问什么,我就是按您的吩咐做的,我问的就是这些,她说的也就是这些,这怨不得我。再说了,我来前您说过,我来一天您给我双倍的钱,今天您让我走,那怎么也得给了我钱再走啊。”
“给你钱?我给你一颗枪子!”女人听了吓得忙退了出去。参谋长接着又喊:“下一个证人。”这一次是女看守走了进来。
“这可是你看守的犯人,这些天你天天和她在一起,按说她的事你应该最清楚。我问你,她跟你说了什么没有?”参谋长问。
“没有,她只跟我说过她家的事,别的什么都没说过。”
“那,他们那儿谁家吵架了拌嘴了这些事都没说过?”
“没有。”
“嘿!真邪门了。还有,你看的这个孩子也没说出什么来?”
“没有,真的一点没问出来,我用过好多办法套他,他除了哭之外什么也不说。”
“连个孩子都问不出来你们算干什么吃的!我跟你说,你们都是给我立过军令状的,如果你们审得出来我这儿有奖,如果审不出来你们一个也别想舒舒服服过去!”他有些气急败坏。接着又喊:“下一个!”那个假舅舅和假表兄走了进来。
“我问你们,你们在这孩子身上问出什么了?”
“没问出来,他什么也没说。”
“那,在特派员来的时候你们不是说你们在他的身上做过工作吗?”
“是啊,我们做了,可费了半天劲这孩子就是不说。”
“你们说了半天都是废话,我怎么养了你们这一群活废物,连个孩子你们都问不出来,我留你们何用!对了,你不是说他还给你接头来的吗?他怎么说的?”
“是这样。当时我装他的舅舅,他装接头的人,我们俩一唱一合就演了一场双簧,我让这孩子当传话的人。当时我让他说‘你是卖白薯的吗?’他要是回答说是,你就再问‘你那白薯卖不卖?’他要是说卖,你就再问他是‘多少钱一斤?’他要说‘两角五一斤’你就说‘太贵了,便宜点行不行?’他要是问‘那你说多少钱?’你就说‘两角钱要是卖,我包圆了。’没想到我这一说他过去对得还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