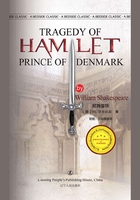女人停住火,用一把小笤帚扫着灶台上的柴灰,说,这就是吴大贵家。你们找他……
夏萍惊讶道,那你是他……
女人说,我是她姑,住在刺梨沟。大贵弟兄这两天在山口上收药,三天才回来一次拿馍馍,我是来给他们蒸锅馍,拾掇点菜,扫扫炕。
夏萍说,听说他们赡养了一位孤寡老人,我们就是来采访的。
女人愣住了,随即笑道,有啥访的,先吃饭。说完去案前忙活了。不一会儿,在炕墙上摆下一盘腌韭菜,一盘油泼辣椒,然后,去掀锅盖卸馍。一时间蒸气腾满屋子,馍馍的香味直往人鼻子里钻。
夏萍说大婶,不等他们来一起吃么?
女人一边吹着手替换着往笸箩里拾馍,一边拿三个碗从锅里舀出三碗蒸馍水,一同放在炕墙上说,他们要夜里才回来呢,你们吃,早起怕是饿到这会了。
蒸馍水黄黄的,要不是亲眼看着是从锅里舀出来的,打死他们也不敢喝。馍馍又白又大,一掰两半,夹点腌韭菜和辣椒,怕是这山里最好的饭菜。即使在刺梨沟村长家里怕也没有这标准。
大婶,你这侄子光景不错哇,有白馍馍吃。夏萍说。
女人也夹了菜并舀了一碗水端着往外走,边走边说,是好光景,我们家现在也是一半粮一半菜呢,别看他爹还当村长。
夏萍才知道这女人就是刺梨沟村长的女人,便也跟在后面进了另一孔窑,只见炕上黑乎乎一堆,一股浓浓的尿臊味扑鼻而来,要不是散乱在枕头上那团白发和还能转动的一双眼珠,真不敢相信那是一个生命。
女人把馍馍塞进那只手里,水碗搁在炕墙上,夏萍不由得打个冷战,这才发现屋里冰窖一般寒冷。
下山的脚步有些沉重,三个人远远落在女人后面,看着她臂挎小竹篮快步如风。夏萍本想在山上住一夜,一听说那孔锁着的窑洞就是让人用镰刀砍死的那家人的,不由得毛骨悚然,那张鲜血淋淋的照片就在眼前晃,连单独走进老婆婆那孔窑洞也头皮发麻,她总觉得那老人随时都会死去。刘敏和谢一飞也不肯单独留下来,何况采访任务是夏萍的,就是等到吴大贵兄弟回来,晚上也无法拍照和组织附近群众。只好回刺梨沟找村长帮助,让他通知吴家兄弟上山等一天。谢一飞让吴大贵的姑姑扶起那位老人,把吴家兄弟的被子从另一孔窑里抱过来靠在身后,又把炕上收拾一番,草草拍了两张照片。三人都不说话,心里却清楚这照片拿出去,哪里会像是被赡养的孤寡人,倒像是无人管的一具尸体。
满腔热情像是被浇上一盆冷水,三人虽没有泄气,已是凉了半截。整整忙活了一天,只知道那位老人是从后山的枣树凹接来的,差一个月七十三岁,姓名不详,人们都叫她花姑。村长女人就只提供了这点情况,老人以前是怎样生活的,有没有人赡养照顾,怎么会来到这里,一概不知。夏萍从她闪烁其词的言谈里捕捉到一点东西,起了一些疑问,却没有再问下去。
天却是黑了,有风飕飕地刮在脸上,刀子一般。脚下一步一滑,稍不留心就一屁股坐在地上。身旁的谷底时而传来一阵不知什么叫声,吓人一跳。夏萍紧紧拉住刘敏和谢一飞的胳膊,想那老人此刻一个人被锁在那孔窑里,不知会不会死去,心就一阵抽紧。望望山道,并不见有人上来,便问谢一飞,哎,如果吴家兄弟今晚不回来,怎么办?
谢一飞说,怎么办?你没听他姑姑说他们三天才回一次家么,就那样办,锁上门。
夏萍不语,又走了几步,刘敏说,我看这次的任务不好完成,这吴家兄弟就不具备赡养老人的条件,家里连个女人都没有,三个男人接来个老婆婆,又不在家侍奉,是什么目的?
谢一飞说,他们不是成了万元户么,为什么不结婚?莫非……
夏萍说,你瞎猜什么,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们今晚就去找村长,让他明天就去找吴家兄弟上山回家,先采访然后根据情况再去请示于头儿。
刘敏说,我看这事有点蹊跷,不如……一句没说完,脚底一滑屁股就墩了地,夏萍也被拉得扑倒在他身上,谢一飞又倒在了夏萍身上,三人都滚了一身雪。
天是完全黑了,远远的,几星微弱的灯光萤火虫般闪烁在山凹里,有狗在汪汪地叫,前面岔路口就是拐往刺梨沟的小路。谢天谢地,总算回来了。刘敏喊道,脚下又滑了一下,却没有摔倒。
早饭是在村长家吃的,确实不如吴家的伙食标准,玉米糁子粥和搀了一半不知什么菜的馍馍,一碟腌韭菜,一碟腌芥菜丝。村长女人从山上带回的白面馍馍没有往饭桌上摆,而是端进了正坐月子的儿媳妇窑里。村长抱歉地说,将就一顿,前晌我就去乡里想办法,你们是来帮助我们的,哪能叫你们吃这,猪食一样。
谢一飞说,村长你别客气,我们是有思想准备的,你先给找吴家兄弟,不然误了文章见报,头儿要我们仨了。
夏萍说,要不我们和村长一起去,顺便看看他们弟兄的生意,然后让他们回家。
村长说,他们怕是夜里才能回去,这阵子正忙哩。你们去了怕也顾不上说话。
刘敏说,就耽误他们一天,让他们和那位老人拍两张照片,再把附近的村民集中起来开个会就行。
要不咱们分头跑,我和谢一飞跟村长去山口,你去梁上周围那几个村组织群众,中午在吴家碰面?夏萍对刘敏说。
村长不去,老百姓会听我的?又当是收税的。让我一个人去吃闭门羹,不干。还是集体行动,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刘敏坚决地说。
一行人出了村长家,还没上崖就听有人喊,五叔五叔,回头一看,谢一飞眼睛一亮,忙用手捅捅刘敏说,哎,快看小芳。
刘敏一看,深吸一口气说,乖乖,真是深山出俊鸟啊。
村长说,她不叫小芳,叫腊梅,我本家侄女,当着村里的妇女主任。这刺梨沟满村里就她念过几年书。
夏萍瞪了两人一眼,细看那姑娘确实长得好,无论是眉眼还是身材都让人无法挑剔,仿佛一泓山泉,清清亮亮一尘不染,就是女人也会喜欢她的。
五叔,你去跟我爹讲,他要是再逼我,我就跑呀,再不回刺梨沟。叫腊梅的姑娘穿一件红底黑花的棉袄,黑紧身裤像是套在棉裤上紧绷绷的,跑得气喘吁吁,鼓鼓的胸脯一起一伏,浑身充满了一股青春的气息。这是他们进山来看见的第一个与众不同的姑娘。她一把拉住村长的胳膊,泪就在眼眶里打转,要不是这几个工作队员,怕早就淌下来了。
村长为难地说,我这会儿没空,急着给他们找大贵呢,再说,不是有媒人么,你咋不找媒人?
腊梅说,媒人能向着我?我就找你,你是村长。
村长说,村长能管了这事?大事还管不过来呢。你不也是妇女主任吗?你先回去,我夜里去给你试试。
腊梅说,你给大贵捎个信儿,甭有两个臭钱就烧得不知姓甚叫甚,他甭想买我,我不是牲口,不稀罕他的钱。
村长忙说,看这女子,快回去,这话我咋能给你捎,说完拉着刘敏说走。
腊梅喊着,你不是他姑夫吗,你不捎谁捎。
夏萍走了很远,扭头看还见那红红的身影柱子般立在村口,就问,村长,她不愿意嫁给大贵?
村长说,如今的女子不能念书,更不能当村干部,当了几天妇女主任就心高得不知姓甚叫甚。嫌大贵岁数大,不就大十来岁吗?可人家能在山口给你盖房,女子家你就愿一辈子住刺梨沟?这正月就过事(结婚)呀,她倒不干了。她爹把人家钱都花了,赔不起。
刘敏说,现在是20世纪90年代,山里还包办婚姻,你这村长就不管?
村长说,村长管收粮要款刮宫流产还管不过来,哪有这闲工夫?
夏萍知道刺梨沟的支部书记去世后暂时是乡政府的包村干部兼着,就岔开话题说,村长,这吴家兄弟是咋富起来的?一样在山里住,一样的条件,是念过书还是有啥技术?
村长说,啥都没有,胆大。前几年不知从哪儿弄来点洋烟种,在山里种,等乡里有人知道了,钱都挣到手了。也就一年就发了。
谢一飞惊讶地说,那不犯法的事么?就没人管?
村长说,那两年谁顾得管这山凹里,不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吗。要不是扶贫喊得紧,乡里一年也没个人上来。这两年弟兄几个收药材就凭的那本钱。在山下买了地皮盖了房,日子是没说的,可我那侄女还看不上,心高得不知想咋哩。
夏萍说,他们没娶媳妇,接孤寡老人谁伺候?一个人躺在窑里,怪怕的。
村长说,瘫了几年啦,还有几天活头,怕啥?早死早享福。要在枣树凹,谁管她去?还能让她睡松木棺穿绸挂缎?连杂木的都没人弄。
刘敏说,这弟兄几个思想觉悟可不低,弄来个瘫子伺候着,在门槛乡也没有第二家吧?
村长说,是够孝顺的,该好好宣传宣传。他爹要是知道了,该歇心了。咽气时硬是不肯闭眼,一手拉一个,让人看了惶。大贵才八岁,二贵三贵还没炕沿高。如今人高马大三条汉,一个比一个能干,你见了就知道了。
那他妈呢?夏萍问。
跟人跑了。一个外路打窑工,硬是撇下三个亲生娃儿。如今要是回来,不后悔死才怪。村长说。到了,前头那房子就是。山口拐弯处一座新房从院墙里露出屋脊,一条大路从门口通往乡政府。夏萍知道,这已不是刺梨沟的地盘了。
那他们咋不把老人接下来住呢?照顾着多方便,倒叫大婶来回跑。看到跟前的新瓦房,夏萍突然想起来。
村长说,咋能接下来,他爹当初就死在那孔窑里。这房子是给他弟兄娶媳妇的。
夏萍还没想明白,村长就喊起来,大贵,工作组来啦。
采访进行得很顺利,照片也拍得很成功,附近的老百姓围了一圈看,脸上无不露出羡慕的神情。一具白茬松木棺摆在窑前做背景,上面专门盖了一床大红缎被面。老人穿一身黑的发亮的缎子衣服,戴一顶黑缎帽,被扶坐在椅子上,脸上竟然泛起一丝红晕,与夏萍第一天看到的判若两人。眼角眉梢流露出深深的满足,在丝绸衣服的包装下展示着一位老寿星的幸福。弟兄仨众星捧月般簇拥着她,裂开三张大嘴笑,像极了几个孝顺的儿子。夏萍想让她说两句,可她耳朵聋得厉害,村长老婆在她耳边大声喊也没用。她只是睁着一双浑浊的老眼无目的地看人,任凭人们摆布。偶尔咧嘴一笑,露出满嘴豁牙,夏萍想不通那天她是怎样吞下那夹了咸菜的馍馍。
村长连连说,这老婆不知前辈子积了多少福,这辈子幸这大运。遇上这弟兄仨,啧啧,看这老衣,看这松木板,还是四独的,咱老了要有这排场也就不枉人世一遭。
有人喊道,村长,你儿子不管你,你就来给大贵当爹,保准让你睡柏木棺,再扎一辆小汽车、大彩电。
村长骂道,龟孙子,咋说话哩?我是他姑夫。
村民们都笑了,大贵说,姑夫你放心,表弟要不买我们弟兄买,不就一副柏木棺吗,三千块,算不了甚。
就是,有这话,你尽放心地死去,今黑里就死。有人喊道。
人们哄地笑了,村长骂道,没良心的巴结我死呢,明年不给你指标,看你养了儿子咋上户口。
要户口干甚,只要有吃的就行。那人说道。
他连结婚证还没领呢,有指标也轮不上他。养了儿子先等着。有人说。
围观的人渐渐散去,老人被抬回窑里,村长老婆忙着给她脱掉身上的新衣,换上原来那身衣服。夏萍奇怪地问,就穿这不好么,留着过年?
村长老婆说,闺女你不懂,那是老衣(寿衣),不是为照相,现在哪能穿。
夏萍方才明白。
大贵兄弟为招待工作组特意从山下带了肉菜,饭桌就摆在窑里,村长老婆在案前忙,二贵坐在灶前烧火,三贵则在院里宰刚打来的几只兔子,要给夏萍他们带。刘敏喜滋滋地说,我老婆最爱吃兔子肉,不发胖。他挽起袖子给三贵帮忙,血溅在裤子上也不在意。
酒桌上,夏萍问大贵你要结婚了?
大贵说,忙完我爹的事就结,一年不能过两事,得过了年才能办。谢一飞不解地问,你爹的啥事?大贵说,我爹结亲呀,你不知道?谢一飞说,你爹不是去世了么?大贵笑道,结鬼亲呀。说完赶紧岔开话题连连说,喝酒喝酒。又忙着夹菜。夏萍不寒而栗,酒菜到嘴里全变了味。
晚上,夏萍的稿子还没动笔,腊梅就跑来了,说,夏姐你们要给大贵上报纸?夏萍说,这不正要写吗,咋啦?腊梅说,他上了报纸我可就退不了婚啦。说着眼泪就下来了。夏萍安慰她说,这是两码事,结不结婚是你的自由,谁也不能强迫。
我们宣传他们弟兄致富不忘济贫的事,跟这没关系。腊梅说,你不知道,他一上报纸就成了名人,我爹绑都要把我绑到他家去,我爹花了他的钱。他一出名就是找谁也没用,没人肯帮我说话的。夏萍说,订婚又不受法律保护,只要没领结婚证,你怕啥?就是领了结婚证还能离婚,现在是20世纪90年代啦,又不是旧社会。
腊梅说,夏姐你哪儿知道,村里人就认个订婚。再说,有钱啥事都能办。我就是不去乡政府,大贵也能把结婚证领出来。只要我爹和村长把证明开给他。
夏萍惊讶道,有这事?这不违法的吗?正说着,刘敏和谢一飞进来了,不约而同地说,哦,小芳。夏萍瞪他俩一眼说,也不看时候,开啥玩笑。俩人才看到腊梅的泪水,悄悄坐了,听夏萍讲。夏萍说,你先回去,我再找找村长,没有你同意,让他不要开证明。
你不也是妇女主任吗?首先要坚强些。不过这不是长远的办法,你要有个打算。
腊梅说,我爹要是再说不通,我就辞了妇女主任去城里打工呀,当个主任连自己都保护不了,我还当个甚劲?听说现在城里的饭店到处招服务员。
谢一飞说,哎,那种地方你可千万别去。
为甚?我能干了,腊梅说。
不是说你干不了,那种地方能把好人变坏,像你这样的,简直防不胜防。刘敏插了话。
我说呢,门槛乡有两个闺女在城里干了两年回来没人要,敢是学坏了?腊梅说。说完,犹犹豫豫地问,夏姐,买人不是犯法的吗,怎么还上报纸?听说还要上电视呢?
夏萍说,当然是犯法的,谁买人了?
大贵家呀,你们不知道?腊梅说。那个老婆婆就是从枣树凹买的,给他爹结鬼亲的。
三人瞠目结舌。夏萍问,结鬼亲不是买尸骨么,怎么倒买开活人了?
腊梅说,听说找了几家都属相不对,这个老婆婆跟他们跑了的娘一般大。
材料是无法写下去了,谢一飞等着拿稿子回风城洗照片,赶着往报社送,此刻三人都没了辙,大眼瞪小眼地互相盯了一会儿,刘敏说,要不去找于头儿,让他定。
夏萍想了想说,先拖一天,等我从枣树凹回来再说。
谢一飞说,值得去调查吗?头儿说写你就写,管那么多干什么?
夏萍说,我要为我自己负责。再说,你敢把前一天拍的照片交给报社么?
谢一飞沉默了。刘敏说,真是,这山里啥事都有可能发生。
夏萍还没去枣树凹,就被于成山叫到乡政府。于成山说,你写的稿子呢?三天都超过了。
夏萍说,于局长,我正要向你汇报呢,这稿子能不能写还值得考虑。
于成山说,为什么?
夏萍说,有人反映大贵弟兄买人,如果是真的,那就触犯了刑律,我们还要树他为典型,是不是不合适?
于成山说,有什么根据说他们是买人?
夏萍说,村长的侄女讲的,说是给他爹结鬼亲的,我看不像假话。说着就把腊梅提供的情况讲了一遍。
于成山说,一个女娃的话有多少可靠性?她会不会是因为不愿意这桩婚姻编造出来的,要不,村长怎么没说呢?
夏萍说,是呀,村长应该懂得这件事的性质呀。真要是买活人当殉葬品,这可不是一般的问题,不要说宣传,他们这可是触犯刑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