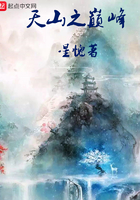女人说,你只想着图自己方便,我几时指望过你们伺候?你也不想一想,这牛呀羊呀的能放下么?冬天没有青草本来就不好喂,雇人喂再不经心,我这工夫就白费了,到时候拿啥还贷款?再说,文苑小区的房子是我能住的么?那是市委领导住的地方,整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我还出门不出门了?我们住回去了,贝贝她妈住哪儿?
人家不是住别墅里吗?小凤说。
那也是人家贝贝姥姥的,不是她自个儿的。女人说。
你怎么就知道是贝贝姥姥的?我听人说就是她自己的,是怕爸要分她的才这样说。妈老是为别人想,就不为爸打算。我知道爸喜欢清净,也就是爸这文化局长能欣赏了这世外桃源,空气好,可冬天这背阴地方你们哪能受得了啊,下去住三个月,明年春天再搬上来不就得了?等雪封了路,你就知道呆在这儿是什么滋味了。媳妇放下筷子站起来,拿了湿毛巾小心地去擦沾在毛料裙子上的一点面粉,完了把毛巾往脸盆里一扔,水就溅了出来,溅在了婆婆的鞋子上。
梅一民拿根牙签,慢慢地剔,看女人低头把吃剩的饺子一个一个往空盘子里夹,对媳妇的建议根本不理睬,心里就有了说不出的感动。他真是没有想到女人那么希望有一套自己的单元房,却从未对他的房子动过心思,看来自己的那点戒备是有点小心眼了。于是站起来拍着小凤的肩膀,一遍遍地说,小凤的孝顺我知道,小凤真是个好孩子,我不怕冷,我喜欢这冷,你不知道,我年轻时候就喜欢围着小泥炉烤红薯,喝那种酽酽的砖茶,唱着蒲剧,高兴了就跑到院子里去翻跟头。后来住进了暖气房子,这情调就再也没有了。梅一民想说我和你妈将来会搬到文化局家属院那套房子里去住,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不想提前做这个承诺。他知道小凤现在是租着房子。如果说出来小凤现在就要搬进去,他怎么办?
爸不愧是搞文化的,还挺浪漫的嘛,怪不得你和妈会……小凤的话说了半截就咽回去了,后面的意思不说也明白。
梅一民突然就脸红了,这是年轻人对自己这件事的定义?浪漫?他有点尴尬地喃喃自语,又笑了一声,是自嘲还是解围,连他自己也不清楚。
但他看到了小凤眼睛深处隐藏着的东西,那东西是从充满希望到变化成失望那一瞬间暴露出来的,让他暗里一惊。
这天是进城洗澡的日子,因了下雨,这日子比平时推后了一礼拜,就让梅一民感到浑身痒痒,像当年下乡回来长了虱子一样难受。一个夏天懒得往城里跑,就在盆里凑合,浑身的毛孔都堵塞了。在热水里泡一个小时,让女人给搓搓背,就是莫大的享受。那时候在家里最享受的就是女人的搓背,躺在浴缸里感受女人手指的那种轻柔,那种细致,那种爱抚,那种无微不至,像母亲抚摸着怀里的婴儿一般,让梅一民每一根肋骨都舒服,惬意,放松,每一个毛孔都兴奋,膨胀,激动。这哪里是搓澡,女人是把他当了一件艺术品来珍惜来欣赏来爱护哇。那一刻,梅一民对妻子所谓的习惯简直深恶痛绝。
妻子从不为他搓背,当然也不让他为她搓背,妻子只让母亲、女儿或者保姆搓背。妻子严守着他们家的文明习惯,比如小声说话,比如咀嚼不出声,比如不能当着异性赤身裸体,还有搓澡。包括夫妻这样的异性。那时梅一民为岳父搓背时就常常想,如果自己和小舅子不在家时,岳母会为自己的丈夫搓背吗这样的问题。
有一次梅一民在妻子洗澡时打发女儿出去买烟,然后趁机走进浴室,那是他第一次在灯光下看到妻子的裸体,妻子闭眼躺在浴缸里的姿态真是美丽无比啊,像是西方的维纳斯。可惜他还没走到跟前,一只沐浴露的瓶子就砸在了脑袋上。无耻!下流!肮脏!卑鄙!妻子的骂声像锥子一般直戳他的心,那种痛一点不亚于脑袋上的疙瘩。
女儿买烟回来诧异地望着父亲时,梅一民简直无地自容,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女人没有买双人间,她买了大间。叫个搓背的才两块钱,这一次就省十四块呢,一个冬天省多少钱?你不是说现在要省着花吗?女人算账给他。
这账好算,双人间二十块,大间一人两块,加上搓澡一次省十四块,一礼拜洗一次,一个冬天不就二百多吗?就这样洗上十年,才节约两千多块,值得吗?
可舒服多少钱一斤?
享受多少钱一斤?
情爱又多少钱一斤?
梅一民想说我一千五百块的月工资连洗个二十块的澡都不能?人家还桑拿呢。
梅一民还想说我就是想享受一下你的搓澡你不明白吗?
可他忍了忍。他不想在大庭广众之下为花钱与女人争执,那样就显得太小气了。何况,如今要抠着钱过日子是他的倡导,这不自己打自己嘴巴吗?
梅一民早就不习惯进大间洗澡了,像是看一屋子的肉体展览,鸡皮疙瘩层出不穷,扒在皮肤上战栗。又像是进了屠宰车间,只差把肉挂在那一个个铁钩子上,排队一般。
池子里泡着几个老头,泡好了的慢慢扒着池沿上来去莲蓬头下冲,鸭子一样蹒跚。梅一民可不敢下去,这不是自己家里的木桶,谁知道里面藏了多少病菌?其实这池子本身就是个大传染源,腾腾热气把千百种细菌混合培育随意杂交无限繁衍。
水哗哗响着,不时有管理人员进来检查洗完走了人仍在哗哗响的莲蓬头,边拧开关边嘟囔,谁这样不懂节约水啊?要是你家的能这样吗?边嘟囔边拿起笤帚扫地上的积水,脏水溅到了梅一民的腿上,一只空洗头膏袋子上到脚背,也没有一点道歉的意思,仿佛是梅一民把所有的莲蓬头打开了似的。
同志,咱俩互相帮助帮助,怎么样?省两块钱呢。
一个老头悄悄站在梅一民身后说,吓了他一跳。他的肋骨一根一根在胸前突起,生殖器耷拉在两腿间,看不出颜色的搓澡巾捧在手里,对着梅一民,眉里眼里全是讨好。
梅一民帮他搓着,看着垢泥翻卷下来,一条条布满发红的肉体,又从老头手里接过不知在多少脊背上扫过的小笤帚,把那些东西扫在地上。听着老头情不自禁的哼哼声,一种难以抑制的恶心泛起在心里。他堂堂梅局长,就因为走进了这样的浴室,就给人当了一回义务搓澡工。他当然不会让他互相帮助,因为他不习惯,他不想让自己的肉体在别人的目光中也产生自己刚才的感受。
梅一民选了靠窗口的莲蓬头,挤了半瓶沐浴露,还觉得老头的体味留在他的指甲缝里。
搓澡工进来了,大声喊道,搓一个?两块钱买舒服,多划来啊?
没有人应声,他悻悻地边走边嘟囔,小气鬼。还特意看了梅一民一眼,仿佛说我说的就是你呀。
梅一民草草揩干身体,他已经看到又一个老头拿着搓澡巾向他笑着走过来,他逃一般冲出浴室,觉得自己非但没有洗浴后的爽快,反而浑身针刺一样别扭,肉体上沾满了龌龊,连呼吸都不洁净。
女人已在院子里等他,一个熟人刚从桑拿室出来,红光满面地朝他打招呼,梅局长怎么不在家里洗,跑这儿体验生活来了?哎,我听说市委领导们家里还有安桑拿的,嫂夫人没安?看到女人,熟人又哈哈道,听说你最近在乡间别墅养病还带着保姆,你老兄可真会享受生活啊,怪不得越来越年轻,简直就是倒着活呢,山里空气好吧?赶明儿也给我介绍一个好的,我家都换三个保姆了。哎,那天我在高速公路上看见你在爬护栏,咋,又找到长寿的新方法了?
熟人钻进车子后又摇下玻璃喊道,你的车子还没来?要不我捎你一段?反正也不绕路。
看着车子绝尘而去,一种无名的火气顿时从梅一民胸中涌出,排泄一般痛快:要是洗双人间,哪会给那个老头搓背?不搓背哪会一遍遍地冲他的臭味儿?哪会耽误时间正好碰上这熟人?哪会让他奚落一顿?你就知道省那十四块钱,钱是个什么东西?我才值那么点钱么?攒钱干什么?我一个月的工资洗你十年澡你知道不,你算不来这个账?你是成心让我丢这个人?
女人傻在台阶上。
没有稿子可写,日子便渐渐由单调变成乏味。作为男人,梅一民没有理由游手好闲地捧着茶杯品着龙井观秋天的美景。他要帮女人割最后一茬苜蓿,帮女人晒草,帮女人把晒干的草搬回草棚,帮女人铡草,帮女人起出圈里的粪担新土垫进去。
毕竟五十多的人了,这种活偶尔干干可以,天天如此就有点体力不支。最初劳动的快乐就被肉体的疲惫一点一点侵蚀,最后只剩下那点理智在撑着面子,还有做男人的自尊。
牛要吃夜草。原来女人每天夜里起来添草时他不觉得,他通常是晚九点上床睡觉,凌晨四点起来写作。女人添草正是他做梦的时候,他哪里能体会到夜里添草的辛苦?秋凉了女人的哮喘病就犯了,他就主动夜里起来添草。添草就不能九点睡觉,睡熟了再爬起来是最难受的事情。他只能看书,烛光下看不了几页眼睛就酸得顶不住。就与女人坐着。
添过三次草后就到了午夜,过了午夜睡觉就打乱了生活习惯,梅一民又把睡眠丢了。连丢了三晚上梅一民就有点顶不住,眼球上爬满血丝,嘴唇长一排水泡,在女人买的简易马桶架上蹲一个小时也解不下大便,还把痔疮给蹲犯了。食欲也明显减少,饭吃进嘴里没味儿不说,还搁在了半道上不肯下去,憋得一股股酸水往上冒。整天提不起精神,像是断了鸦片的大烟鬼,一脸的晦气。
女人心疼了,不再让他起夜添草。
可梅一民的内分泌分明是紊乱了,听着牛们的叫声,听着女人咯咯地咳着一次次开门去添草,他彻夜无眠。
把牛卖掉算了,听我的,钱算个什么东西,咱俩这老命值钱还是牛值钱,这账你不会算?吃早饭时梅一民实在忍不住了,没有那些张口的畜生,日子就会轻松许多。
你不懂,现在卖不上价钱,就是卖也要等生了犊子才能卖呢。女人不同意。
我是不懂你的养牛经,可听着你一夜夜地咳,我都疼得慌,你就不难受?你说这是何苦呢,这钱莫非比命都重要?一个牛犊不就四千块么!累病了进一次医院,恐怕花的还是多的。
你说得轻巧,好像你多大款似的,钱不就是一点点攒起来的么?不然,拿什么还贷款?你那几个钱只够咱们吃饭的,顶多攒几个将来看病,再说,万一有个急事怎么办?女人不同意。
梅一民想不到什么是“万一”,也许真该攒点钱?那么办手续时就要跟妻子提提家里的存款。他从来不知道家里有多少存款,虽然那时他管家,他的工资不用交妻子,买菜买日用品足够一家的生活费了,但也所剩无几。至于孩子上学集资房子这些大花销,从来是妻子全部包揽,他根本就没管过。家里如今到底有多少存款,他好意思和妻子张口么?
为什么不好意思?夫妻结婚后的财产就是共有的,无论多少都应该有他梅一民一份。还有,梅一民多少年如一日的家务劳动,莫非就一钱不值?雇个保姆一年也得好几千吧?梅一民当了多少年保姆不说,还给岳父搓澡,每年腊月二十三去扫房子擦玻璃,换煤气罐就是他一人包了,小舅子即使在家也不干。岳父这老革命宁可累他这女婿,从来不让司机干家务,这该算多少钱?
梅一民一次次地在心里为自己寻找着理由,他仿佛看到了妻子签字时那鄙夷的目光,那目光足以又一次把他击败,败得一塌糊涂。
梅一民终于决定去找村长,让他仔细算算接电要多少资金。他想起自己的一位高中同学就在电业局,也许这点事对他们来说根本就不是个事。
刚走出小路,一辆黑色轿车远远驶来,梅一民心里一沉,到底找来了,意料之中的事情。当然,妻子自己不可能来,只能是她的秘书或者司机。那就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吧,早晚有这一回不是?车子吱地停在他身边,却是村长与市里气最粗腰最壮的房地产开发商钻出车门。梅一民绷紧了的神经顿时松弛起来,心里却多了一丝说不出的怅然。
找人不如碰人啊,这么巧,梅局长就像我肚里的蛔虫,就知道我今儿找你,就站在这儿候着。我没说错吧?这地方就这点邪乎,这就叫风水好啊。再往里走十几里,就是关老爷的祖茔哇,不是这风水,关老爷能封了皇帝?你再往东看,那是蚩尤村,几千年的历史啊,踢一脚土都是文物。再往东,是当年运盐的古道,听说有人投资开发呢。这一开发是什么光景?北接关公机场,南通西北五省,这地方啊,寸土寸金也不止呢。我们村里要是有资金,能轮上外人开发?先下手为强啊。村长拉住梅一民滔滔不绝,像是怕没人听他说话似的。
开发商握住梅一民的手。梅局长真不愧是文化人啊,我说这满凤城市也就您一个是真享受生活,这空气这绿地真是没说的,别墅盖好了,先让梅局长住一套,终生免交管理费,怎么样?享受我公司最高待遇,够意思吧?对了,还请您给我们这乡间别墅区起个名字,要文化味儿浓的,再请您帮帮忙,请省书法协会会长给写个匾额,听说是您的中学同学,告诉他润笔费从优,我看满凤城市就他给博物馆门上的字写得最好,让人看了就顿生敬意,以为王羲之再世呢。怎么样?
梅一民一头雾水。村长继续拉着开发商东西南北转,你看,这满山坡的绿颜色,盖十几栋外国式的红房子,山上封了林,又安全又环保。山下不到三里路就上高速,到机场只要二十分钟。山后有黑龙泉,是凤城最优质的矿泉水。我们村里一年四季供应无化肥无农药污染的蔬菜和水果,土鸡保证不喂饲料,鲜牛奶和羊奶保证不加防腐剂,那儿挖一个养鱼塘,用矿泉水养鱼怎么样?那鱼肉肯定天下第一鲜,比喝啤酒长大的外国牛肉好吃多了。是不是梅局长?
兴致勃勃地环视一周后开发商来了兴趣,是啊,我们小区的居民可以自己提着篮子到菜地里去摘西红柿黄瓜,去鸡场捡鸡蛋,去鱼塘钓鱼,烤鱼架就支在鱼塘边。还可以办个酒作坊醋作坊酱菜作坊榨芝麻香油作坊什么的,让他们自己抡抡锤子踩踩轮子推推碾子磨子,亲自体验劳动的快乐,让他们的孩子去接受劳动的锻炼,好!不过你说的外国红房子早过时了,现在是要盖农家院。看到村长瞪成铜环般的眼睛,开发商笑着拍拍他的肩膀,不懂了吧?没文化了吧?老兄,当然不是你们住的那种农家院,是外面像农家院,里面全套的现代化装备,暖气空调抽水马桶桑拿,煤气管道宽带家庭影院,一个都不能少哎。老兄,这才叫天人合一,这才叫返璞归真,这才叫构建和谐社会,是吧梅局长?说着又拍拍梅一民的肩膀。
可盖房子不就得把这些树砍掉?修管道架电线不就得把这些天然草地都毁了?修车道建停车场盖幼儿园学校超市得占用多少耕地?还有文化设施体育场馆你能一一做到么?这又得毁掉多少土地?这跟城市有什么两样,什么乡间别墅。梅一民一头雾水渐渐散开,质问开发商。
是呀梅局长,你不愧是文化人,简直比内行还内行。老实说,现在的乡间别墅叫乡间别墅,城市功能可一样也不能缺,不然卖给谁?谁来住?住在这儿怎么上班怎么上学怎么买东西怎么娱乐怎么交流沟通?不方便嘛。一切都要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对不对?一切都要人性化设计对不对?开发商言之凿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