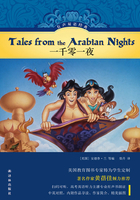1
中国饮食传统素来忌生冷,推崇热食。
广东人有“够镬气”的讲究,上海人喜欢“热灼火烫”,北方人要“滚得冒泡”……可见不论南北,中国人忌生冷的传统是一致的。
《红楼梦》中宝钗劝宝玉不要饮冷酒那一番苦口婆心,足见国人对冷寒食物的忌讳,或者因为古代医药不完善,摄入的卡路里又不够,因而肠胃较娇弱,受不得半点寒气。
今天冷饮风强盛,三九寒天孵哈根达斯、天寒地冻饮啤酒、威士忌里放冰块……真正三九严寒何所惧!冷饮,已成都市时尚生活的佐证。
“冷饮”一词,是解放后才叫出来的,老上海话称之为“冰激凌 ”。当然,“冷饮”的叫法也许更科学、更简明,但远不及一声“冰激凌”,在一片冰清玉洁之中,沁溢出一缕温情脉脉的浪漫。总觉得老上海的英汉翻译,又贴切又朗朗上口,从字形发音到字面都考虑周全。如弹簧锁 Spring为“斯必灵”(是必灵),Smart为“时髦”, Model为“模特儿”…… Ice-cream前半个将冰直译出来、后半个则是意译和英文谐音,“激凌”也有译为“结凌”,那种琼瑶剔透、晶莹沁亮的感觉扑面而来,既有汉字之美,又符合上海人崇求西洋新奇花样的心理。冰激凌,那三个字包含的那抹璀璨锦簇、温情浪漫,哪是“冷饮”两个字所能表达的。
冰激凌在上海的历史,应与上海开埠史同步。初时只在洋人餐桌上现身,即使到了 20世纪20年代,因为电冰箱在上海尚属奢侈品,连一般中产人士家居都罕有冰箱,更遑论市面上的小商小铺,所以在 20世纪初,“冰激凌”这个名词十分华丽娇贵,代表一种奢华。而且还得有点洋思想的上海人,才敢品尝这种冰嚓嚓、寒咝咝的物什。
上海和香港,可谓中国最早有冰激凌的城市,那时吃冰激凌,也属开洋荤之举。
直至20世纪 20年代后,现代化的大批量生产的食品厂,如益民四厂前身沙利文、可的牛奶公司、屈臣氏等在上海纷纷建立。此时在上海才开始有批量生产的冷饮走上市场。冰激凌也是从那时走出深闺,但也只是进入上海一些为中产人士服务的洋烟纸店、网球场、跑马场、电影院及咖啡馆,与广大市民阶层仍是缘悭一面。
据笔者八十五岁母亲回忆(她生于 1920年),在她十岁时,一只“海丝娃”纸杯卖 2角洋钿, 1块“海丝娃”冰砖售 1块洋钿。一张首轮电影院票是 6角洋钿。当时我的外祖父为中国银行八仙桥分理处主任,月薪为 216块洋钿。那时一只红木百龄桌连四只圆凳一套售 120块,一担米售 3块,一个熟手剿丝女工月薪 20块,可见冰激凌,仍与一般平民大众相距甚远。
因为其市场定位的特殊性,冰激凌的零售点大多设在租界地沿马路公寓大楼底层的洋烟纸店——洋烟纸店之有别于上海人的夫妻老婆店,在其是以一众西洋侨民和上海生活西化的中产专业人士为对象,老板大多本身为西崽( boy)出身,熟谙西方人生活习惯与口味,并能扯几句流利的洋泾浜英文,上海人俗称这样的洋烟纸店为“士多”(store),即英语“杂货铺”的意思。也只有这样的士多,才有经济实力置一只电冰箱。
士多出售的冰激凌,有家庭型包装的,如半加仑装、一加仑装的,价钱相对零星小买要便宜,但购买家庭需有冰箱。
士多里最受小孩子欢迎的,是蛋卷冰激凌、纸杯冰激凌和涂上一层淋淋漓漓的巧克力—— Ice-cream Bar,上海人称之为紫雪糕,以此区别纯白的香草冰激凌。
那冻津津、甜腻腻的冰激凌,因为价钱不菲,一直是几代上海孩子童年的向往,即使对中产家庭的孩子,也是一个惊喜。于是连带那马路边垂着蓝白相间的帆布篷下的士多,都成为老上海们成长回忆中的一个情结。
40年代中期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大量美军剩余物资倾销上海,从克林奶粉到军用听装巧克力,其中包括大桶听装的冰激凌粉。
抗战胜利后,大量美国家用电器开始抢滩上海,包括电冰箱,著名的有“北极”“奇异( GE)”“西屋”等,并开始在上海中产时尚和富有之家亮相。有了家用冰箱,总会出点新花样做点家制冷饮,如杏仁豆腐、冰冻果汁……自制冰激凌,也成当时时尚,在上海一些有闲人中十分时兴,有如今天上海时尚人士自己烤蛋糕一样。
家制冰激凌全靠人工摇出来。在一只木制的内有铝制内胆的尺把高桶里,四周铺满碎冰块,然后要不断摇动把柄,原先调好的冰激凌酱就会变稠变厚,成为冰激凌。
家制冰激凌全在其娱乐性,通常最起劲的都是家中年轻人、小孩子,享受的是那份热闹和开心,根本已不在冰激凌本身。
2
对都市来讲,冰激凌贩卖的已不只是炎炎夏日中的一个清凉世界,更是一份温情和童真。
一个到老仍对冰激凌有嗜好的人,一定是个乐观、健康和幽默的老顽童。
八四老人,美籍华人马克,我的忘年之交,就是一个爱冰激凌的快乐大孩子。“二战”期间他入伍参战,参加过残酷的冲绳岛登陆。
每次登陆前,后方驻地总要以丰盛的大餐为出征壮士送行。很多战士忧心忡忡根本咽不下去,唯他乐呵呵地从头盘吃到甜品,从牛排吃到冰激凌。
即使身在大都会纽约,对一个唐人街的穷孩子,冰激凌仍是一种奢侈。
入伍后在后方驻地可以开怀对着冰激凌大快朵颐,这令他很开心。
“就是打死也死而无憾 ——吃饱冰激凌再死,死了也开心! ”他这样说,“冰激凌样子是那样动人可爱,凉笃笃的让人头脑清醒,精神振作。不像白兰地,让人越喝越沉沦。冰激凌让我相信,生活是那样美好,战争总有一天会结束,我一定要活到那天,然后恋爱、结婚、生孩子……”
他活下来了,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还成为 1971年度“纽约成功人士”中唯一的一位华人。他仍爱吃冰激凌,特别是顶端那粒艳红的樱桃。
“二战 ”结束那年,他从菲律宾调防到远东第一都会上海候轮回国。候轮期间,他任美军第四海军陆战部队俱乐部(南京西路春雷集团现址 )餐饮部沙展(类似餐厅大堂经理 ),日日可以尝到餐台上的各式冰激凌。
“上海的冰激凌比美国的口感要细腻得多,甜得适中,糯软得多……”他如此评述。
早从20世纪20年代始,上海的时髦家庭已开始在炎炎夏日用冷饮款待客人,直到五六十年代,用冰激凌招呼客人,在上海,仍属十分有品位的待客之道。
年少时逢夏日家里来客,我和哥哥总会十分雀跃,因为这意味着我们也可以叨光吃一次冰激凌了。
果然,妈妈会慷慨地扬起一张 5元面值的钞票,差我们去对面马路的冷饮店(前身就是解放前的士多)买大瓶装汽水和冰砖。为了怕冰激凌顶不住三伏天太阳的烘烤,家里有专门的五磅广口保暖(冷)瓶。
那时市面上已没有“海丝娃” “Dairy Farm”,只有单一的“光明牌”,但就一只光明牌,已给我们的童年带来无限欢欣和光明。
冰砖买回来,放在特别的苏打水杯里,冲上正广和汽水,一时咝咝地冒起奶白色的稠厚的泡泡,一阵夹着奶油香的清凉迎面扑来,这就是冰激凌苏打。
如果正好有草莓上市,就将草莓拌在冰激凌里面,变成一抹粉红色,夹着乳白色,十分梦幻,撩动人心。
冰激凌兑上汽水叫冰激凌苏打。
冰激凌缀以水果装饰,叫冰激凌圣代。“圣代”一词来自 Sunday。冰激凌圣代,即星期天吃的冰激凌。星期天吃的冰激凌,用水果巧克力装饰得特别精致悦目,代表一份放松娇慵的星期天的心情。
可见,冰激凌贩卖的,不在味觉口感,更在视觉和心情。
3
20世纪20年代起,上海时髦白领交往,很时兴吃冰激凌,当然不是坐在家里,而是指堂吃。
那时堂吃冰激凌主要有两大场所,一是咖啡室内,还有更时尚的,是在网球场、法国公园或兆丰公园的露天茶座的太阳伞下。
感情尚未成熟,或只差一层窗纸未捅破的男女约会,最合适点叫冰激凌。特别在露天茶座的太阳伞下,极其浪漫又轻松自然。
靠着绿茵茵的草地,他一身白夏克斯基西便装配白帆布西装裤,黄白镶边的高尔夫球鞋;她一身白底红点的泡泡纱旗袍,白凉鞋。两人隔着茶色太阳镜深情款款地互相注视,那精心配制的冰激凌圣代,是用巧手和创意浓缩而成,鲜艳而饱满,就像此刻两个情窦初开的男女。
真的,如果你是内向的、拘谨的,那第一次约会她的场所,最好是露天的咖啡座吃冰激凌。
首先,面对一客精工细作的冰激凌,光是欣赏和赞扬之语,已可省略许多无话找话的烦恼。此外,冰激凌经不起时间耽搁,因此必须不断抿尝,如是可以打破冷场 ——细细欣赏他或她尝冰激凌也是一种肢体语言,但如果他或她不断呷茶或咖啡,就会显得很傻,没有了那份美感。
当一个女孩子低头含笑羞怯地品尝冰激凌,真可谓此处无声胜有声。
“我们等一歇去看电影好吗? ”
她只是低头微笑着抿冰激凌。
“等一歇我送你回家好吗? ”
女孩子将一小口冰激凌送入嘴,嫣然一笑:
“随便!”
……
中国人的记时方式,有“一支烟工夫”,或许对都市时尚男女可说,吃一杯冰激凌工夫。
吃一杯冰激凌工夫,正好够自重的一对渴望进一步交往的男女,进行一次最初的谨慎的近距离接触,进行一次圆融恬淡的一对一对话。然后,冰激凌化了或者说尝完了,正好有个好体面的理由告辞。
老上海的咖啡茶座,冰激凌都盛在沉甸甸的特制的喷银高脚杯中。为方便洗涤,内胆衬有一张白硬纸,几只各色球形冰激凌被各种红红绿绿的水果点缀得一片姹紫嫣红、娇艳欲滴,恰如两个心里甜蜜蜜的青年男女的心情——灿烂又明亮。
喜欢相约在露天太阳伞下吃冰激凌的男女,心情必是十分阳光的。即使在幽暗封闭、情调典雅的咖啡馆点冰激凌的男女,也必有一份喜滋滋的心情。两个正要谈分手的男女,是没有点吃冰激凌的心思的,苦涩涩的咖啡或振奋神经的威士忌倒很适合他们。
风尘女子与她们的恩客相好,也绝不会有那份心情点叫冰激凌——那份健康明快的灿烂不属于她们的世界,反令她们触景生情:那只是一片顷刻就化为一堆五彩黏液的浮华,正如她们的青春。男的也没这闲情陪她开这洋荤,这种花钱又没意思的花头经,才不值得花在这种女人身上。他们需要的不是情调和心情,只是直接的交易。
男女约会吃冰激凌,特别在露天太阳伞下,透明度极高,落落大方,光明磊落,与相约坐酒吧或喝咖啡或烛光晚餐,有种很微妙又极具原则性的区别,故而老上海有冰室和咖啡馆之分。应该讲,许多上海人初恋的记忆都是与冰激凌有关系的。就是今天的哈根达斯或其他品牌的冰激凌的专卖店布置,都是开放明朗为主格,不同幽暗、强调私密性的咖啡吧,或者就是与那份愉快单纯的冰激凌心情有关。
一个男生看中班上一位姣好的女生,但又不好意思单独约会她,他就可以大胆邀上几个死党朋友,一伙人径自走到那女生一伙中:“今天放学后请你们吃冰激凌,去伐 ?”
“呵,阿光今天请客吃冰激凌呀!去呀! ”女孩子们高兴地尖叫起来。
于是,一簇男女大学生,热热闹闹地跟着阿光到兆丰公园的冰激凌店或大学门口那一长列俄国人开的冰室:
“拿八只蛋卷冰激凌……”
阿光从袋里掏出钞票,一副小开气派。也只有小开,才有集体请吃冰激凌的豪气,冰激凌本身,在上海,好长时间来也都只属小姐小开的消闲。即使今日,可以在哈根达斯一声“来八客香草冰激凌”的,也需要有点豪气和财力的。
同样是请客,“来八客生煎馒头”与“八客冰激凌”境界完全不同。冰激凌是属于时尚青春派的。
但是,两个女孩子可以在一角边吃冰激凌边喁喁私语,两个男人对坐一起吃冰激凌,就有点娘娘腔,令人怀疑他们心智尚未成熟;一对老夫妇对吃冰激凌,看入眼十分可爱,觉得他们童心未泯;一个老人带着第三代对坐吃冰激凌充满温馨慈爱;中年人带着两老吃冰激凌令人感到一片孝心。曾见到一位老人带着他的中年儿子来吃冰激凌 ——儿子有唐氏综合征,吃得眉飞色舞,老人只是在一边默默看着,这样的画面凄凉又悲壮。
今天电冰箱已普及,大部分上海家庭都拥有冰箱。但是上海人,包括我,尽管家里冰箱还有满满的各式冰激凌,仍不时要在外面,如恒隆66那大堂咖啡室、老锦江南楼的咖啡室,甚至麦当劳,点一份冰激凌。因为,吃冰激凌是一种心情。
4
上海人的冰激凌情结,是坚韧不拔、忠诚又执著的。
解放了,跳舞厅、夜总会等都关闭了,唯独冷饮,只是名称改了下,而且统一成为“光明牌”,一直持续至今。
上海人的冰激凌情结依然。除了老牌西餐店、咖啡店“凯司令”“老大昌”“德大 ”外,解放后甚至还开出了新的如 “上海咖啡馆 ”“海燕 ”“海鸥”等,这些场所仍有冰激凌圣代和香蕉船供应,只是名称改成什么水果冰糕之类,全然无一点浪漫的空间。即便如此,这样的地方仍坐满情侣。
至于大众化的冷饮店,更是比比皆是。一般较大型的食品店都有一片门面,特别辟出一个冷饮部,供应大冰砖、中冰砖。然后沿墙是几张简易的方桌长条凳,搪瓷的碟子、铝质的匙勺已被摔打得伤疤累累,上海人仍合家坐在那里吃得乐滋滋的。这种吃了就走人的简易冷饮座生意十分好,不大有空闲的时候。当然,来帮衬的都是平头百姓,但由此可见,上海毕竟是个大都会,冷饮文化是如此普及、深得人心 !
好长一段时期,上海市面上的冰激凌只有单一的冰砖。纸杯、蛋卷冰激凌、紫雪糕都不见。然而上海人已十分满足。特别我们小孩子,一块“光明牌”三色大冰砖已可令我们雀跃不已。至今犹记得那分别由乳白、粉红和淡褐色组成的“光明牌”冰砖,三只颜色粉嫩粉嫩的,很淡雅、很娇俏,以后但凡见到那种粉红、粉啡色,总会想起三色冰砖。
即使困难时期,上海市面仍有冰激凌供应,仍是“光明牌”一样一式的包装,只是那时不叫“冰砖”叫“雪砖”,颜色如巧克力色但一点没有巧克力味道,只是一块冷冻的带甜味的冰砖状物体。上海人欣喜地接受了“雪砖”,在电影院里,在冷饮店里,在公园茶座里,“雪砖”点缀了上海人当时贫乏苍白的城市生活,犹如“二战”期间的欧洲人用炒焦的大麦代替咖啡一样,上海人在全国大饥荒年代,还是尽力用替代品持续那割舍不了的冷饮情怀。
直到大饥荒年代过去了,到了 60年代中,上海冷饮如百花齐放的春天:纸杯、紫雪糕、加仑冰激凌又回来了。但只是昙花一现,1966年“文革”开始,谁还有吃冰激凌的心情 ?
直到“四人帮”粉碎后,各色各样冰激凌先后开始再度于上海滩亮相。此时出了一种奶油味浓、口感更细腻、价钱也贵一点的“白熊牌”冰砖,开始在市面上唱主角,打破了上海冷饮市场“光明牌”一统天下的局面,这也算得上是上海改革开放的第一道曙光吧 ?
近年咖啡文化的白炽化,大批大型购物中心的落成,海外冰激凌品牌的大举抢滩上海,再加上家用电器的普及,令上海的冰激凌市场,呈现出百年来从未有过的绚烂。
冰激凌,永远是都会一朵开不败的时尚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