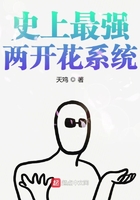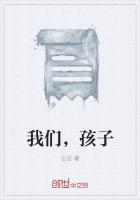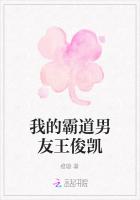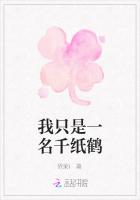如此枪林弹雨而又久拖不决,未免令人心焦。这就是杨瑞轩要跟刘玉春打擂的背景。他们有言在先:杨瑞轩获胜,鄂军让开西门,老陕经由豫西入陕;刘玉春打赢,老陕出北门接受改编。
杨瑞轩与刘玉春的底细,赵明远兄弟二人自然比谁都清楚。论起师承,杨刘二位虽然官居将军,但却比赵明远兄弟俩晚一辈。比武打擂的消息,就是他们俩传回来的。江湖有江湖的渠道。起初李玉亭不敢相信,但是转念一想,又觉释然。春秋无义战。瞬间敌友沧海桑田,都是常事。你看看当时的大人物,有多少盟兄弟,并且还在不断地义结金兰?今天结好明天厮杀,或者倒过来。这样打上一架,也没啥了不起。
双方议定在北门外徒手比武。红拳对通臂。比武场设在战线正中,双方步枪的射界之外。如此一来,鄂军的战线要局部后移。不过事先已经说好,鄂军的炮兵阵地不动,一旦老陕突袭,鄂军立即实施拦阻射击。
当日北门附近人山人海。达官贵人可以占得先机,登上城墙远眺,李玉亭便在其中。他爬上去一看,城墙已是坑坑洼洼,千疮百孔,露出里面发白的乌青。
那时天气已经回暖,几天后便是惊蛰,大家的衣服自然不那么臃肿。只身出城的杨瑞轩远在千米之外,此时居高临下看过去,他原本魁梧的身材已经萎缩许多,刘玉春也是如此。二人都是短打打扮,到了跟前互相一抱拳,随即开始交战。
刚开始大家还喝彩加油,但很快便都屏住呼吸,双眼圆睁,一眨不眨,唯恐错过精彩。二人拳脚交加,你来我往,不分上下,荡起地面的尘土微扬,如同淡云。正打得激烈,鄂军方向忽然有人高声呼喊:“大捷!开封已下,岳维峻已死!”
比武就此打断。二人朝后一退,只听鄂军那边的呼喊越来越高,越来越齐。后来才知道,此前一日,靳云鹗已破开封。由于信阳的电话电报全部中断,报纸也送不进来,消息此时才刚刚传到。而五天以前,岳维峻召集高级将领商议对策,竟然议而不决;浪费三天时间之后,又做出错误决定:退回陕西。危急时刻,人们的选择无非有二,一是母亲二是故乡。八百里秦川毕竟是生养他们的所在,而李虎臣还头顶着陕西军务帮办的名义。
南人计议未定,北人兵已过河。当时老陕的上策自然是退往直隶,与冯军会合。然而这都是事后诸葛。岳维峻并不那么想。他将财物装满十七个车皮(其中想来有禹县的收获),便向西起运。可惜的是,这些年他们荼毒地方,豫西百姓早已恨之入骨。各地红枪会配合刘镇华余部,沿途持续劫杀,五六万老陕就此风流云散,财物再度回归民间。岳维峻只身渡河逃往山西,但坊间盛传他已丧命于红枪之下。消息传到湖北,吴佩孚心生恻隐。跟他刀兵相见的对手,绝大多数会成为朋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赵恒惕。冯玉祥是唯一的例外。吴佩孚随即发表通电:“生则为敌,死则为友。眷念前情,怆然涕下。虽解项王之体,应归先轸之元。”意思是说,即便岳维峻已像项羽那样被肢解,也希望他能如同先轸,魂归故里。
先轸是第一位明确带着头衔的元帅,晋文公所谓的“谋元帅”,曾指挥晋军取得城濮之战的胜利。殽之战中更是全歼秦军,俘虏其主将孟明视、副将西乞术和白乙丙。所谓秦晋之好,晋文公的夫人既是秦穆公之女,又是晋襄公之母。她劝儿子释放秦将,以免增加仇怨,终被采纳。先轸乍一听说,对襄公大发脾气:“将士们拼力死战才擒获他们,而妇人不过说几句谎话,国君就将之赦免。毁伤战果而长敌人志气,晋国要不了多久就会灭亡的!”说完气冲冲地朝地上吐口唾沫,拂袖而去。
称国君的母亲为“妇人”,对国君“不顾而唾”,均不合礼法。晋襄公越是宽怀谅解,先轸也就越发愧疚悔恨。后来他指挥晋军与狄人在箕(山西蒲城西北)作战时,怀着必死之志,脱去甲胄冲入敌阵,直至战死。据说他死后尸体屹立不倒,狄人以为神降,恭恭敬敬地问他愿意葬在狄还是晋。问到晋时,尸体倒下。狄人于是将先轸的首级送回晋国。那时他依旧面色红润,犹如活人。
却说比武当时,电报员正巧接到总部的消息。苦战月余,双方均已疲惫不堪。得知此事,电报员大为惊喜,不觉脱口而出。周围的军兵听见,一传十十传百,声浪自然越来越高。杨瑞轩见势不对,指责此举乃是鄂军故意安排,刘玉春有违道义,随即掉头奔回城内。
城中百姓闻听,短暂地叫了声好,便飞快地看看周围,然后再无声息。老陕终究就在旁边。大家都指望这是劫难的结束,但却未能如此。当天夜里,老陕出城逆袭,结果遭遇密集的炮火拦截。次日他们再度力杀四门全面反击,小南门一带炮声震天弹如急雨,但打了半天,除了一堆死伤,再无收获。
那时烟馆早已关张,因为烟土断档。李玉亭也颇为不安。这倒不是因为岳维峻已经倒台,柜上大量的豫票必定已成废纸。这个消息他内心已经消化。他感觉自己就像油酱铺前的那具尸体,被人割去髀肉,却感觉不到疼痛。他担心的也不是粮油食物,这至少还能对付一月。他最担心的,也是烟土。他只抽娃娃土,别的烟土都不对路。可是眼下,娃娃土只够三五日之用。假如不能迅速开城,那他如何是好。
很久以前,即便在李家寨,李玉亭也不再过问巡夜之事。但是如今在信阳城内,每天晚上他都要亲自查看门窗是否关严,家人是否都在。而那几天赵明远兄弟俩经常很晚不着家,说是想以武会友,与杨瑞轩交流交流。他们虽然互不相识,但彼此已有神交。李玉亭起初并未在意,次数多了方才起疑:杨瑞轩已是堂堂旅长,更兼军情紧急,哪有那么多闲工夫论交?追问之下,高继古这才说出实话:他要找麻浩清报仇。
高继古之所以流落到禹县落脚,是因为那里的中药材生意。习武之人难免要受跌打损伤,中药必不可少。他因此顺藤摸瓜,到了禹县。反正当初也是茫茫大海漫无目标,就像抓阄,碰到哪里是哪里。在禹县这三十年,他交了两位挚友,一文一商。他们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平常走动很是频繁,逢年过节更要像亲戚那样来往。
禹县屠城之前,李世登匆匆传回来的救命消息,高继古自然要向他们通报,但最终却只救了一家,另外那家未能逃脱。全家连人带物,都被一把火烧得精光。
那家的女主人姓何,没多少文化,但侠气十足,人称何仙姑。高继古刚逃到禹县时,一路惊慌失措颠沛流离,偶感风寒,因而病倒。等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间药铺里,有个伙计在给他灌姜汤,旁边还站着个店主模样的女人,用热毛巾给他敷头。
女人一袭藕红袄,年龄三十上下,模样很是俊俏。那时高继古还年轻,尚未婚配,且几乎从未与陌生女人有过如此近距离的接触,不免有些害羞。那种窘迫也提醒了女人。她暗暗一笑,微微撇嘴,把高继古交给伙计,起身进了后院。
那女人便是何仙姑。她丈夫也是读书人。当时医生分为几类:行医骑驴四处巡诊,看病不收费,开定点药方,跟药铺结算;堂医在自家或者别人的药铺里坐堂接诊;儒医有玩票性质,多读了点医书药方,因而也成了医生。何仙姑的丈夫,差不多就是个儒医。
然而药铺真正的灵魂人物,却是何仙姑。她丈夫心里眼里只有诗书,很快就将高继古引为同调,走动日渐频繁。彼此熟络之后,何仙姑曾经调侃高继古道:“怪不得你当初那么害臊。原来也是个读书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