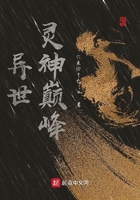一个饼子要是能充饥,那可真是太小瞧何顺仔了。甭说一个,就是十个、二十个这会儿他也能一口气不剩渣儿地吞掉。但十个、二十个毕竟太遥远了,只这一个,就已经使何顺仔感动得几乎要流下泪来了,总算是给肚子里有了一点交待。可……也真的太少了!他咂咂嘴,一副回味不尽的样子,一副想象着饼子无穷好处的样子,那样子,何顺仔自个儿感到是可怜之极了。
何顺仔摸着衣袋,现在他渴望的是奇迹。摸了又摸,翻了又翻,底朝天了,奇迹没有来。何顺仔倒下去了。他倒在一排楼房下,缩在一个角落。眼睛闭不住,他不想睡,准确说,是饿得睡不着。他瞪着双秃圆秃圆的眼珠子,吸收了周围四面八方的黑暗和明亮,直直地发着愣。
何顺仔怎么睡着的,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总之,醒过来时,天已大亮。他醒得最早的肚子,先咕咕叫着吵醒了他。鸡巴子了的,饿!何顺仔自言自语了。猛然他想起来了,鸡巴子了的,上当受骗了!他一骨碌跳起来,直奔昨天早上交了钱找铁饭碗的迷你公司。鸡巴子了的,铁饭碗不找了,先找口饭吃,得要回那五块钱!他一路想一路跑。五块钱哪!那不是小数目!咋白白地就给了人?何顺仔啊何顺仔,你也是进过几天学堂的,还是古店庄里一个大名赫赫的独秀才,咋这么没有脑子?没有分辨能力?没有多长个心眼?唉唉——唉唉唉——如此马虎,如此丢三拉四,如此容易受骗……你今后还过不过好日子啦?在几个大男人面前你都如此上了当,那要是在几个广告牌上假女人那样的真女人面前呢?你恐怕是把自己也卖啦?人都说英雄难过美人关,何况你何顺仔,卖了自己,肯定是帮着人家数钱哩!唉哟……何顺仔,一个大意的险些卖了自己的何顺仔啊!他一边跑,一边嘴里不住地咕哝着。因为他声小,别人听不清他咕哝什么,就当城里又添了一个疯子。
何顺仔一口气跑到昨天七拐八转弯的地方,找到了那排房,却找不见挂着的红牌子。于是在那排房前徘徊,心里发了急。他东瞧瞧西瞅瞅,房子虽眼熟,就是找不出标记来,这才后悔忘了问那些人的名姓了。怪那个真女人!当时只顾紧贴她的圆屁股,倒忘了该暗暗记住个记号的。鸡巴子蛋,这女人!这女婊……他一抬头却惊住了:真女人来了!
“你……”何顺仔说。
“噢,你……”真女人愣了愣,随即又镇定了。“有事?”她表情冷漠。
“我要……要那五块钱!我饿……饿……不找铁……铁饭碗了……”何顺仔结结巴巴地说,并且眼里这次是由于饿极而露出了很凶的光。
真女人不答他话,只默默沉思状看着他。
“我要钱……要我那五块钱!”何顺仔摊开两只乌黑肮脏的手。
真女人便后退了一步。立即,她做出了痛苦而无可奈何的样子,伤心没有流泪;气愤、骂叨起来——“老乡,你来要钱是吧?你可知道我来干什么的吗?”见何顺仔睁大奇怪的眼,她用快要哭泣了的语调说,“老乡啊,我们都上当了,他们——”她指着某个门,“都是骗子啊!”
何顺仔表现的更为吃惊了,“你也……”“是的是的,你才小小的五块钱,我可是交了六百元钱的!化为乌有了呀!你,不就五块钱吗,一碗饭钱,你还要什么呢?算了吧,老乡,跟谁去要啊?我那六百元都没地方要了呢!”真女人说着就唉声叹气起来了。
何顺仔收回了那两只手,悲哀地叹着气。他又朝那排房子望了一望,呆呆望着真女人。
真女人说:“回去吧,老乡,我六百元钱都不打算要了呢。”
“不想要了?”何顺仔心里跳了一下。
真女人说:“嗯。”
“我……我得要!”
“你到哪里去要啊?”
“我告!”
“就为五块钱,老乡?你也不想想,为五块钱你得再花多少钱才能告倒他们?开玩笑吧!回去的好!我一个女人家,六百都不要了呢,你一个大男人还在乎五块钱!小气!”
何顺仔觉得无话可说了。就同时很为自己的“小气”而可笑。他笑了笑。“我开玩笑哩!不就五块钱么,小事一桩!不要了!不要了!”他说,“鸡巴子了的,拿去吧,拿去买药吃吧!”
真女人又愣了愣。
然后,何顺仔脸上堆满笑,仿佛是想唱的样子,很潇洒地离开了。临走,他对真女人挥挥手,竟说:“六百块么,小事一桩!你莫要难过哟!”
真女人先点点头,后望着他的背影骂:“乡巴佬!笨猪!愚蠢!穷鬼!短命!”
六
现在的何顺仔,转到了县城的某个角落。他缩在墙角下,侧目观看一场戏:有个男人,胖胖的,从一个店里走出来,惊慌失措的样子,好像要钻进店门口停着的小车里,于是把左手搭在车门上,却不拉开;有个女人,披着头发,涂着红嘴,脸白,好看,紧跟了来,扯住那个男人的衣袖,只扯了一下,又松开手,后退一步,嘴唇在动。男人转回脸去,抬起左手,用手指了指右臂上的什么,又想钻进车里,嘴唇也在动。女人又赶上来一步,拉住,使劲往后拽,男人又立定站好,对着女人,伸手扳她的肩,然后推她,似乎想推到远处,不想要的意思。但女人如蛇,缠着她,推不出去却带得更近,女人眯起眼,两只手伸进了男人的衣服里……
何顺仔看得无聊,嘴里骂了一句“鸡巴子了的”,就顺势把头勾下,听着肚子里咕咕大叫的声响。他再一次抬头时,看到有个孩子胸前挂着一张写满字迹的纸牌,在大街上跪着,过往行人都驻足看一阵,摸索着把零钱扔在了孩子面前。何顺仔大脑突然一闪,“鸡巴子了的,连讨饭都不用说!”心里嘀咕着,便也想好了一招。于是他来了精神,跑到远处捡来一棵草,想顶在头上,却怎么也顶不住,就只好插在衣领里,远远看去,那头上倒也像是长着一棵草。
何顺仔这样了,就跑去学着那个孩子样跪在大街上。但他很快发现,人们照样给那孩子扔钱,却没人理会他。更为可恶的是,一个和跪着的孩子一样大小的孩子还朝他唾口水。何顺仔心里开始动摇了,也冰凉了。他想站起来,可肚子在一个劲地叫唤不住。忍一忍吧,再忍一忍吧。他心里对自己鼓着劲。何顺仔一直跪到腿都疼痛得有些不听使唤时,才有个老人从面前走过顺手扔给他五毛钱。何顺仔原本要高兴,却不料鼻孔忽然一酸,有几滴收不住的眼泪就滚了出来。他赶紧低了头,只把那五毛钱在手心里捏得似乎要淌出水来。
寻到这样一条求生路,何顺仔每天都要找一棵鲜艳的草插在衣领里,用以吸引同情者,且练好了长久下跪的功夫。虽然也有人路过看见讥笑他这是卖身的做法,但何顺仔已顾不了那么多。
尽管如此,也好景不长。几天后,何顺仔面前站了两个真正的公安。何顺仔当时勾着头并不知道。他只看到有四条长腿立在面前,以为有人扔钱来了,心里叫着大爷大叔的行行好么,却不见有钱落下来。正犯疑的当儿,公安说:“起来!” 何顺仔抬头,妈呀!鸡巴子了的!咋办?想站起来,腿早已麻木,试着站了几次最终倒了下去。公安们弯腰一左一右把他几乎是抬了起来。“丢人显眼!”其中一个骂。“骗了多少钱?”其中另一个问。
“我……我……”何顺仔在想敢不敢说实话时,一个公安从他衣领里拽出了那棵草,感到了真实的好笑。说:“你算是给县里把人丢尽了,解放前都没你这号人,谁要你啊?”另一个脾气有点爆,扯住何顺仔问:“哪儿的?”何顺仔答:“古店庄。”“干什么的?”何顺仔说:“我找铁……铁饭碗来了。”“铁饭碗?神经病,我还没有哩,轮得到你!”
何顺仔被押着走的路上,一个劲的向公安们讨好。他也油嘴滑舌了,说:“瞧瞧,你们大人不记小人过嘛,我世代贫农,又没反动过谁,干嘛这么过不去呢?你们都是有铁饭碗的人么,跟我一个乡下人见识啥吗?喂喂,同志,饶一饶好么?我不找铁饭碗行不?我死回我们古店庄好不好?嘿,那古店庄也是个好地方,有山有水有地种,对了,我种地!我回去种地!”公安问:“你不是要找铁饭碗吗?把你关进号子里,有吃也有喝,人人都把那儿叫铁饭碗哩。”何顺仔挣扎着,“我不去我不去,我真的不去!我什么都不找了,我种地!我们古店庄人呀,一辈又一辈,一代又一代,都端铁饭碗,知道么?那才是铁饭碗!”
公安们站住,问:“你真打算回去种地?”
何顺仔说:“嗯。我回去,我一定回去,我种地!”
“你不找铁饭碗了?”
“不找了不找了,我不找了!”
“好,现在就放你回去,可要回去种地。”
“嗯嗯,我种地!”
何顺仔一被丢手,就如笼中鸟儿解了困,狱中犯人不再囚,立时有了些兴奋。但同时又发生遗憾,觉得应该去尝尝号子里的铁饭碗。鸡巴子了的,尝一下就走才好哩!他伸手进去,在衣兜里反复揣摸着那些可怜得来的钱币。之后觉着该是要大吃一顿了。他四下里瞧寻,恰就见一城里女人进了饭馆,于是,何顺仔几乎是唱戏文般地跟了进去,眼睛不住地往别处瞧,最后只相着城里女人脸。可是何顺仔也没贼胆,虽挨个桌儿坐了,只眼睛死死盯着对面那张冷冰冰的脸。末了,服务员送上菜单,何顺仔也不知道点什么菜,胡乱往菜单上一指,说:“随便。”服务员细细看了看他,预算了什么人上什么饭,笑笑而去。
直到城里女人面前摆上了炒菜、摆上了鲜汤、摆上了米饭,直到城里女人文雅地一小口一小口把面前丰富的佳肴快吃完蛋了时,喉咙里直翻口水的何顺仔面前才摆上了一碗干面条。何顺仔便想发火。而服务员站在面前挡住了他瞧城里女人的视线,“交钱!”服务员说。何顺仔心里就更加恼火了,但碍着城里女人暗里射过来的目光,他大度地笑笑,伸手进去,掏出一把杂毛乱分来。服务员便也有些不高兴的清点了,何顺仔才吃了两口,服务员抢过碗,“还差两毛!”何顺仔又探手进去,却摸了空,心里发了凉,怅怅望着服务员。服务员怅怅望着城里女人。城里女人不抬头,唏唏溜溜喝下一口汤,说:“赶出去!”
何顺仔就被赶了出来。夜里,何顺仔在一连串的“鸡巴子了的”咒骂声中游荡到一片寂静的住宅区。他有些想哭。有些真的想回古店庄了。但就这样回去么?不能什么都没有就回去吧?汽车不买了,女人不找了,衣服不穿了,皮鞋不要了,铁饭碗没有了嘛!
那好,就回去吧!待回去,东山再起,几年间就会是一条好汉了!
那也不行,总不能饿着没气力,浑身上下无分文,让古店庄人笑掉大牙。也好,就弄他一回,带个什么也罢,不枉上城一趟。
他想的时候,就看见了路面上的下水道铁盖,这不好吗?拿回去打造他一只铁饭碗来,祖祖辈辈子子孙孙还不就一直用下去了!何顺仔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卸下铁盖,刚扛到肩上,巡警们就迎面而来,几道电灯光一射,何顺仔就中了弹一样了。
当几天后何顺仔被警车送回古店庄时,他看到古店庄人全都站在古店庄口等着迎接他。何顺仔猛然心里一阵酸楚,禁不住嚎啕大哭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