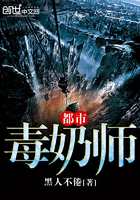“从上海开往成都的K290次列车已经开始检票了,请各位乘客抓紧时间到5号检票口检票。”
“开始检票了,开始检票了。”
“检票就检票了,你激动个啥,没坐过火车啊?”我推了一把奶妈,“有力气大叫,还不如再提个包呢。”这句话比什么都管用,奶妈彻底闭嘴了,乖乖地提着一包行李在人堆里缓缓前行着。
一大早,我们几个人忙着帮阎维打包整理,然后坐上奶妈叫的一辆出租车就屁颠屁颠地赶到了火车站。一下车,放眼望去,就看见黑压压的一片,简直跟蚂蚁搬家似的,排山倒海的。每到了放假期间,火车站外见到的不是民工就是学生,还都是一伙一伙的,我们几个差点就像小时候春游一样,手拉着手前进了,就怕走失,怪不得阎维那小子从一开始就始终狠命地抓着他那包藏有贵重物品的行李,死活不肯放手给我们提,估计就怕我们在途中装迷路。
说实话,这还是我自小以来第一次上站台送人,感觉挺新鲜的,每次坐火车都幻想着在站台送行是个什么滋味,会不会也像电影里的场景一样:依依不舍,含情脉脉,欲言又止,挥泪告别,随着火车启动便顺着站台一路狂奔,就在快要接近站台尽头时,又非常凑巧地“吧唧”摔一跤,然后泪眼朦胧地看着列车渐渐远去,伸出的右手却抓不住那离去的但仍在挥动的双手。当火车终于没有了一丝踪迹时,立马回过神来,一抹眼泪,然后迅速地回过头去:“操,刚才谁他妈绊我的。”想着,我就止不住地笑。
“一个人偷笑,傻啦。”道长拍了拍我,“到你检票了,别做梦了。”
检票?哦。梦被敲醒后,回到现实中的我面临了一个实际而又严酷的问题,站台票找不到了。我几乎翻遍了所有的口袋,甚至差点把阎维的行李包也想拿来翻个地朝天,但最终在他犀利眼神的威慑下,也只好借势挠了挠头。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不动啦,没票你别堵着啊,到后面找去。”有一位大叔显然不够友好,完全没有人民群众需要互相团结的味道。
“你要不先站旁边,慢慢找吧,不要耽误大家的时间了。”身后一帮子人开始骚动起来。
检票员看了看我,然后给了我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顿时好绝望,得,那就站旁边吧,谁叫我自己没准备好呢。我提上了行李,刚转身,突然又被检票员叫住:“哎,你手上的东西。”哎?你叫谁呢,我不爽地把右手上的行李包就往他的检票台上一放。
“你给我行李干吗,我又不是寄存处,那只手。”检票员有点不耐烦了。
我又极其不情愿地伸出了左手,不过很快就有了想找一堵墙的冲动,看着手上死死拽着的站台票,心想,这回糗大了,肯定要被奶妈嘲笑死了,原来没坐过火车的人是我。
有了这一段不大不小的插曲,让我对刚才想象中站台送行的感觉便大打了折扣,一时竟然提不起精神来,事实上,奶妈并没有嘲笑我。到了快要临别的时候,他越发显得安静,说实在的,我是越来越看不透这个小子了,不知道他的快乐到底是什么。
“回去后,打算做什么工作呢?”道长和阎维并肩走在我们前面,他们两个人身高差不多,因此肩并肩走感觉很舒服,不像我和奶妈,简直不是同一水平线的,怪不得他只能是后卫,括弧,还一强力后卫。
“我父母帮我联系好了一家物流公司,说先在里面学学,回去后可能形式上还要面试一下。”
“那么牛,现在做物流的太火了,你小子以后可要发大财了。你爸妈的门道还挺粗啊,连面试也只是过过堂。”道长看上去有点羡慕。
“没有想得那么好,这家公司规模小着呢,其实也不是我爸妈门道粗,主要是那家公司是我叔叔一个朋友开的,也就是看着面子照顾照顾我罢了。”
“也别那么说,你会学出样的,不过专业不同,需要更加努力了。”我插了句嘴。
“我会的,毕竟父母现在身体不好,家里还要靠我呢,这个我明白。”虽然阎维看上去五大三粗的,可是他的确是个孝子,内心深处说不定柔情似水呢。
“哎,你怎么不说话啊,装深沉呢,你装也是装不像的。”我用肘捅了奶妈一下。
“别烦,老子在思考问题呢。”
“我考,什么时候成思想家了,思考什么问题呢,说出来大家一块参悟参悟。”我用对奶妈一贯的语气嘲讽着他。
“我在想,阎维要是回四川了,那以后我们篮球队不就少了‘阎罗王’的组合了吗,那多没意思啊,所以我怎么也要再想出个组合来,填补一下。”
“你小子突然沉默寡言就是在思考这个啊,兄弟们,不理他,不理他,让他一个人思考去,我们管我们走。”我脚步加快了一点,开始和道长他们并排走着。
“苏旸,要不就我们俩组合一个。”奶妈也跟上了我的步伐,还冲着我抛了一个媚眼。
我不自觉地颤了一下。
“我和你?什么组合啊?”我十分不解。
“你说是‘羊奶’好,还是‘奶羊’好啊?”
“我考,这就是你思考了半天的组合啊,什么馊名字,看我不教育教育你,有种你别跑。”我开始摆开了冲刺的架势,但脚跟压根没有离地,因为论速度我比不上奶妈,论精神,我犯不着和他耗,就让他在几十米外一个人折腾吧,懒得理他。
“阎维,你少了一包行李哦。”我很平静地说了一句。
阎维环视了一圈,然后猛然抬头,高声疾呼。
“奶子,你给我他妈滚回……”他一开口,我们就迅速地捂住了他的大嘴。
“冷静点,冷静点,在外面还是叫他本名好,叫他本名好,不然影响不好,影响不好。”我和道长两个人反复强调着这几句。
“那小子就是他妈欠揍。”阎维愤愤地说。在场唯一偷笑的就是我一个人,心想,要治你小子,才用不着我出手呢,只可惜,世界上你唯一怕的人就要离开上海了,我们又要经受被你精神摧残的命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