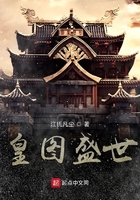哑炮?
白宗错愕之际,早被宫让一枪扫下马来,跌落尘埃。
“大哥!”白成狂吼起来,疯了一般想挣脱开身上的铁链,可是又怎么挣得开?
好在宫让并没有下杀手,只是用枪尖指着白宗的额头。
白宗不敢动弹,恨恨道:“你这厮的狗运确实不错……”
“什么狗运,你以为你的火枪只是哑火了这么简单?”宫让冷笑道。
“难道说……不可能!”白宗睁大了眼睛。
宫让悠然解释道:“你的引火线在靠近我的那一瞬间,火就熄灭了。我对火焰极为敏感,也具备操纵火的能力。简而言之,你大意了。”
白宗怔住,转眼就被叶龙拿铁链绳索缚了,与白成、贺阙二人锁在一块。宫让忍不住嘲笑道:“以为掌握了火器,就可以荒废术法与武艺吗?幼稚可笑!”
号称“智将”的白宗实在难以忍受这样的侮辱,忍不住回头问宫让:“为什么不杀了我们?你想利用我们做人质吗?”
宫让看了看白宗可怜的模样,道:“不,是因为我不杀南将。”
贺阙冷笑一声:“呵,好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随你怎么想吧,胜者可不在乎手下败将的想法。”宫让示意叶龙带他们下去,自己则与墨城准备击破山坡上的敌军。
宫让非常喜欢墨城,喜欢这个年轻英俊、武艺高强的小伙子,甚至数次有冲动想招揽他到自己麾下。但宫让又是个多疑的人,他对墨城始终有种隔阂感,这种感觉源于汉开边,也源于百里中正。
墨城一马当先,率火龙军发动突击。白宗手下人马早就军心涣散,加之没有了指挥官,更是不堪一击,哪里挡得住墨城这般的勇者?登时溃败,四散而逃,墨城轻松得胜而归。
“你的枪法真不错,颇有我当年考到武状元时的风采。”宫让策马走近墨城,有意说些恭维的话。
“将军谬赞。”墨城却不愿意多作回应,“末将斗胆提议,加速行进,攻击朴山。”
宫让听得此言,知道墨城已是迫不及待想回到首辅亲军,心里有些不快,脸上却仍是和颜悦色,呵呵一笑道:“好,听你的。”
白宗军的残部星夜逃回朴山,把情况告知了白云儿。
白云儿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两位兄长都在宫让手里,自己已是方寸大乱。帐内一灯如豆,她屏退左右,思虑良久,看着桌案上的那个铁兽面具,眉头紧蹙,一个时辰、两个时辰,却始终想不出破解困局的办法。她向来是女中豪杰,性格外柔内刚,遇到这般没有退路的情形,她仍不愿意在脑海中闪过“投降”二字。
“镇南以国事托于我兄妹三人,而今岂可以一家之私而废天下事?”
她看着铺在案上的地图,自言自语。忽然,一个名字在她心里一闪而过。
但她很快又把这个名字抛在脑后:“即便是欠我人情,他恐怕也不敢帮我。”
“报——”
一声呼叫打断了她的思路。卫兵在帐外尖声报告:“北面敌军似乎有了动作,而南面出现了一支人马!”
白云儿霍然起身,斩钉截铁道:“开阵,随我迎敌!”
朴山驻军合营点起火把,片刻间完成布防。火炮、火枪、枪兵、刀斧手全部依照白云儿的计划部署完毕。
“把南北两个大门打开!”白云儿在高台上发号施令。
两个旗号兵接了命令,骑上马,飞快地朝相反方向跑去。
宫让站在外围,远远看见寨门大开,疑惑不已。叶龙见状,上前一步道:“将军,内中必然有诈。”
宫让尚未作出回应,又听见轰隆之声,循声望向朴山下,只见四条金柱拔地而起,直插云端,好不唬人。宫让道:“白宗已被我擒获,敌军应是群龙无首才对,怎么还有此等异法?且待北面信号,再依计行事。”
夜是黑夜。
无月,无星,无风。
四野寂静,万籁无,肃杀气氛却悄然腾起。
公孙浒稳坐中军大帐,对汉开边、张时二人道:“既然经略王让尔等执行秘计,那便全权交由你们指挥了。”
汉开边闻言,激动道:“定当击破敌营!”
公孙浒道:“你看样子还未伤愈,眼圈与嘴唇怎恁的发黑?这模样,还能指挥作战么?”
汉开边苦笑道:“末将已无大碍,只待王上一声令下。”
公孙浒将信将疑,沉声道:“那就有劳你们了。”
“是!”二人齐声应道。
汉开边、张时二人一齐现身将台,台上灯火通明,早有一人久候,正是陆英。
“那就拜托陆英兄弟了。”开边拱手道。
陆英兴奋叫道:“好说!看我的好戏吧!”
说完,陆英挥舞手中令旗,高声喝道:“公孙衮,发号箭!”
话音刚落,台下一员小将,催开坐下白马,飞驰到台前,取一张大弓,指捻号箭,朝天一射,顿时一声尖锐长啸划裂夜空,直迫九霄。阵前诸将听得信号,纷纷率领士兵双手合十,念动真言,使起呼风之法。渐渐地,本来无风的夜晚,空气却开始流动起来。
“古德!擂鼓!”陆英喝道。
古德站在一面巨大的军鼓前,拿起木槌,擂起鼓来。他臂力惊人,捶起鼓来,声音极大,震彻数十里地,连另一边的宫让都听见了。
“听——鼓声!”宫让道。
叶龙道:“必是汉开边行动了。将军,我等该如何配合?”
宫让道:“便用我久未使用的妙法,赞他一臂之力。”
“难道是‘业火幡’?”叶龙颇为讶异,“此法不是将军压箱底的秘术么?怎可轻用?”
“此阵能阻朝廷大军多时,若不用此术,焉能击破?”宫让道。
“可是此法耗费甚巨,将军可要三思。”叶龙担忧道。
宫让笑道:“因此需要众军协力助我。你率火龙军使用招火符,一齐念动真言,剩下的便交由本将军来办。”
叶龙领命,飞速策马发令。众军闻得军令,立即自背囊中取出招火符箓,念动咒语,手捻火诀,每人挥出一颗火球,朝天空飞去,瞬时数千火球如流星雨般挥洒而出,惊得朴山下南军士兵个个瞠目结舌。此时,宫让亲自挥枪跃马,驰骋阵前,手中大枪朝夜空一指,真力爆发,只见一道烈焰腾空而起,宛如一长竿,耸入云霄。朴山上,白云儿遥遥望见,如一条红线,被云端一仙人牵着,垂下凡尘,不由狐疑:“那是什么?”
那飞火流雨在夜空中华丽坠下,忽又被一股神秘力量引导,纷纷朝宫让头顶的火竿上聚集,竟是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形成了一道烈焰之幡,威严恐怖,自云天垂下,气势压人。宫让稳坐鞍鞯,双手擎枪,势成托天,火幡熊熊燃烧,照耀四野,亮如白昼。叶龙仰头望着这面业火长幡,面色肃然,只因这招妙法威势赫然,极少需要使用,他这个副官也只见过一次。
白云儿遥见火幡,花容失色,失声道:“宫让竟有如此能为!”
正自踌躇之时,白云儿又惊察风向有异,忙令手下盯住火幡,自己飞奔山头的另一边,拿望远镜观看北面敌军,见将台之上,陆英手执羽扇,挥斥方遒,指挥着前面众将,施展法术,竟是引起猛风,往北面劲吹。
“不好!”
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白云儿差点站不稳脚。她虽然智勇双全,但却缺少独自引军的经验,面临如此阵仗,没有兄长撑持,她便顿时乱了内心。
“若让那道火幡被风引动,必然延烧朴山连营,我军便难逃一败。但若离开金阵去突袭敌军,我却难是宫让敌手……”她细想之下,作出决定——突击汉开边的法阵!
只要将汉开边的风阵破了,便可解除朴山危机。白云儿的想法不无道理。
她戴上面具,背上剑盒,火速提兵,率三百个精锐骑兵近卫,从北面寨门突出,直冲陆英所在高台。怎料,虽然速度已是极快,却仍被一支彪军截住,为首一将正是梁弘。朝廷军以数百火把照亮战场,梁弘手持骊燹宝刀,展示过人武勇,直扑而来,惊得白云儿忙以孤鹜剑抵挡,二人斗了二十回合,白云儿剑法散乱,不敢再战,祭起背后另一柄剑,首现落霞剑法,半空中劈下一道磅礴剑气。梁弘大喝一声,骊燹宝刀急速挥出,竟硬接下这一击,那厢白云儿见状,忙借机拨马逃走。梁弘见她奔回朴山连营,也不追击,收刀回兵。
将台之上,汉开边轻轻咳嗽两声,深吸一口气,对张时道:“多得张先生安排梁弘在侧翼埋伏,护住将台。”
张时淡淡一笑,道:“如此周密计划,岂容半点闪失?只是未能擒杀那人,有些可惜。”
汉开边听了这句,心里竟“咯噔”一下,虽然他猜梁弘并非嗜杀之人,更不会轻易杀害一名女子,但此时也难免替白云儿捏一把汗。
张时似乎没有察觉到汉开边的神色,自顾自道:“待大火焚山,浓烟必将朝我方吹来,汉将军,可作好对策?”
开边点了点头,心里却盘算着别的事情。
却说白云儿逃回营中,欲再作应对,已是来不及了。业火幡腾在高空,猛地炸裂,散作漫天火雨,在风力助威之下,朝朴山连营落去。顿时,朴山上的火炮被火雨点爆,爆炸声此起彼伏,振山撼地;树木燃烧起来,冒出滚滚浓烟,好不吓人。营帐难逃祝融之灾,士卒争相抱头逃窜,整座固若金汤的雄关,顿成炎热地狱。白云儿没奈何,召集身边士兵,下令各自朝四面突围,自讨生路。众军听罢,潸然泪下,不愿背弃。
环视四周,一座座帐篷、一片片鹿砦被火焰侵噬,哀鸿遍野,冰冷铁面之下,白云儿也已泪流满面。
她挥舞着马鞭,决然喝道:“撤!随我撤!”
数百南国步骑掩护着白云儿往东南方突围。而此时风向骤变,竟是以朴山金阵为中心,形成一股巨大的旋风,所有的火焰、乌烟,都被狂风挟着,旋转着,上升着,肆虐朴山。
金柱轰然崩塌!
“不错嘛,陆先生的指挥能力一点不亚于你呢……”张时朝汉开边诡谲一笑,“我原以为要避免浓烟朝这边袭来,须把风停了,没想到竟能把八面风变幻成羊角旋风,好手段,敌军怕是要全军覆没了。”
汉开边苦笑不语。
奇怪的是,白云儿一行人竟好似不惧怕风暴一般,毫发无伤地撤出了暴风圈,找到一处山凹歇脚。
“为何……”白云儿也感到疑惑不解。
她下马清点人数,无意间看见剑盒上有一张奇怪的符箓,于是猛然醒觉:“必是此物避风——是他!他是什么时候留下这一张符的?”
必是前番金阵之中,汉开边趁自己不注意,在背上剑盒动了手脚。
白云儿不禁陷入沉默。
却说那厢宫让望着朴山金阵已破,喜不自胜。叶龙道:“将军,此阵既破,我军困局已解,何不收了火幡,去与王师会合?”
“可也。”宫让遂作起法来,竟又把金阵内的火焰全部收回头顶业火幡,仰头张口,将那火幡缓缓吞下,咽入腹内,吓得在场众人目瞪口呆。宫让笑道:“莫怕,经此一役,我功力又有增进。”言语间嘴角犹在冒烟,看得墨城骇然。
另一边的陆英看见火焰消失,高声喝彩:“赢了!”
朴山北面瞬间爆发起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
汉开边早已骑上战马,率首辅亲军冲进朴山阵去。
公孙浒遥望汉开边离去身影,喃喃道:“好个急先锋……”
一旁洛京云却露出了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