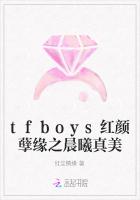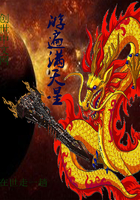三
十多年后,凤山寺旁的小茅屋内。
离鸳在砚盒上轻轻地拭着毛笔,直到那笔尖变得圆滑饱满,方在纸上运笔疾书。离鸳的字,吸取了王羲之的精华神韵,并在其中揉和了颜筋柳骨,自成一家,气势浑宏磅礴,豪迈奔放而又不失携永清秀,潇洒流畅如行云流水,看起来爽心悦目。再配上他所填写之绝诗妙词,简直就是难得一见的天工巧作。
离鸳才写出四五个字,便停笔摇头直叹息。自从前日武玄方丈说要带他去广西桂平,离鸳的心就不再静若止水,而是时时泛着莫明其妙的心烦意乱和困惑不解,字亦写得不堪入目,大不如从前,所作之词亦是句句落入俗套。离鸳看着桌上墨迹未干,败笔横生之字,不觉间又怒火攻心,便将毛笔狠狠扔于桌子上,走到窗前,倚窗眺望,企图让心情平静下来。离鸳看着眼前的秀山美景,那怪石尖尖如指,圆圆如笋,又有如鹰蹲,有如猴跳,有如狮怒,有如龙腾,有如虎跃,形态各异,耐人寻味。奇松古柏粗粗细细,高高矮矮,遒枝横错,郁郁葱葱,令人叹为观止。离鸳不免又生慨叹,甚觉人生如梦。茅屋独居十数载,有喜有忧,喜忧无常,如诗凝笺上,孕于平仄。
离鸳知道,八年前鸦片战争结束后,朝廷增加赋税,横征暴敛,广大贫民饥寒交迫,已纷纷揭竿而起。洪秀全亦是从广东赶至广西,与冯云山在广西组织拜上帝会,秘密进行着反清活动。不久前,洪秀全又发布总动员令,号召各地拜上帝会成员到广西桂平金田村团营。离鸳心想,师傅此去广西,莫非是应洪秀全之约?可他是佛门中人,不应参与红尘俗事。自己亦非拜上帝会成员,去之又有何用?离鸳纵然有万千疑团,亦不敢去求师傅解惑。十多年来,离鸳对师傅言听计从,对于师傅的决意也不敢过问。离鸳深知师傅的脾气,那就是师傅愿意告诉自己的,不用问他自会说,如果师傅不愿意告诉自己的,问了他不但不说,反而会遭受无情的训斥。
按理说,离鸳听到师傅告诉他的这个消息,应该要高兴才对。因为明天,师傅就要带他下山,从而离开这个终年死气沉沉的地方。十多年来,这里的死气沉沉一尘不变,那日复一日的晨钟暮鼓,按部就班的木鱼经诵之声,响彻耳畔的阵阵松涛和昏鸦的啼鸣,以及午夜梦醒时声声入耳的凄切狼嚎,无不在离鸳的记忆中打上深深的烙印。十多年来,除了陶新春叔叔带他去过几次威宁城,偶观人间一隅的繁华,离鸳就没有去过别的地方,其余的时光都是在凤凰山上度过的。确切地说,是在距凤山寺和神仙洞均约半里之遥的这间小茅屋里度过的。武玄方丈把离鸳安置在这间小茅屋里,让离鸳终日看书习字,舞墨弄琴,寒窗苦读中琴声幽幽,花开花落,日出日没,整个人变得郁郁寡欢,多愁善感,单任那一双充满忧伤的眼神就令人为之无比心痛。离鸳终日独坐小屋,人亦变得弱不禁风,手无束鸡之力。有时殇鸯前往小屋,见到离鸳沉默不语,仅用一双忧伤的眼睛盯着她,她就误以为离鸳对她冷漠无情,不喜欢她这个妹妹,为此常常对离鸳拳打脚踢。
想到这里,离鸳忍不住苦苦一笑,这世间竟有妹妹欺负哥哥的。离鸳想,要怪也只能怪师傅偏心,自己与妹妹是孪生兄妹,但师傅却只让妹妹习武,并把上乘的苗家拳法和绝世武功传授给妹妹。自己则只能终日闭门伏案,舞墨弄琴,纵有万丈豪情,亦被几行缠缠绵绵的文字和几声凄凄切切的琴声所淹没。每每只能临风倚窗,对空长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