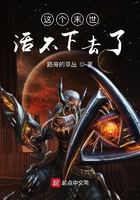心田上的百合花开
在一个偏僻遥远的山谷里,有一个高达数十尺的断崖。不知道什么时候,断崖边上长出了一株小小的百合。百合刚刚诞生的时候,长得和杂草一模一样。但是,它心里知道自己并不是一株野草。它的内心深处,有一个顽强的念头:“我是一株百合,不是一株野草。唯一能证明我是百合的方法,就是开出美丽的花朵。”
有了这个念头,百合努力地吸收水分和阳光,深深地扎根,直直地挺着胸膛。终于在一个春天的清晨,百合的顶部结出第一个花苞。百合的心里很高兴,附近的杂草却很不屑,它们在私底下嘲笑着百合。偶尔也有飞过的蜂蝶鸟雀,它们也会劝百合不用那么努力开花:“在这断崖边上,纵然开出世界上最美的花,也不会有人来欣赏呀!”百合说:“我要开花,是因为我知道自己有美丽的花;我要开花,是为了完成作为一株花的庄严使命;我要开花,是由于自己喜欢以花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不管有没有人欣赏,不管你们怎么看我,我都要开花!”
在野草和蜂蝶的鄙夷下,野百合努力地释放内心的能量。有一天,它终于开花了,它那灵性的白和秀挺的风姿,成为断崖上最美丽的风景。这时候,野草和蜂蝶再也不敢嘲笑它了。
百合花一朵一朵地盛开着,花朵上每天都有晶莹的水珠,野草们以为那是昨夜露水,只有百合自己知道,那是极深沉的欢喜所结的泪滴。年年春天,野百合努力地开花、结籽。它的种子随着风,落在山谷、草原和悬崖边上,到处都开满洁白的野百合。 几十年后,远在百里外的人,从城市,从乡村,赶来欣赏百合开花。许多孩童跪下来,闻嗅百合花的芬芳;许多情侣互相拥抱,许下了“百年好合”的誓言;无数的人看到这从未见过的美,感动得落泪。那里,被人称为“百合谷地”。
不管别人怎么欣赏,满山的百合花都记着第一株百合的教导:我们要全心全意默默地开花,以花来证明自己的存在。
平淡地生活
1980年我考上北师大,9月初的一天我登上北去的火车,从此离开古老潮湿的苏州城。在经过20小时的陌生旅程后我走出北京站,我记得那天下午明媚的阳光,广场上的人流和10路公共汽车的天蓝色站牌,记得当时我的空旷而神秘的心境。
对于我来说,在北京求学的4年是一种真正的开始。我感受到一种自由的气息,我感受到文化的侵袭和世界的浩荡之风。我怀念那时的生活,下了第二节课背着书包走出校门,搭乘22路公共汽车到西四,在延吉冷面馆吃一碗价廉物美的朝鲜冷面,然后经过北图、北海,到美术馆看随便什么美展,然后上王府井大街,游逛,再坐车去前门,在某个小影院里看一部拷贝很旧的日本电影《泥之河》。
这时候我大量地写诗歌、小说并拼命投寄,终获成功,1983年的《青春》
《青年作家》《飞天》《星星》杂志初次发表了我的作品。我非常惧怕和憎恨退稿,而且怕被同学知道,因此当时的信件都是由一位北京女同学转交的,她很理解我,以她的方式一直鼓励支持我。我至今仍然感激她。
大学毕业时我选择去南京工作,选择这个陌生的城市在当时是莫名其妙的,但事实证明当初的选择是对的,我一直喜欢我的居留之地,说不清是什么原因。我在南京艺术学院工作了一年半时间,当辅导员,当得太马虎随意,受到上司的白眼和歧视,这也不奇怪。因祸得福,后来经朋友的引荐,谋得了我所喜爱的工作,在《钟山》杂志当了一名编辑。至此我的生活就初步安定了。
1987年我幸福地结了婚。我的妻子是我中学时的同学,她从前经常在台上表演一些西藏舞、送军粮之类的舞蹈,舞姿很好看。我对她说我是从那时候爱上她的,她不相信。1989年2月,我的女儿天米隆重诞生,我对她的爱深得自己都不好意思,其实世界上何止我一个人有一个可爱漂亮的女儿?不说也罢,至此,我的生活要被她们分割去一半,理该如此,也没有什么舍不得的。就这样平淡地生活。我现在蜗居在南京一座破旧的小楼里,读书,写作,会客,与朋友搓麻将,没有任何野心,没有任何贪欲,没有任何艳遇。这样的生活天经地义,心情平静,生活平静,我的作品也变得平静。唯一让我焦虑的是我辛劳了一辈子的母亲,她患了重症住在医院病房里。
其他还有什么?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一朵花的快乐
那天,我正在我家的邮箱前取信,老远就看见邻家的小姑娘简爱正好从校车上下来,蹦蹦跳跳地朝家里跑去。
当她走到我身边的时候,她停下脚步,然后笑逐颜开地对我说道:“您猜怎么样?下个星期我们班将要在学校演出一场戏剧呢!里面有一个像神仙一般的公主,她有一头闪亮的长发,一套粉红色的长裙,漂亮极了。不仅如此,她还长着一对漂亮的翅膀,手里还拿着一根金光闪闪的魔杖呢!”
说到这儿,这个年仅7岁的可爱的小姑娘又高兴地蹦来蹦去,那天使般的脸庞也因为喜悦而备显生气勃勃。
少顷,她又气喘吁吁地宣布道:“我也出演了一个角色!我们演的是一出音乐剧,在剧中,我们都要唱歌的!”
“哇!像神仙一样的公主!”我惊叫道。看着眼前这个天真可爱的小姑娘,听着她那稚嫩的话语,我的心不禁猛地一颤,我知道,我内心深处的某种东西已经被她深深地触动了。
简爱紧抿着嘴唇,微笑着使劲点了点头:“嗯,是的,一个神仙一般的公主。”
说到这儿,简爱模仿起她想象中的那位神仙公主的样子来。她首先旋转起来,然后,她用双手轻轻地滑过身上,就好像是滑过她想象中的那件粉红色长裙似的;接着,她又用双手轻轻地抚摸着她的肩膀,就好像是在抚摸她肩膀上的那对看不见的翅膀似的。做完之后,她就立刻转过身,蹦蹦跳跳地向家中跑去,她一边跑一边还快乐地唱着歌,尽管她唱得都跑调了。
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里,有一天,当我又一次站在我家的邮箱前取信的时候,我注意到简爱的妈妈杰德正站在校车站上等待着女儿。不大一会儿,校车来了,简爱兴高采烈地跳下车来,经过我家门口的时候,她们看到了我。
于是,简爱便转过身来,蹦蹦跳跳地向我这边走过来。“您猜猜怎么样!”她笑容满面地对我说道,“今天,我们班的音乐剧举行了一次预演!”看她那欣喜若狂的样子,我理所当然地认为她一定是得到了她梦寐以求的角色。
“哦,那你扮演的一定是那位漂亮的公主了!”我高兴地说。
“不是,我扮演的是一朵花儿!”简爱摇着头纠正我道,“他们选我扮演一朵花儿!”
看着她那天真而又严肃的样子,我感到非常有趣,但是我却极力地掩饰着,生怕自己会笑出声来。“一朵花儿?”我故作惊讶地问道。
“是的!”她笑着向我解释道,“到时候,我的头上要戴上紫色的花瓣,身上要穿上绿色的紧身衣和紧身裤。”说到这儿,她不禁开始模仿起头上戴着花瓣的样子来,那神情就好像是几天前她为我模仿头上戴着神仙公主的冠冕时一样。
“哦,真是棒极了!”我向她表示祝贺道。由于我知道她是多么渴望能在剧中表演歌唱,于是,我就问道:“那么,在剧中你唱的是什么歌呢?”
听我这么一问,她不禁睁大了眼睛,天真无邪地注视着我,答道:“哦,在我们这出戏里面,花儿一定要保持安静。”说到这儿,她轻轻地把她小小的手指竖在嘴巴前面,做出保持安静的动作。
当她蹦蹦跳跳地跑进她家的车道的时候,她的妈妈杰德把目光从我的身上转移到了她的身上,然后苦笑着摇了摇头,说道:“她总是会做些令我感到惊奇的事情。您瞧,她们班上几乎每个孩子所扮演的角色都有台词说,或者有歌唱,只有我们简爱选择了扮演一朵默默无闻的花儿。可是,她还照样那么高兴!”
“哦,这也许就是孩子看世界的方法吧!”我感慨地答道,“他们对世界的认同度是多么宽广,他们的接受能力又是多么强啊!”
“是的,这真是令人可喜的事情。”杰德赞同地点点头道,“记得有这样一个典故,说是同样半杯水,悲观的人说还有半杯是空的,而乐观的人却说还好有杯水呢。简爱就是领悟了这种看问题的诀窍。每当我感到沮丧感到气馁的时候,我只要和这个快乐的小精灵待上一会儿,思想就会立刻豁然开朗。”
“那么她快乐的源泉是什么呢?”我问道,“在过去的这些年里,我一直在关注着她,我发现她总是那么乐观,就好像她总是在‘赢’似的,任何一种结局对她而言都好像是胜利。您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一切的呢?”
“她就是这样的。”杰德答道,“不过,有一件事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
现在看来,那天晚上您带我去商会参加的那个招待会对我来说真是意义重大啊,它让我领悟到了许多。”
听她这么一说,我顿时想起来了。那是四年前我第一次见到杰德不久以后发生的事。
那时,她们一家刚搬到我们这个地方,与我成了邻居。为了表达对她的友好,我带她去参加了一个在商会举办的招待会。按照规则,在招待会上,我们每个人都要向别人介绍自己,介绍自己的所从事的工作以及自己在工作中所处的职位。
“我是第一世纪银行的行长。”这时,人群中有一位看上去非常高贵的绅士首先说道。
“哦,真是太了不起了。”其他人纷纷啧啧称赞道。很显然,他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接着,一位衣着潇洒的年轻人说道:“我是边缘电脑公司的总裁。”于是,人群中又一次响起了“啧啧”称赞声。
当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我身上的时候,我自我介绍道:“我是大学研究生院的教授,还是教育和职业发展公司的总裁,我们公司是一家全国性的咨询公司。”
“哦,真是不错。”大家纷纷赞道。
当我说完之后,正好就轮到杰德最后一个做自我介绍了。这时,大家纷纷把目光转向她,并冲她点了点头,示意该她说了。
为了参加这次聚会,杰德穿了一身漂亮的鲜红色丝绸套装。“我的工作就是待在家里专职照顾我的女儿。”她介绍道。
还没等杰德继续往下说,那位电脑公司的总裁便不屑地嘟囔了一句:
“哦,原来只是个家庭主妇。”说完,他很老练、很巧妙地侧过身去,背对着杰德,和站在他左边的那位银行行长聊了起来。
当自我介绍结束之后,人们便开始自由选择自己感兴趣或者认为值得进一步交谈和询问的对象。最后,原来的那一大群人分成了三个小组,然后,大家就开始互相交流起来。当然,只有杰德除外。
“你瞧,”杰德回忆着那天的情景,然后坦言道,“在人们的眼里,成为一名总裁的重要性很显然要比成为一名——用那个男人的话说就是‘只是个家庭主妇’强许多许多。他们所关心的只是‘总裁’和‘家庭主妇’的身份与地位的问题,而对于一个家庭主妇在家照顾小孩所付出的辛劳却全然不感兴趣。不过,说实在的,那次的招待会对我来说真是一次很好的经历,因为那个人对我明显的排斥刺痛了我,而且有时候还会让我反思一下:我放弃名利双收的职位去做全职家庭主妇的决定是否正确。我深知帮助简爱形成这样一种观念很重要,那就是让她明白不管别人怎么看,她所做的事情都是很重要的。我要让她明白,生活中她既有被选为扮演仙女一样的公主的时候,也有像今天这样扮演一朵默默无闻的小花的时候。我希望她无论在哪种情况下都快快乐乐。虽然我非常希望简爱将来也能够成为一位总裁,但是,我并不希望她把这个用作衡量自己是否快乐的尺度。”
的确如此,在扮演一朵默默无闻的小花中寻找快乐,发现潜力,比因为没有扮演成光彩照人的唱歌的公主而感到失望要更加有意义!
君心可晴
“君心可晴?”这是我通过手机短信问候远方朋友的一句话。很快,朋友就回复了,居然是:“君心可晴!”
对着阳光微笑,再一次感到汉语的无限美好——我殷勤地探问朋友的心空是否晴朗,当然,这里面也蕴含着我的一个未曾明言的祝愿,那就是,唯愿朋友的心恰如那“蓝蓝的白云天”;朋友复我时,巧妙地将我原先用以表疑问的“可”字改换成了表“可以”的“可”,用不容商榷的口吻告诉问候者,你的心空是不应该有阴霾与云翳的!这有硬度的祝福,恰如那一句“你必须幸福!”当然,这个机智迅捷的回复也透露出了这样一层意思,那就是,此刻,祝福者的心空亦未曾落雨。
走在阴晴无定的四季,老天的脸色就是变给你看的,你掌控不了这一切,你所能够做的就是被动地接受,接受微风惬意的吹拂,也接受狂风肆虐的鞭挞,接受那“润如酥”小雨的多情爱抚,也接受“大如席”雪片的无情扑打。卫星云图永远做不成你的“解语花”,由着你的心性儿派送阳光抑或派送风雨,它只是预先知会你它将要怎样怎样,你断然没有“民主参与”的机缘。
但是啊,你可以做自己心情的主子!
我曾经有一个同事,经年累月地做着自己心情的奴才。他应该是个典型的“胆汁质”的人吧,凡事不可遏抑,激愤的咆哮几乎成了他生命的常态,发作过后就往嘴里塞“速效救心丸”。于是,办公室便总弥漫着一股驱不散的那种丸药所特有的味道。他似乎也意识了自己的心情需要拯救,便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下压了一幅自书的座右铭:“愤怒,等于用他人的过错惩罚自己。”大约在这位仁兄压了那名言一周之后,单位聘请一位专家来做报告,那专家出语惊人:“一些人总是喜欢把自己做不到的事儿编成座右铭,供起来。”与“胆汁质”同一办公室的人全都憋不住哗然大笑。散会之后,“胆汁质”怒吼着,连玻璃板带座右铭全部痛而毁之。
坏心情不需要任何理由,好心情也是。
我博客的“友情链接”只链接了一个人,一个与我同姓的爱笑的天使,总觉得她是为了开发我的好心情而闯进我的世界的。身心俱疲苦不堪言的时候,我就遁入她的天地,听她讲自己在一个毛绒动物玩具厂辛苦劳作时怎样靠着居里夫人的故事取暖,看她面对阿尔卑斯雪山时兴奋地宣称要“站起来”拍照。她总是笑靥如花,唇膏美艳,皮鞋锃亮。她每一篇博文后面都有无数跟帖。我注意到,在一个特殊的日子里,她在凌晨三点发表了新博文,热心的人们问她:“这么晚了还没睡?”“这么早就起来了?”“因为这个日子特别所以睡不着吧?”我也跟了帖,说:“姐姐让我感到了这个世界的暖。”——那个日子是“国际残疾人日”,这个爱笑的天使是张海迪。
如果发明一个“心情按钮”,我想没有人会不愿意将按钮永远调到“愉快”的位置,而修炼心灵的慈悲度、宽阔度、高远度、明亮度,无疑是有助于“心晴”的。在生命的列车上,我们说不清自己最看重的人或物会在何时下车,连同我们身体的某一部分,都有可能不会陪同我们走到终点,只有心情,是我们一生不离不弃的契友,是与我们的生命“等长”的东西。即使我们没有安装“心情按钮”,我们也可以在哪怕是阴雨连绵的日子里悉心营造一个“局部晴天”。
心儿晴好,你才能活得美,活得赚!
——君心可晴?
——君心可晴!
像她一样姿态从容
楼下有个花店,一个老太太卖花。店的名字很奇怪,叫“花开花”。小小的门面,门前挂着一副竹劈滇石绿的对子,改的鲁迅先生的两句诗:犹有(不是“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心知(不是“由之”)。没有横批,门楣上常常悬着一瀑悬崖菊,冬天则是一个大头朝下的绿皮红心萝卜。
老太太一年四季裹着个大披肩坐在花丛里织毛衣,腿脚好像不大利索了,但身材娇小慈眉善目。替她进货的年轻男子叫她姑妈,挺拔开朗,开了辆很帅的吉普车——隔三差五捎点儿零食日用的东西,有次竟拎了一对美丽的珍珠鸟。常见她收到世界各地的明信片,但没见她有什么别的亲人。
不知为什么,这老太太常让我想起林徽因、杜拉斯什么的。她的花便宜得根本不能讲价,她从来不说身世,偶尔谈文论画。说《红楼梦》里宝玉给平儿搽的胭脂里的紫茉莉,其实就是夜来香;说起周天民的花卉画谱,线条清丽,文字干净:“木香,春末新叶生蕾,初夏开花,花开高架,满栅生香,亦称锦栅儿。”简直就是诗嘛!我曾疑心她是位植物学家,或者学过园艺,但她的侄子悄悄告诉我,姑母在师大教了40年英语呢。当我低头嗅一捧新雪般的满天星,老太太问我:“知道它的英文名字吗?”我摇头。“Baby"s breath,婴儿的呼吸啊——多美。”
她的身体一天比一天衰弱,但精神还好。周末我常常煮汤,一个人喝不完,就分一半端到店里去。暮色渐合的窗口,我看到她正专注地侧着耳朵聆听着什么,脸上有种奇异的微笑,“听!”我听了一会儿,“什么?”“鸟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