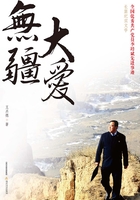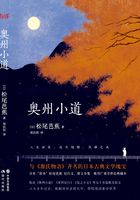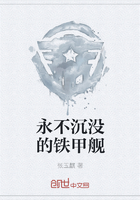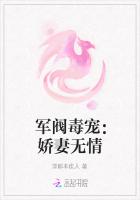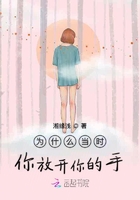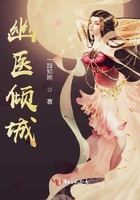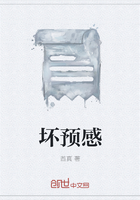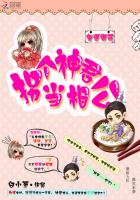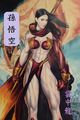白杨木制作的翘头木鞋是中古时期荷兰平民必备的日常用品,就好像我国江南农民的蓑衣、海南渔民的斗笠一样。荷兰的西北部濒临北海,有一半的国土属于堤坝围垦地,地势低于海平面好几米,全国最高点仅300多米。加之境内多雨,很潮湿,那时的荷兰老百姓干活时总是穿着这种木鞋,它不渗水,防潮,又容易清洁。像小船一样的翘头,造型可爱而美观。现在的荷兰人已经不怎么穿它了,作为荷兰的国粹它流传下来,成为各国游客们喜欢的工艺品。木鞋厂专门加工各类型号的木鞋,大得像小汽车一样,小的只有拇指一般大。作为荷兰的旅游景点,这里的生意还红火得很呢,它们的产品已从踩泥的用具变成游客的爱物,每只鞋真像一只只翘头木船一样游向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风车是人类最早发明的动力机之一。而荷兰的风车是主要用于排水的中空立式风车,通过两极传动,带动勺形轮将水舀到高处。这种风车的造型非常艺术,它兀自立在原野上像一支舒展四个花瓣的巨大花朵。当它随风舒缓转动的时候,就好像在昏沉中思考,又像在奔跑中睡着了。
以前只知道著名的威尼斯是座水城,到了阿姆斯特丹一看,它全然是一个被桥连接的水上城市——城内有100多条运河,河上有1200多座桥——比威尼斯的桥还要多呢。一个城市有那么多的桥,就好像平静的睡眠上长了很多梦。这些桥是城市的美丽饰物,而蜿蜒的道路则如同绳线一样将它们穿在了一起——阿姆斯特丹就像是一串层层叠叠的大项链。
在这里最让一个中国人感到亲切的是,城市主要的交通工具居然是自行车——而在其他的欧洲国家自行车多被当作运动器械用来锻炼身体。阿姆斯特丹的道路多是中古时期的马车道改造而来的,很窄,而且拐来扭去的,还常常有陡坡。政府提倡市民骑自行车,既减少空气污染,又对健康有利,也许还比汽车快捷方便。那里人们娴熟的车技可以和自行车王国的中国人媲美。
小尿童
从荷兰到巴黎必须经过比利时和卢森堡,这一天的经历被称作是“一天吃三国”:早餐在比利时,午餐在卢森堡,晚上就到了巴黎。
在欧盟国家旅行是很便捷的,一个签证走到底,不需要再办理出入境等手续了。欧元使用之前各国的货币,如马克、法郎的纸币都可以在诸国相互通用。那里的人们也大都能用英、法、德语交谈,我们很难分辨他们到底是哪国人。
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我们专程去看了那座挤在街角里的著名的“小尿童”,他是比利时的英雄象征。关于他,最多听到的是说他机智地用自己一泡清澈的童尿浇灭了一个导火索,从而避免了一场残酷的战争。于是他的雕像就是他痛快撒尿的样子,非常顽皮。
当各国首脑、名人访问比利时时,都会给这个身高不足1米的顽童赠送量身定做的服装,有古典的,有现代的,带着各国的风情。据说小尿童有成千上百套各种风格的服装。可他就喜欢光着身子,无休止地撒尿,春夏秋冬都是一个姿势。到了节日,他还能尿出美味的葡萄酒呢,人们争相品尝。据说中国代表团也曾送给小尿童各种中式服装,我们看到小尿童的那次,他正好穿着一身丝绸的唐装冲着众人撒尿。
老头君特与大宝贝卡西木
那天我们终于到达了巴黎。
巴黎,这个名字对我几乎一直都不具有真实性,它好像不是地图上标着“巴黎”的那个地方,而是文学艺术家们共同杜撰出来的一个并不真切的艺术作品的背景。
可就在这梦境之地,我的身体居然失去了健康的状态,庸常到要闹病了。在如此难得的一个时刻,我躺在车上,用卧着的姿势穿越我一生中相遇一次的巴黎,就像鱼视而不见地游过任何一片水。
窗外天空明澈,几朵飘忽的轻云像是永远厮守着巴黎这个巢窝,从未离开过。可它们并不向我说什么。
我不能像其他的人一样登上那个叫埃菲尔的人修建的铁塔,去看一个真实的巴黎了,真是沮丧。
车上剩下三个人,我和两个职守的司机。
他们是两个德国人,年长的是个灵巧的小老头,有个典型的德国名字,叫君特,和199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同名,可他一点也不知道这名字在全世界已经多么响亮。
君特身材短小,动作敏捷,开车的时候神情非常专注。奇怪的是他一点都不能像其他欧洲人那样使用一点英语,总是用晶亮的目光和一成不变的笑容向我们传达他的热情和友善。
副司机是个26岁的小伙子,身高体健,臂膀宽阔壮硕,那肌肉的流线让人联想到一种越野车的车头,连光泽都是相似的。而当他转过身来时,却露出一张地地道道的娃娃脸,目光清澈单纯,一笑两个酒窝绽开,好像他这时不想和你认真,把另一种相称的表情藏起来了似的。这使他得到了一个很恰当的绰号:大宝贝。他听到后放平了笑窝,尽量严肃地用英语解释说:“我不是大宝贝,我叫卡西木。”然后把证件给我们看。好像他要认可了这个称呼,今后就真的永远也长不大了。
卡西木很惊讶我在巴黎的放弃,可又对我留下感到兴奋,因为每次我们下车总是剩下他和君特看车,从没有人与他们共度等待的闲暇。
他走过来递上一条毯子,然后满意地微笑,好像对自己的有用很欣赏。
“头疼?”他问。
“不,这里。”我指指心口,摆出苦脸,做呕吐状。
这个卡西木突然眼睛恶作剧地一亮,极其夸张地“哦”了一声,然后说:“你的肚子里有小宝宝了!”
我愣了一下,看出他百无聊赖中的好兴致。
卡西木很兴奋,欢快地说:“小宝宝是我的吗?”
他像惯常的西方人一样,用性开了个玩笑。我尽量收敛起惊讶的表情,不知所终地看着他。
居然没有在一个古老国度的东方女人面前受挫,他显得很鼓舞,竟然得意忘形地搬着他的粗手指头假模假势地算起来:
“是在哪儿呢?莱比锡、海得堡、阿姆斯特丹……”
他将我们一路上经过的城市都数了一遍,然后用他那与这玩笑毫不相干的儿童目光询问我。
“巴黎。”我说。这是我们今天到达的地方。
这回轮到他惊讶了。这更让他高兴得手舞足蹈。
大宝贝奔到君特面前,居然对那老头转述刚才的一切。要知道他们的年龄是两代人的差距。
君特听过后,先是愉快地大笑,然后把脸转向我,狡黠地闪闪眼:“小宝宝应该是我的吧?”
在这么短的瞬间两位德国人都让我感到很大的意外,真不知如何应付。
君特更加愉快地笑着,展现着整个旅途中少有的表情。我心里只是纳闷,两代人居然开同一种水平的玩笑,而且充当同样的角色。
君特约有六十岁了吧,有点谢顶,虽然依旧灵巧健康,可在一般人的眼里仍是该称作“老头”的,他也一定有孙子吧。我想,如果把君特换成一个与他同龄的我的中国男同胞,那他看着卡西木的表情一定是含笑不语,像看一幕多年前的旧电影。他不会像君特似的把自己搭进去,他会认为那样太冒失了。
君特不同,尽管我不习惯他,但卡西木信任他,一点也不剥夺他,卡西木在讲笑话的时候不就平等地对待他了么?君特的发言在他眼里不是很正常么?如此看来,在这一点上我们中国人和他们是很不同的,我们自己放弃的和相互剥夺的也许太多了,而且是在无意和善意中。
在巴黎我们有宝贵的三天时间,其中这一天我什么经历都没有,只在车上和“老头”君特、大宝贝卡西木一起等待。
巴黎印象
想说清巴黎是困难的,已有的铺天盖地的游记和评介比我的了解要全面系统得多,我只能把自己的零星感受只求随意、不求正确地表达出来。因为不管谁说什么,巴黎就是巴黎,永远是它自己的模样。
巴黎很美丽,优雅的古典意味和前卫的现代感完美地结合着,是别人几百年都难以模仿的。
卢浮宫是个聚宝盆。每天全世界有多少人在朝着这个方向出发,而且这种向往的热情世世代代也不会泯灭,只会随着卢浮宫的日益古老而与日俱增。宫内的收藏难以一一历数,每一件收藏的价值也不是金钱所能衡量的。单说三件镇宫之宝——“断臂的维纳斯”、“无头胜利女神像”和“蒙娜丽莎的微笑”,拿德国导游的话说用多少钱也是不会出卖的,就是用整个美国来换也是不可能的。卢浮宫不仅是巴黎人、法国人,甚至是整个欧洲人的骄傲。
欧洲历史悠久、文化发达,这里的人从骨子里有点蔑视美国人,认为他们的文化多是快餐式的,是没有文化的文化。
英国作家王尔德写过一篇《美国印象》,时间是二十世纪初,他说他看到的美国是现存的最喧嚣的国家,只有技术和工业。清晨人们不是被夜莺婉转的啼声唤醒,而是被机器的轰鸣声惊醒,人们的行色都是匆忙和焦虑的。他认为这样的国家很难诞生真正的音乐和诗歌。他还举例说:有个美国的艺术经销商,从火车货运处收到了欧洲发来的货物,他发现维纳斯的胳膊没有了,很气愤,于是起诉车站的野蛮装运,要求赔偿损失。王尔德最后说:“而更令人惊奇的是,他还赢了此案并获得了赔偿金。”
王尔德眼中的美国就是这样的,他的看法在当时的欧洲一定很有代表性,但那已经是将近一百年前的事了。
王尔德在《美国印象》里有几句话特别让我惊讶,我曾重复看过很多遍。这是一个唯美主义诗人面对被称做天堂的美国,无意中对中国人发出的赞叹:“唐人街是中国劳工的聚居地,是我曾经到过的最有艺术性的城区。古怪、犹豫的东方人……他们无疑都是很穷的,但和他们相关的事物无一不美。挖土工人……用精致得像玫瑰花瓣那样的中国茶杯喝茶……而中文账单是写在宣纸上的……犹如一个艺术家在扇面上蚀刻的小鸟群。”
王尔德所看到的那种优雅的中国传统文化被他描述出来的时候,甚至对我这个中国人来说也是陌生而新鲜的,现在我们几乎也很少能在日常生活中感觉到它了。原本作为一门极其普及的艺术——书法,现在在中国也仅存于少数爱好者之中,而出生于、成长于六十年代之后的中国人大多已失去了这样的修养,尤其是在电脑普及的当今,我们所看到的新新人类用笔写在纸上的汉字,不再像“艺术家在扇面上蚀刻的小鸟群”了,基本上和外国人写的中国字差不多了。
凡尔赛宫是法国的历史名胜,被称为建筑杰作。但如果不作为文物和历史遗迹去了解的话,我是不喜欢的。
凡尔赛宫曾经是法国几代皇帝的宫廷,是表现绝对王权的硕大舞台,反映了当时皇室的浮华和穷奢极欲。它的室内墙壁和屋顶几乎堆砌了所有的色彩和装潢的方式。无论是哪面,墙都毫无例外地在上面拥挤着雕塑、壁画、浮雕、镂空图案,凸的、凹的、金的、银的、红的、绿的……你不需要观察它有什么,你只需要观察它没有什么。虽然金碧辉煌,令人目眩,但实在是毫无节制,给人填堵。显示的是财富,是各种手段的堆加,很难说有一种纯粹的艺术美感。这个宫廷里曾经发生的故事倒是让人不陌生的,阴谋、篡权、乱伦、谋杀、享乐、挥霍,这些内容和相距遥远的中国宫廷如出一辙,出奇地相似,就好像法国皇室和中国宫廷沟通过并达成了协议,分别在东方和西方为世界上演同样的故事。
著名的塞纳河波光粼粼,慢慢悠悠地向前移动着它亘古不变的梦境。悬铃树在四月的开始正要冒出它的叶子,空气中都是闲散的味道。
巴黎养狗的人很多,他们的爱狗也是世界闻名的。据说欧洲人喜欢养狗是因为人情淡漠,孤独难耐。而狗通人性,忠实可靠。在欧洲各个国家的街头到处都是牵狗的人,男人、女人、老人、青年,各牵一狗,像牵着情侣和老伴儿。他们牵的往往不是中国人喜欢的那种哈巴小狗,而是高大的、躯体庞然的大家伙。有时一个纤细美丽的女孩同时牵着三四只面目怪异、形态不同的大狗,那种组合看上去很奇特,却又其乐融融,就好像他们和我们生活的不是一个世界。
在巴黎街上我看到一家狗的美容店,门面漂亮,窗明几净。里面的美容师穿着洁白的长褂,手里拿着锃亮的剪刀,一只长毛狗像个小姐一样蹲在升高的椅子上,乖乖地接受清洗、剪发型、吹风、喷香水,一看就是美容店的常客。只是不知道它会不会在某一次突然说:先生,我不满意啦!
除了把狗像人一样地关爱以外,还有人把自己变得更像狗。
有一天在巴黎的一条街上,我看到一只怪头怪脸的大狗走上桥来。它的毛很特别,不是一根一根的,而是一柱一柱的,比手指还粗。头上的柱毛一直纷披到脸上,狗的眼睛从狗毛帘的缝隙中看出来,鬼鬼祟祟的。而全身的柱毛披落到地下,看不到狗腿,就好像这只狗故意把自己藏起来了。它就这样拖着一身脏毛仓皇地、孤独地走着,我以为它是一个失落了主人的丧家犬。离它十来米开外,毫不相干地走着一个小伙子,看到他的背影我一眼认出他是狗的主人。他的长发拖到小腿——全是用他爱犬的毛一柱一柱接的,形态色彩毫无二致。只是他立着,狗趴着,一前一后,像有着共同遗传基因的兄弟俩。他们互相模仿,说明互相爱慕。
狗多,****就成了巴黎的一害。但人们对狗的容忍比对人的容忍要多。人不可以随地吐痰、扔垃圾,但狗可以随地屙尿拉屎。它屙不择地,堂儿皇之,让我们这些中国人倒不习惯了。因为在我们的眼里,洁白的****还是屎,踩上去依然恶心。那天我们走在巴黎的红磨房附近,突然听到有人大喊一声:“小心****!”随处都可见这种狗造地雷,而当地人安之若素。
不过他们终不至于爱屋及乌至此,听说巴黎也在治理****。
但丁吃鱼
但丁应一贵族之邀在威尼斯做客,席间主人以鱼待客。但丁盘中的鱼很小。他不快乐。于是他拿起那条鱼放在耳边听。主人很诧异,问他在听什么,但丁回答:“我的父亲死于亚德里亚海,我在问这条小鱼父亲究竟是怎么死的。”主人问:“它告诉你了吗?”但丁答:“它说它太年轻了,只有它的祖父和父亲才知道。”主人会意,给但丁重新换了一条大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