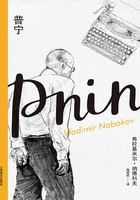诃黎布石回到府邸,径直来到李加的房间。这是套独门独院,三间北房为李加所住。里面陈设考究,挂满了画稿、墨迹,摆放着文房四宝,墙上悬挂着箜篌、五弦琵琶。四围清幽静宓,是个修身养性的佳所。
诃黎布石问过仆役,说是李加不在室内。他好生纳闷。忽听后院锣鼓喧天,人声鼎沸。他知道,这是卫兵们在演练“苏幕遮”呢。吐屯夫妇要回来了。各个府邸衙门在他们进城的时候,都要击鼓奏乐,歌舞相迎。因而这两天,走到哪里都可以闻听管弦伎乐的悦耳之音。
诃黎布石怀着一线希望来至后院,啊!“苏幕遮”排得正热火呢!
八个人戴了龙、虎、牛、羊和凤、雁、鹅、雀的假面具,披着五颜六色的兽皮、羽皮,随着鼓乐的节奏,腾舞跳跃,交错变换。几个人提着盛水的油囊,把水泼在他们身上。他们周身滚动着闪闪发光的水珠,随着剧烈的跳跃,迸溅在干燥的土地上。乐队排在一侧,伴奏的乐器有大鼓、小鼓、琵琶、五弦、箜篌、笛子,铿锵嘈切,洪心骇耳。
“苏幕遮”又叫“乞寒舞”,在西域各地颇为流行。尤其是在诃黎布石的家乡龟兹,更为老少男女所喜爱。《周书·宣帝纪》载:北周天元大象二年(公元580年),乞寒舞传入大唐。《唐书·张说传》云:“自则天末年季冬为泼寒胡戏,中宗尝御楼以观之。”两京而外,并行于各地,是以中书令张说上疏谏止,有云:“裸体跳足,盛德何观?挥水投泥,失容斯甚!”
因而,至开元元年(公元713年)下敕禁断。
所谓“乞寒”,实为乞雪。西域夏季炎热少雨,庄稼和人畜用水多赖山上积雪融化,因而雪厚意味着丰收。人们乞雪,也就是乞求来年有个好收成。各地的“苏幕遮”有的入冬之前举行,有的在夏秋之季举行。年深日久,这也成了一种传统的娱乐内容。
诃黎布石看到这龙腾虎跃的场面,早已按捺不住。他从来都是“苏幕遮”的活跃分子啊!可是,又有点后悔。李加哪会有这个心情呀?
他向人群望了一圈,果然不见李加的影子,就想踅身返回。
还没挪动脚步,被“苏幕遮”的扮演者看见了。他们哪敢冷落将军呢?唿啦一下,就把他围到了中心。鼓乐吹打得格外急骤了。人们相互笑着,叫着,闹着,欢迎主人卷进欢腾的人流。两个头戴假面的舞者拿起长长的羂索、搭钩缠住了诃黎布石,邀他共舞。若在平时,这正好显示他的机智、灵敏。他可以跟他们跳一阵,玩一阵,可以精猴似地溜脱羂索的绊绕,逃之夭夭,引起观者的喝彩。
然而今天他心不在焉,跳过一会儿,就想溜走了,可怎么也难以脱身。执索的舞者实在是个狡猾的舞伴,他死死围绕着诃黎布石,封死了他脱身的企图。诃黎布石又气又恼,动作失谐,一脚踏进泥淖里,跌倒了。军服沾满泥污,双手黄浆淋漓,观者哗然大笑。两个舞伴扔下搭钩急去搀扶他。
他刚一起身,举拳就打向执索者。幸好另一个人手脚利索,及时托住了他的胳膊。
执索者摘下牛头假面露出冒着热汗的脑袋。诃黎布石一瞧,傻眼了。不是别人,正是他要寻找的李加。
“是您?”
“没想到吗?”
“你对‘苏幕遮’倒很内行?”
李加笑得十分开心:“不管在哪儿,只要遇上‘苏幕遮’大会,我是宁肯推延行期,也不肯放过的。将军,您说是龟兹人,我看不像。”
“怎么?”
“龟兹人都是‘苏幕遮’的行家,哪儿像你,绊倒在地还要举拳打人的?”李加诙谐地说着。
诃黎布石面红耳赤,一句话也说不出。围观的人都掩嘴窃笑,敢和将军这样谑而不虐的,只有这位“术士”啊!
诃黎布石和解地笑着说:“今天让您见笑了。我在到处找您啊。”
“找我?”
“呆得无聊,找您下棋。”
李加信以为真,就随着来到了诃黎布石的逍遥斋,围着一张精雕的石桌双双坐下,摆起了围棋。
“吐屯夫妇什么时候到呀?”开枰不久李加先发制人地问。
“天知道。”诃黎布石对这个话题毫无兴趣。
李加并不在意——他从士兵的嘴里已经知悉诃黎布石那段难言的隐痛。他想摸清的是张雄到底是何种样人,便故作好奇地问:“听说吐屯夫人是左卫大将军的掌上明珠?”
“掌上明珠?”诃黎布石冷笑着反唇相讥,“是。是很贴切的比喻!”
“怎么?”
“一件值钱的玩意儿。”
“大将军的女儿和吐屯大人结亲,不也是攀龙附凤吗?”
诃黎布石手拿棋子,停在空中,对于这个“是”与“不是”,一句话哪能说清呢?他陷入了沉思。猛然,他眼睛一亮:李加为什么对这件事如此关注?他干脆把棋子放回绣袋,直截了当地问起李加。
“你忘了,我是术士。术士是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李加随机应变地说,“来,下棋,您干嘛收起来?”
诃黎布石依然瞧着李加,没说话也没动弹。李加感到他有点不同往常,就避开他咄咄的目光,从盘子里揪下了枝葡萄,一个一个地放到嘴里。短暂地沉寂之后,诃黎布石轻声地、清晰地说道:“您不是术士,也不是商人,您是唐朝使节!”
李加神经一紧张,一颗葡萄从嘴边掉进袖管里。他稍稍镇定了一下,作出受惊的样子说:“将军,您可别这样开玩笑,你是想把我送进牢房吗?”
诃黎布石走到窗根,左右望了一眼,转过身来说:“刚才大王找我了。”他把声音压得很低,表情极为严肃,“问我在一眼泉是否救过一个商人?”
“您就照实说吧!”
“我说没有。”
“您敢欺骗大王!”
“因为他说那不是商人,是唐朝使节!”
“大王何以知道他一定就是唐朝使节?”
“他没说。”诃黎布石走近桌边,抓住李加的手腕:“可我知道,您确实是在一眼泉得救的!”
李加不紧不慢地说:“将军怎么断定,除我之外,再无别人途经一眼泉?”
李加神色泰然的回答,把诃黎布石气得脸色发青,肚子鼓胀,又不知对谁发泄。是啊,道经一眼泉的商人每日驼铃相闻,肩影遥见,怎知就是李加?然而,诃黎布石又想,“五十来岁,西域人模样”——说的不就是这个李加吗,难道还有第二个?可是怎知没有第二个呢?诃黎布石就这样颠来倒去地想来想去,越想越气。他恨自己无能、鲁莽,又恨李加——他断定他是唐使,虽然他缺少真凭实据——对自己的心情太不理解。住在自己府邸,又是自己冒死搭救的,却偏偏与自己玩起了“捉迷藏”!
诃黎布石叉着腰在屋里闷头走了两个来回,“咚”地停在李加面前,伸出双臂掐住李加的肩膀,把他从座位上拎起,脸对脸地瞪着他,焦躁地说:“你到底是谁?你要对我说实话,不然的话……”
李加看着急得发疯的诃黎布石,内心也在掂量:诃黎布石耿直,忠厚,出身贫寒,对于高昌王、西突厥阻遏丝路、称霸西域素有成见,是可信赖的。但要把真情向他和盘托出,为时尚早,万一事出意外,岂不毁了大计。
李加迅速掠过这些念头,对着那张由于激动而涨红扭曲的脸,不得已地故作俏皮地说:“我已说过多少次了,再说,就得到都官府都官府:掌刑法、狱讼之事。了!”
“我要你说,说实话!”
“长安上一品绸缎庄……”
诃黎布石重重地喟叹一声,没待说完,就把他推到座位上,面壁而立,从心底发出了自语:“您在哪里呀?您需要帮助,需要庇护,一旦落入他们之手,就凶多吉少了。”
正当这时,白斥候走了进来说:“布石将军,有人求见!”
“谁?”
“傅加斯。”
“傅加斯先生?快请。”
傅加斯的到来像是刮来了一股东风,吹散了诃黎布石脸上的愁云。
他和傅加斯是至交。对于这位远道而来,长年累月奔波在丝绸之路的外国客商,他是很敬重的。而且,傅加斯常去长安,断断续续住过多年。他对长安的向往、仰慕之情,部分地也得益于傅加斯的描述和情绪的感染。这位不速之客的到来,会给李加增加一位志同道合的伴侣呢,还是揭掉李加那身变来变去的外衣呢?
傅加斯的到来,惊得李加差点喊出声来。他和傅加斯今春还在鸿胪寺舍下举觞畅饮,畅谈通宵。怎能暗示傅加斯在这不期而遇的时刻,为他的身份保密呢?
这太难了,不如暂避一时。可是,诃黎布石拦住了他,把他按在椅子上,就去门口迎客。
李加索性走到窗前,若无其事地向外望着。果见白斥候引着傅加斯离开林荫道,绕过圆形花坛正向这边拐来。傅加斯还是那副“笑面虎”的面孔,两只牛眼滴溜溜地转个不停,扫瞄着周围的一切。对什么都好奇,都爱发问,好像随时准备做一笔你意想不到的生意。他的视线扫过这扇敞开的窗户,直视着立在门口的主人,离的老远就喊叫起来,两条长腿也紧跑了几步:“布石将军,知道了吗?又有变故了!”
“什么变故?”
“哎呀呀,这位高昌王呀!”傅加斯连说带比划,激动地和布石嘀咕了半天,这才跟着布石向里屋走来。
李加鼓足勇气,先自迎了上去。
诃黎布石指着李加,向傅加斯介绍说:“我给你结识一位朋友……”
不等诃黎布石介绍,李加先已上前几步施礼,自报家门道:“敝姓李,长安上一品绸缎庄……”
傅加斯习惯地拱手还礼:“哦……”他本来还要顺嘴说上几句客套话,可是抬头一看,这副熟悉的面孔顿时令他方寸大乱,嘴讷舌拙,几句说滥了的恭维话也抛到了九天之外。除了剪短的胡须和风吹日晒而变得黝黑、消瘦的面庞,这不就是那个活脱脱的鸿胪寺少卿吗?可是他为什么落魄至此?为什么隐瞒身份?
就在傅加斯左思右想,不知其所以然的当口,李加适时地打破了这尴尬的局面:“傅加斯先生,久仰大名!敝人初来高昌,还望多加照应啊!”
“好说!好说!”傅加斯顺口答应。他从李加滚动的眼波中,领悟出“慎勿多言”的暗示,而“多加照应”的言外之意,自是不可揭开谜底。他不知个中奥妙,只有谨遵照办。
他们的“眉来眼去”,使诃黎布石如堕五里雾中。他不便冒昧地插话,只有和傅加斯开着玩笑:“您天天在我面前吹牛,自称‘长安通’,什么从达官贵人到老板、帐房,一提起您的名号无人不晓,怎么反倒不认得这位李客官?”
傅加斯打着哈哈说:“将军没听李客官刚才说‘久仰大名’吗?”傅加斯机巧地辞令使李加赞佩得连连点头,也把诃黎布石噎得说不出话来。他责怪自己的失误。在巧言善辩上,自己真不是商人的对手。
傅加斯见布石脸红得像猪肝,就转移了话锋,接着说道:“可是我和上一品确实交往不多,和这位也是初交。如果您说我爱‘吹牛’,或者温雅一点,‘言过其实’,我是不会争辩的。您先别开口,我知道您要问什么。我为什么和这样一个名噪遐迩的商号交往不多呢?这得要由他自己来说了!”
说什么呢?李加不知如何把话茬接下去。但他毕竟经商多年,又有仕途生涯,对付这种场面还游刃有余:“是呀,我们商行和傅加斯商队有过不愉快的往事,虽非我亲身经历,却是常听人说起的。我们老板姓康,康居国人士……”
“有名的‘铁公鸡’,一毛不拔!商人都贪财,爱钱,可从没像他那样不讲交情、不讲信誉的。”傅加斯接下去慷慨激昂地挥着双手,吐沫乱飞,真像吃过“铁公鸡”天大的亏。
他们俩不期而遇,竟然一唱一和,天衣无缝,让诃黎布石没看出一丝破绽。
诃黎布石听着,不得要领。如要傅加斯讲述经商的种种遭遇,那就等于讲说几十年的历史,只怕几天几夜也难以讲完。何况他有那样一张商人的嘴巴。而诃黎布石哪想知道这些呢?幸亏两名侍从走了进来,在客厅中央的圆桌上摆好了雕花绿漆盘。布石趁此打断了他眉飞色舞的讲说,把客人请到桌边坐下。
桌上,三只玲珑剔透的瓷碗里斟满了茶,几只赭底银边的瓷碟里盛着各式各色的点心:有油炸的也有烘烤的,有甜的也有咸的。依照高昌的习惯,客人面前是不能“白桌”的,总要摆上茶点或者酒肴。否则,会被视为礼貌不周或者下“逐客令”。
他们三人各怀心事,身在咫尺而话不投机。诃黎布石只能不停地劝客人吃呀,喝呀。傅加斯和李加也只有相视作笑,客客气气地劝吃劝喝。如此这般地吃了一顿,天南海北地聊了一阵,都觉得有堵冰墙隔在中间,看得见,摸不着。
正当大家都不知如何了结的时候,白斥候进来通报说:“大王派人传送敕令来了,请将军接旨。”
诃黎布石未敢怠慢,请客人稍候。
傅加斯也趁便告辞。临别时,告诉诃黎布石,说他还住在“天西”,有什么事情就去找他。
这个未了的会面就此了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