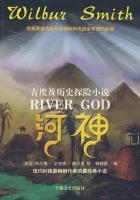沙飞在戈壁滩疯跑了一阵,直到听不见追蹑的蹄声,这才蹿离软绵绵、虚塌塌的荒漠,拐向大路直奔高昌。没跑一个时辰,刮起了东南风,虽说爆沙扬灰,迷津障目,倒也马添双翅,人驾轻云。沙飞还让戴上了黑纱眼罩,即使和客商对面寒暄,也难认他们的真面目。
第三天寅时,高昌城还在酣睡,他们就到了东门,脱掉了伪装,塞到屁股下面,神不知鬼不觉地钻回了老窝。饱吃足喝了一顿,就各自回房歇息了。要知道,他们在蛮荒野地里颠簸了几天,还没踏踏实实睡过一个囫囵觉呢!
沙飞虽也困顿难熬,上床之前,还是忍不住打开了抢来的漆盒,看看里面究竟是什么宝贝,值不值得献给吐屯大人。当他揭开盒盖,只见绛红的缎带十字捆着一个黄绸包裹。他小心翼翼地解开缎带,摊开两层****,才见里面一尺见方、端端正正地叠放着一块联珠宝相花锦。色彩斑斓,工艺精细,间有金丝经纬。沙飞从未见过这么美丽的织品,禁不住惊讶地叫出声来。待他抖展一看,更是目痴神呆,睡意顿消了。原来花锦中间对称地织着两条盘尾金龙,形质逼真,腾挪欲飞,有吞吐云水之势,俯仰六合之态,富丽辉煌,气概非凡。沙飞知道这叫“双龙锦”,是御记织坊专为圣上精绣的,西域各国都视为国宝。倘使吐屯大人能把这块双龙锦献给麹文泰,大王定然高兴得手舞足蹈,也会对自己格外器重了。
他对着天花板没边没沿地胡想着,兴奋得难以入眠。迷迷糊糊地睡去了,又接连不断地做着香甜的梦……
李加自从进了高昌城,就穿上了灰色的道袍,戴上了软顶高帽,把自己装扮成“术士”。为什么要乔装打扮呢?以防万一。万一旌节被人发现,必定严加追查。他不能甘冒这样的风险。可是,又不能身在将军府里享清福。他要从市井百姓、从摊摊贩贩发现旌节的蛛丝马迹。
他早出晚归,左手擎起风云八卦图,右手摇着铃鼓,出没在王城的大街小巷、闹市僻里。他自称云游中原,与圣上——当今的天可汗交深谊厚。在圣上世封秦王的时候,曾为之占卜善相,预期秦王“明星照临,必为人主”,遂使秦王翦武周、殄世充,发动“玄武门宫变”。他自称足遍西域,曾在波斯宫廷供职,是俾洛斯亲王的谋士,预言了亲王不幸的未来……他口若悬河,天花乱坠,细作以为不过是瞒天过海,骗人钱财。市井商贩却深信其真,相随左右,竟成了方圆十里的王城的新闻人物。
诃黎布石对他的行动也不加干涉。他是受害者,土匪们洗劫了他的财货,他能以占卜糊口敛财,略补穷蹙,不也很正常吗?何况,布石还有更令他操劳的公事。
麹智盛派人送来一封信嘱他“速找贝罗奇运回兵器”。还有张卷成卷的黄纸条,歪歪扭扭地写着“我困龙沙,贝”。
诃黎布石看罢,立即叫上精壮兵勇,套上两挂马车,来到龙沙驿馆。
龙沙驿馆是个小客店,不太显眼,座落在民部旁边的小巷中。布石见几名持刀小吏威严地站在驿馆门前,好生诧异,上前问道:“你们站在这儿有何公干?”
“还不是这些猾头,不肯交税,害得我们从早陪到晚!”小吏认识布石将军,吐掉瓜子皮,没好气地说。
“贝罗奇也没交?他住这儿吧?”布石试探地问。
小吏的目光在布石脸上扫了两圈,诡谲地嘬了嘬牙花子,反问道:“将军跟他很熟?”
“不熟。”布石照实说道:“‘交河公’认识他。托他从突厥买来一批货,派我来取。”
“噢。”小吏没再问下去。只是高深莫测地笑着,带他走进院里。
布石闷头跟在后面,眼光从院子的这头睃巡到院子的那头,兜了个来回。他希望看见几辆绑裹得严密的满载的车辆,或者从门缝看见堆放在屋里的兵器……可是他失望了。
小吏把他带到一间平房门口,推开屋门,就让他走了进去。
布石踏进门槛,就见土炕的光凉席上,头朝里躺着一个人,身上横搭着一件白长袍,听到动静,那人睁开眼,可是因为布石挡住了光线,没认出来者是谁,依旧一动不动。
“还躺着装死?折冲将军来了!”
小吏说话的口吻使布石有些吃惊:贝罗奇也是个有身份的商人,怎能如此出言不逊?不过,他心里这么想,嘴上没说,就不动声色地径直走到炕边。贝罗奇用肘撑着炕席吃力地坐起来,额头沁出黄豆大的汗珠。当他认出布石,就急忙伸出微颤的左手,语调悲凉地说:“布石将军,是你。”
他和布石认识,不太熟,更不知布石已谪戍交河郡。
布石也认出了贝罗奇,急忙上前挽住他的臂膀,问道:“你病了?怎不通告一声?”
贝罗奇坐起来——弯着腰坐在炕沿上,活像一把拉满的弓。
淡黄的眉毛不时抽搐一下,牙齿紧咬着腮帮子,倒吸着凉气,轻握的十指无节奏、无目的地抖动着。
“将军,告退了。有事就喊我,别客气!“小吏恭顺地婉言,识趣地退出了屋外。
布石出示了交河公的手令,问贝罗奇:“兵器呢?没买来?”
“买了。”贝罗奇无精打采地回答。
“在哪儿,交河公让立刻运走!”
“运?我在焉耆城都卖光了。”贝罗奇声音不大,语调可是恶狠狠的。
“卖给了焉耆?你……你混蛋!”布石怒火难耐,出口大骂。因为交河郡所要防备的首先就是焉耆国。可贝罗奇竟然把武器资助了敌国。
“怨谁?我是商人,不是傻子!我不能眼看着肥肉不吃啃骨头!”贝罗奇也来劲了,抬起佝偻的上身,梗着长脖子,瞪着红眼珠子,可他的目光没敢正视布石,只盯着墙根的木水桶,像是跟它吵架。
诃黎布石被噎得无话,钉钉地傻愣了一会,扭头就走:“好!咱们绝交!以后,你就别做交河的生意!”说罢,就脚步咚咚地向门口走去。
贝罗奇一按炕沿立了起来:“将军请留步,我有话说!”
诃黎布石停住了脚步。
贝罗奇一步一步移过来,拉住布石的右手,把个硬硬的东西放在他的手心,含着泪,哀求着:“求您照应啦!把我放了!真的再没珍珠啦,你给他们说说!”
诃黎布石低头看了看手心,是一对光彩夺目的红宝石。他五指收拢,攥住,静静听完贝罗奇的话,然后说:“你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贝罗奇喘着粗气,用手背抹着渗出的冷汗,吃力地坐回炕沿。
布石看他可怜兮兮的样子,猜他或有难言之隐,态度和缓了些,伸手去摸他的前额,热得烫手:“你在发烧,没去诊治?”
贝罗奇没理会他的话,只管滞滞哀哀地说:“我来高昌,是为取珠子——一个老板早替我买好了——我寻思这玩意小,不扎眼。没成想,还是让他们查出来了!交就交吧,赶上了,只有认晦气、认倒霉!可他们硬说我还有珠子,藏起来了!不让我走!菩萨有眼,我真冤枉哪!”
诃黎布石看这个壮年汉子哭得那么伤心,又信誓旦旦的,真动了怜悯之心。可是想起兵器的事,顿又七窍生烟。
贝罗奇也知道自己有亏于交河公,痛心疾首地唠叨着:“我回去,一定给你们重新置办!这次怪我,恳求将军和交河公海涵,饶了我这一遭。”
平心而论,自己不该怪罪贝罗奇。布石这么想。关山万里,暑蒸风割,不就为挣几个钱吗?应当责怪的倒是高昌。他转向贝罗奇,说:“如果真是这样……”
话没说完,四五个人呼呼啦啦就闯了进来。为首的向布石拱了拱手,大大咧咧地说:“布石将军,对不住了。这位老板生了重病,我们请来位医生,给他看一看。”他用大拇指冲身后的人指了指。
“不!我不看!我会好的!”贝罗奇像撞见鬼一样恐惧地摇着双手,屁股噌噌两下早就挪进了炕里,缩成一团。
布石伸手拽他:“有病还要治。出门在外,自己要爱惜自己。”
贝罗奇死乞白赖地缩着手,紧贴窗根躲来躲去,就是不肯过来。两个大汉跳上去,一人拽一只手,死拉活拖地扯到炕沿,抓住他的胳膊。
医生走过来,切着脉搏,沉稳的目光停留在贝罗奇的面部,打量了好一会儿:“先生,你的病再不能耽误了!”
贝罗奇闪着惊恐的目光,木木讷讷地重复着:“我没病……没病……”
布石把医生拉到门外,问道:“他是什么病?”
“嗯,破伤风。”医生忧郁地说。
“破伤风?”布石提心吊胆起来,眼光从医生的脸上移向为首的小头目。“他没伤呵!”
小头目在手心磕着鞭子,幸灾乐祸地“嘿嘿”笑着,像是不幸而言中了什么。
“别愣着了,赶快治吧!”布石知道,破伤风是九死一生的绝症。
“治病要除根,先从伤口治!”小头目说。
“伤在哪儿呀?”
小头目眨了眨眼皮,斜瞅着房梁说:“反正在他身上!”
他们回到屋里,问贝罗奇伤在哪儿,贝罗奇矢口否认。要脱他的上衣,他拳打脚踢地死也不让。
布石气坏了。从没见过这样的病人,死到临头了,居然这样讳疾忌医。他看两人都收拾不住他,就大声嚷道:“你得了破伤风!都快死了!”
这句话真灵。贝罗奇像遭了电击一般叫了一声,瞪大一双死鱼眼,瘫到炕上,任人摆布了。
两个人扒了他的上衣,就见他上身缠着几圈白粗布。解开白粗布,左腋下三寸的地方,竖着有个一寸来长的刀口,已经溃烂、化脓了。
布石不可思议地连声叹息,这是为什么呢?
医生面无表情,用棉花蘸着药水,清洗着伤口的脓血。
小头目显得不耐烦了。他跳上炕去,拨开医生的手,伸出短粗的五指就在伤口四周红肿的创面上细细触摸着。
他摸到了一个硬硬的圆圆的东西,猛一用力,把它赶到刀口处,再一挤,一个血球从伤口滚过肚皮,“啪嗒”一声落在凉席上。
任人摆布、一动不动躺着的贝罗奇像让人深深戳了一刀似地惨叫着,在炕上打起了滚。两个大汉又把他死命地按住,小头目故伎重演,熟练地摸着,赶着……
揪心的惨叫使诃黎布石不忍耳闻。他踱到桌边,等待着这一切的结束。时候不长,小头目满手脓血地捧着两个东西来到布石身边,开心地笑着:“谁也逃不过我的眼睛!我的眼,哼,火眼金睛!”
那是两个圆溜溜的东西,糊着血,布石左看右看也没认出是什么东西。当小头目在水桶里涮了两涮,把战利品再次捧到他面前的时候,尽管他难以置信,但也无法否认,那的的确确是两颗其大无比的稀世珍宝——祖母绿珍珠!
“这么好的一对珠子,为什么要藏在肉里?”布石百思不得其解。
“怕上税嘛!这些人要钱不要命!”小头目揶揄地回答布石的疑问,冷眼鄙视着死猪一样躺在凉席上的贝罗奇。
“这要上好多税?”
“是要很多呀!这些阔佬,有钱!放点血没事!”小头目无所谓地说。
“你真是火眼金睛,隔着肉皮就能看进肉里!”
布石貌似恭维,却投去轻蔑的目光。
小头目理了理密密的两绺红胡子,狡黠地咧了咧嘴,自我吹嘘地说:“他卖给了焉耆国一批兵器,我们马上就得信了。他还敢来高昌取珠子,狗胆包天,我们岂能放过他。多少,什么样的,全都清清楚楚!他还装胡涂,想蒙混过关。小老儿是干什么的?专吃这碗饭的!剖身藏珠的,他也不是头一个!”
“噢……”布石全明白了,话没说完,他就伸手抓住小头目的手腕,因为小头目正要把珠子掖进他的内衣。布石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你看交河公的手令,让我找他运武器!现在兵器没了,我要把祖母绿交给交河公,用它顶账!”
“那不行!这珠子要上不少税呢!”小头目紧捏住不放,虽然他看了交河公的手令。
布石稍一用劲,掰开他的手指。小头目疼得直叫娘,不敢强辩。布石说:“税虽高,总不值一颗宝珠吧?总买不来那些兵器吧?”
小头目揉搓着手指头,哭丧着脸:“郎中大人要怪罪的,将军爷!”
布石没搭理他,来到炕沿:“祖母绿我替你保存了!哼,比放在肉里保险!”
敷好药的贝罗奇,头搁在薄被上,连抬起的劲都没了。只半睁着眼,“哎哎”了两声。他们的话他都听见了,他并不欠交河郡的钱——那批兵器没有付款。但是,他没做多余的澄清。
布石把那对红宝石掏出来,掂了掂,放在小头目手里,要他“好好照看贝罗奇,不许怠慢。”小头目连连点头哈腰。
离开“龙沙”,布石在门口踌躇了一会,他决定先去找张雄大将军。
自从发生了龃龉,他曾暗下决心不再踏进淳风里一步。现在他改变了主意。人哪,是不能把气头上的话都当成信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