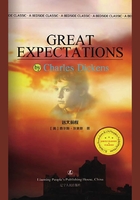坐在落地窗前,俯视华灯初上的北京夜景。舒适的意大利躺椅,穿睡衣半卧着。躺椅微微摇动。
要是他那天冻死了呢……
小张软坡跟绣花拖鞋走过来像猫悄无声息,揉着他的肩膀问:“老公,见了吗?怎么样?”
“这是一个美丽的故事……”他突然发觉自己在模仿他讨厌的陈明新的装腔作势。
法国香奈尔五号香水的气味让他愉悦。
眼前不是当年他离开杨莲英家,徒步沿着铁路所梦想的一切吗?怀着这个梦想,他才能忍饥挨饿,才能走走唱唱。他在那个小站,在裤腿上缝绣了一个奔驰车徽。车徽如同烙印,烙在他心里。“十年我要坐上奔驰!”(他那时只是见过奔驰的照片。)原来买奔驰不难,他八年就开上了。这当真是一个美丽的故事。
近年,他越来越喜欢坐在落地窗前,等着天黑或者等着天亮。
意大利躺椅很贵,他也觉得太贵。坐着舒适。舒适值多少钱?能说出数,用数字表达吗?比它便宜一百倍的塑料躺椅,游泳池边的白躺椅,坐着其实也很舒服。
小张又过来了,端过三脚画凳坐在他身旁。他这时怕人打扰。回忆是一种享受,尤其是对苦难的回忆。难怪他公司的总工,文革中斗得死去活来、家破人亡的他竟然爱听革命样板戏,时不时哼一句“临行喝妈一碗酒”。他问,当年把他倒吊起来,抽皮带,不是天天在听样板戏?他叹口气:“是的。”但对他,样板戏同时意味着青春岁月,意味着一去不复返的时光。尤华生也怀念当年创业的日子,每天晚上两口子在灯下数钱,安排第二天,进什么货,出什么货,吃什么,用什么,有滋有味,充满踏实的喜悦和憧憬。人生这种滋味难再。
小张小鸟依人,善解人意。脱下他的摩洛哥拖鞋,为他揉脚。
她是“三频道”。
“一频道”是家乡人,叫小五。他们是北京“浙江村”的邻居。他做衣服,她卖衣服。婚床是裁衣板,不是买不起席梦思,是无处放。不久,雇了一男一女小工,男的睡在门口,女的睡在裁衣板下。北京最大的方便是房间里不放马桶,出门有公厕。他和小五最大的愿望是做爱时床不摇出声,可以痛痛快快喊出声。几年后,在西单商场租了柜台,在灵境胡同租了房。有了钱,出入时装发布会,他的批发客户悄悄问他:“模特儿怎么样?两千元一夜能搞定。”他说:“我要和小五说说。”小五说:“去啊,省得你看女人眼睛发直。要挑就挑最佳,差的我不答应。花两千元你就知道女的全一样。不就是一个女的吗?”还真让他太太说中了!
十年后,他已经什么宾馆都敢住,什么饭店都敢吃。有一天,他突然发现小五好不容易学会的穿裙子坐着并拢腿的姿态复原了。有一天,他跟在她身后又突然发现小五的腿变短了。从俄罗斯回来,他对她说:“我们离了吧,一辈子你看我我看你,烦不烦?我给你二百万,你也是强人,到乌鲁木齐发展去。”小五不假思索:“行啊。跟你没亏,我十年还真赚不下二百万!”这是硬话,小五爱说硬话。真正的原因是她没有生育(她说是裁衣板上做爱憋出囊肿)。分手时,他俩都哭了。他说再加五十万吧,她说不稀罕。
“二频道”才维持三年,三年生了一女一男。“二频道”人高马大,腿长胸高。“二频道”走时也带走二百万,一儿一女留给他,现在儿子在澳大利亚上学,女儿在英国上学。他们母亲一时去悉尼,一时去伦敦,他不干涉,不时还周济路费。她是好人,就是爱热闹,图新鲜,花钱大手大脚,她的一群朋友吃她的(他的),用她的也玩她。她保证儿子是他的种,没有保证女儿,可是女儿像他,儿子不像他。
女人和男人是一样的。一样爱虚荣,一样爱钱,吃一样东西,排泄物一样脏秽。明白了这一点,人生就缺失了一半的乐趣,不过这就叫成熟吧?他再换频道,就挑小张。小他十五岁,恋家,贪睡。睡够了上健身房,上阳台游泳;爱吃零食,吃够了吃减肥药,打电话招美体按摩师。每次回家她都独自在家。他很满意,这样的太太称职。
小张问:“不是请她来家吗?”
他没有邀请杨莲英。这个项目取消了。
不知道为什么,他感到有点失落。
两年前,他是“开出朵花”了,接父母来北京,他也是这样说的:“住多久都行,去哪里玩都行。”他还说,或者住家里,或者住饭店,随他们意,也是安排一辆车,父母不会讲普通话,特地从宁波分公司调来一位温州人。小张得体,时不时去看望他们,送点小吃,小礼品,父母带来的黑疙瘩“死不了”,她也装出很喜欢的表情,爱不释手的样子,在客厅水晶杯里养了几天。父母在家住十天,搬到王府饭店住一个月。最后几天,是勉勉强强住下去的,他们知道要走是要伤儿子的心,尤华生也明白他们想走只是说不出口。欲言犹止,别别扭扭。最后,谎言解决,父母说家里母猪要下崽,尤华生知道家里没有养猪,也就说既然母猪下崽,先回去也好,什么时候想来京再来。他感到无奈。
夜色中的北京街道,白灯的车流向他驶来,红灯的车流离他驶去。每一盏白灯和每一盏红灯的车里,都有人,都有他们各自的生活,各自的喜怒哀乐,生老病死。无论是驶去的或驶来的,最后的终点都是坟墓。小张娇嫩,小张也是。
看得出来,杨莲英对他俩的重逢并不兴奋。她根本没有认出他,对那件事根本没有情感记忆。对他的兴奋不如对饭菜,不如对北京饭店的富丽堂皇,甚至不如对刚刚见面的小叶。
寻找她,找到她,再见她,真的那么重要吗?
看得出来,是他扰乱了她习惯了的平静的生活。本来,让杨秘书送去钱,他去宁波时顺便看望她,这要简单得多。他财大气粗,他颐指气使,他是强迫她来。这感觉很差。
小张:“你心情不好。”
尤华生:“没有。”
小张:“瞒不了我。”
尤华生:“早点睡,我们生个孩子吧!晚上有节目。”
节目是做爱的意思,他俩的词汇。
第二天醒来,尤华生感到精力充沛。人在夜晚显得沉重,天一亮,阳光照进来,便消释,便驱散。他去了一趟海南,回京后又去了成都。忙碌的好处是紧张而不沉重。
小叶来电话,杨莲英要回家了,想小孙子。
“几点的飞机?”
“十一点。”
尤华生到饭店送行。
杨莲英千恩万谢:“人活到这岁数,才算明白天底下有这么多好东西。六十几年都白活了!人跟人没法比,天上地上都活人;我回去,眼睛闭了也是笑。我是遇到贵人!”
尤华生问:“你在石山的儿子,叫许红军是吧?他还好吗?”
“你还记得他!他不挖煤了,在温州人一家公司上班,看仓库,月薪一千元。这个儿子不孝,亲儿子都比不上你尤老板。”
这么说,许红军没有告诉她是他安排的工作。
他把一个黑皮小包交给她,说:“你随身带着,里面是二十万元现金。你在镇里买套房子。”
杨莲英意外。她望着小包愣住了,二十万对她是难以想象的天文数字,一辈子赚的钱相加也没有这么多。她已经在北京买了好多好东西,都是小叶付的钱。来时一个扁扁的旅行袋,回去已装满一只大皮箱。他给的1万元零花钱,只用了二十八元,是在东华门小吃街吃夜宵花的。对意外的惊喜是需要慢慢体味的,眼泪流出来了,她说话了:“不用,不用,我消受不起。……我留下两万元,两万元足够修整房子,跟新的一样。老房子住惯了,我只要两万,真的,真的。”
他这十几年,给了多少人好处和照拂。他早就明白,给予比索取要愉快,要高尚,但从来没有这次感到付出的值得。原本的感觉,炫耀,报恩,慷慨,施予,和这些感觉带来的愉悦,在这时都显得很轻很轻。
“你留着,给小儿子娶媳妇用。”他竟然只会找到这样一个理由说服。
他临时决定,送她去飞机场。小叶奇怪,只有订单超过三千万的大客户和不明底细的外商,他才亲自送到机场。
飞机上天。飞机上的人看不见他了。他看不见飞机了。
一个寻找的故事,消失在蓝天里。白云朵朵。然而,寻找的意义,又出现心里。
“你在车里等我。”
“好的。董事长再见。”小叶身材高挑,步态轻盈。望着她的身影,美丽撩人。他对公司女职员从来没有非分的念头。这种撩人是享受,感官的享受。他觉得自己老了,或者在老与不老的临界线上。
机场贵宾室十分雅致。服务员送来一碟水果。
尽到心意了。从一开始,他就不是为了别人说什么,甚至不是为了杨莲英认他是知恩知义的人,贵人。一切都是意外,蹊跷,偶然。这个问题又浮现了:他要是二十三年前冻死了呢?即便是早半个小时回到店铺,抓进笼子,他的人生轨迹也得是另外一幅图景。既然是意外,蹊跷,偶然,为什么要寻找?寻找什么?活着又是什么?
他可以在这里坐上一小时,两小时。很安静,没有小张的关切的烦扰。目视一架又一架飞机向上滑,滑上蓝天。飞机其实没有飞的感觉。在飞机里的人都是匆匆忙忙的人,不像现在的他。他有点遗憾这件事就这么结束了。以后不会再见面的,再见面也是情景别样;感情不会重复,也许那时会感到累赘,无聊。这样的事人生只能一次。
他舒舒服服坐着,一小口一小口啜咖啡。品味充实,孤独,怡和,无助。我有朋友吗?我有很多朋友。我没有朋友。我感情丰富吗?有时觉得是,有时又不是。剩下只有一点确定了:我有钱。
当你什么宾馆都可以住,什么饭菜都可以点,全世界什么地方都可以去的时候,那么,我还要什么?还要做什么?
他知道,这是他的问题。
下星期去石山市。温州商业步行街是笔大投入。不会对市长、陶会长讲这个故事。这种事如同口水,含在嘴里滋养,吐出来恶心;也不会对许红军讲,他听不懂,不关他的事。
会再有个杨莲英吗?
(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