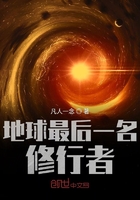林辉顿悟。一是明白自己的确没有写大字的功力,二是写小字是个办法。
“我说嘛,我们党为什么这么重视和尊重专家。对,很好。写六寸大,就不用站着写,也不用悬肘。写一下午,腿也麻手也酸。我马上写,你给我改一改。”
杨兵裁纸,折出方块,说:“这怎么行.我哪有这个水平!”心里在琢磨:到底改一改林书记喜欢还是不改喜欢。
林辉勤奋,提笔蘸墨就写。一口气写几张,紧张得手发抖。他在开会讲话时谈笑风生,挥洒自如,人一到弱项就不一样了,不像同一个人了。杨兵决定动笔改。改好了是林书记的体面,只会感激他。林书记能辨别好坏的。
“这几个字不错;招牌字不同于题字,笔画要粗一些,粗一些站得起来。我来描描粗,行吗?”
“行,行。重新写都行。”林辉激动地说。
杨兵在他的字上,描直描横描撇描捺,一笔一笔描。林辉站在边上不停地说:“好,好。”连他的签名,也稍许加了加工。
林辉十分满意。
“你这一改,连我自己都认不出了。这是我今后努力方向。书法艺术博大精深,中华文化之瑰宝。你们元旦书画展准备得怎么样了?”
“征集到三百多幅作品,是我县历年来最高水平。只是经费上还有缺口。林书记也写一幅,正想约请你,以壮声色。”杨兵顺口说。
“写字免了,经费可再拨一点——六万够不够?”
“够,够。余下我们自己可想办法。感谢县委支持。”
元旦书画展企业赞助踊跃,图个开年吉利。本来不缺经费,一句话就来了六万。意外收获,文化馆干部年终就可多分点钱。
“仙客来大酒店”这六个字,陈碎儿也是给林辉六万元的润笔费。一字一万元。
他照惯例上他家。他已是林辉家的常客,每次来,提两瓶洋酒,人头马、蒙特伯爵什么的,提一兜洋水果,贴着外文标签。林太太有了吃洋水果的爱好。一开门她有个笑脸,进门就不拘束了。
“我这几个臭字,哪值这么多钱!”林辉一副好心情,望一眼放在茶几上的信封,上面是:“润笔费六万元整”。
李爱香也过来看一眼,进去沏茶了。
“这可是墨宝啊!书记亲自为我们题字,我们酒店身价就高了。再说,我们这些人也就是有几个钱,其实我最羡慕还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字写得好!这几笔,没几年几十年的工夫写得出来?拿秤称拿尺量行吗?”
林辉笑笑,不再说什么了。当了几年县级干部,这是他家最大的一次性收入,最重的一个信封。既然艺术无价,他心安理得,乐得接受陈老板的遁词。反正是一个人,真有什么事,他一个人的口供也不足为凭。可见陈老板是有心人,让你后顾无忧。
“坐,坐下谈谈。”
陈碎儿不大放心地坐下。是好事还是坏事?还会有什么事?
“黄书记和阿琴,到底有没有违规的事?”林辉开门见山,推心置腹又不失领导身份地问。
陈碎儿一怔,略略踌躇。说有,在林书记眼中他便不可靠,出卖朋友,而且也失去这位朋友;说无,林书记是不是会觉得把他当外人了,不实在,不堪信任?
“大概不会吧?我怎么没听人说过?”陈碎儿显得天真,张着嘴巴。
林辉心里有数,笑笑,欣赏陈老板的机灵。
“你们舍得让黄书记走?”
“舍不得有什么办法?好鸟就得栖高枝。我不是卖花嘴,我是说实话。对啦,不吹螺,谁晓你卖肉——要不要给县委写几封表扬信,多找几个人签上名?”
“这倒不用。用不着,也没用。关键在上面有人。黄书记太本分,县上没枝,市里没根。在下面呆着,十年也没人想到他。中国那么多人才,也不是一定要谁谁谁。不过你让黄书记放心,我会尽全力的。”
不久,县委常委会上林辉建议黄士宝调任组织部长。时节也顺,正强调重视理论学习。
林辉说:“我们就是要提拔重用理论水平高的干部。美国国防部长要文官当,我们的组织部长要理论家当。副教授当县组织部长,全国全省也不多见。好不好?我看好,很好。黄士宝同志不仅理论水平高,还有基层工作经验。是金子在哪里都发光,在双溪镇当书记,群众说:‘我们算是看到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干部了。’”
全体通过。
不久,市委发文:黄士宝同志担任县委常委,组织部长。
11
黄士宝在部长办公室接到石海琴的电话。
“晚上六点,下了班到我这里来吃饭。我等你。”
他感到蹊跷。从来都是他去,他打电话。他不知道她有自己的电话号码。他也从来不去她那里吃饭。陈碎儿给她买了一套一室一厅一卫一厨的公寓房。
“有事吗?”下班时间楼梯上人多,他不方便。
“来了再说,好吗?”
那么一定有事,不是小事,不是好办的事。
黄士宝走上新岗位,总想一切从头开始。他对自己约法三章:不吃请,不受礼,不公车私用。
不吃请不难,本来就厌恶场面上的吃吃喝喝。当干部也是三陪:陪吃,陪坐,陪玩。名声传出去了,黄部长不参加宴会,做官就省事多了,简化多了。
不受礼他也有招数。在家门口贴张告示:“私宅不谈公事,谢绝接待望谅。办公室电话:921581。”他的办公室取下撞锁,门上是挂锁,一上班就半开着门,明来明往。墙上贴告示:“君子自重,不开后门。”
公车不私用更是有目共睹。组织部有两部小车,普通桑塔纳是工作用车,富康是前任部长的专车。他上下班坚持骑“飞鸽”。“飞鸽”相当于他的工龄,一次被盗,小偷嫌太破旧又撂在街角几天没人捡。他小心翼翼地维护自己公私分明的形象,连办完公事已到下班时间,顺路过家门也怕引起误会,总要坐车到县委再骑车回家。
只是陈碎儿陈老板怎么办?
今天是陈老板的事还是阿琴的事?
他欠陈老板的情。不说阿琴是陈老板送的,阿琴使他一生充实和懂得什么是女人什么是男人,他能出任组织部长,陈老板也出了大力,也许是决定性的——林辉凭什么提掖他?知恩不报非君子,不能忘恩负义,这是他为人的原则。不过,这张陈老板说的你有来我有去的人情锯,却折磨人,痛苦不堪。情和恩如何度量?怎么报答才光明正大和怎样才算报答完?他不做过河拆桥的小人,但他早晚要掉到河里的。他感到,他已不由自主,一种默契,存在在他、陈老板和林书记之间。
然而陈碎儿很少找他。
这一回,是陈碎儿有事让他帮忙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他让石海琴约黄士宝。
县土地局局长受贿,撤职查办移交司法部门。这是个肥缺,不少人看着流口水。路桥镇镇长季兴科太想这个位置了。镇长批土地都有大油水,何况土地局长!路桥离双溪不远,早知道陈碎儿神通广大,白道黑道都有人。陈碎儿来县城不久,一些干部已有共识:听他的话,没有不准的;托他办的事,没有不灵的。季兴科提上烟酒在县城游转了些日子,大家都建议他找陈碎儿。
他空着手到陈碎儿办公室。空手是空手道,学问更多,天地更大。
“季镇长今天怎么有空?有什么事我陈碎儿可以效劳的,尽管开口。”
他那做派,说话架势和腔调,把这位镇长镇住了。果然名不虚传!当年蹲猪圈趴厕所的地痞,现在跷着腿人模人样。他就照直说,儿子在县城中学读书,老母亲在县城住,多病生活不能自理,自己在一个地方窝久了也想换个环境,钱不是问题,花多少通关都行……说着,掏出章永清的引荐信。
陈碎儿摆摆手:“你我谁跟谁呀,还要章镇长介绍。”
季兴科连忙说:“对,对,对。”
“不过话得说回来,土地局可是金库银窟啊。那个局长让人套住了,谁让他在市里买下三套大房子!有钱也不能这么显豁!这个位置是头彩,央求我的就有三个人。”
他这一摆,季兴科更诚惶诚恐。陈碎儿脸上的锦旗——刀疤闪闪发亮。人一胖,光荣的刀疤比先前更亮了。
“我们是老朋友,你得看在老朋友面上……”
“我心里有数。你看,我是生意人,什么都用钱说话。我先出个价,你不一定懂县里的行情。合算,我来操办,不合算,买卖不成仁义在,你当你的镇长也不缺什么。怎么样?”
“你说,你说。”
“二十万。你先拿过来十万。办成,那张印红字的纸到手,再付十万;办不成,我还你五万,那五万就算手续费,操心费,跑腿费,面子费。口说无凭立个字据,成不成字据日后当着你我的面烧了。明晚上就在我这里摆两桌酒席,我做东,算是送给你的。到时候你见见场面,认认人。”
一席话,说得季兴科不敢吸气只有嘘气的份。他这个镇长太不是一回事。
“二十万,是不是……”
“那就免谈。换了别人,这两桌酒我还不给面子。凭什么呀!”陈碎儿说罢,站起来送客。
“可商量,可商量……好吧,一言为定。凭你和我的为人,字据不必写了吧?”
“先小人后君子。”这句话陈碎儿学会不久,经常用,挺有味道。他笑着拍拍季兴科的肩膀,“不是怕你赖,是怕我赖。十万元放下,我不认账,到法院我说你凭什么给我十万,你还得说是买官的。这不,丝瓜打鼓,折了还不响!”
“好,好,明天我带钱来再立字据。”
季兴科千恩万谢走了,他才拆开章永清的信。信里他建议十万。艺术无价,官也无价。他笑笑,这封信也得留着,日后也会有用。
不过刚才一时痛快说了个“明天”。明天这两桌酒请不来几尊神,就塌台了。时下是酒好摆客难请。这在大酒店见多了,天天都有这种事:开宴了,几位头头脑脑还不来,急得主人一个劲的打手机央求人,有时还少不了请陈老板出面说几句话。他就打趣说:“我管鸡鸭王八,还要管局长太太?”说是说,感觉十分风光。现在是自己的事了,二十万元说多不多,说少不少。
想到的第一人是黄士宝。
黄士宝没有骑他的“飞鸽”,怕放在楼下让人认出。一路慢慢走来。
从党校门口走过。他回县上后来党校讲过课。这次他是应石海琴之约路过的,感觉不一样。他突然很怀念那时的他的清白。生活单调,心境单纯。
那时他不可能不发觉,课堂上女学员的火热的眼光。她们不听课,只是注视他,专注,赞赏,随时迎着他的目光绽开微笑。一到课间休息她们就挤过来问长问短,不带耳朵只带眼睛。幸好,党校多的是短训班,三个月半年,感情未到火候就走人。一次,一位乡镇企管所副所长,他始终不明白这位染黄头发、抹紫唇膏、穿露脐短衫的女同志怎么会来党校学习。那天是星期日下午,党校院子如同一个空脸盆。她来了,反锁上门,说,政治上她拥护改革,性生活她拥护开放,她的身体只属于自己,他对她不必负任何责任,只一次也可以。他是个有魅力的男人,女学员在被窝里、浴室里常常议论他。她没有带胸罩,也没穿内裤。大嘴大眼睛,细脖子,乳头在T恤衫下顶起,一条短牛仔裙。她说:“为什么不?你放松一点。”他现在明白,这是外国影片里女人做爱前常说的话。她说:“你会很舒服的。……我们就在沙发上吧?”他一定给她一个不正常、生理有缺陷的印象。他浑身不自在,声音发颤:“我不行。”
男人对性生活主动大胆的女人会有一种畏惧、抗拒的本能反应。如果她那天不那么一副进攻姿态,渐入佳境,也许那个下午他就多了一次温柔热烈的人生经历。
他后悔吗?过去不。现在怎么又想起来了?他是堕落了。他在女人的怀抱里不能自拔。县城有家,他俩同床异趣。他没有告诉叶芬,邢洁非来电话和想约她见面。他当年是胜利者,如今是失败者。有一天想起他,他才和叶芬“充分”了一下。叶芬怪怪地看着他,一动不动。
如果他只是离不开石海琴呢,那是什么?美丽的堕落,快活而丑陋。尽情又不安。他每星期去一次。给她打手机。她每次都说:“好的,我等你。”他是看过中央台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之后去的。总是在八点。她洗澡。她洗澡的时候,他喜欢半开着门倚在门框上注视她。她不时转过脸娇嗔地瞥他一眼。她就穿上浴衣,敞开浴衣做爱。他和她都越来越享受到性生活的兴奋和愉悦。她左右摇晃着脑袋低声呻吟:“阿黄,阿黄。”阿黄是她在床上叫的名字。他放肆地呻吟。然后她进卫生间。他看电视或VCD,她从卫生间出来依偎着他,把下巴支在他的肩头,安安静静,如同一对睡着的鸽子。十点他离开,绝不超过十点半。她从来不提要求,从来不暗示什么。陈碎儿交托她的事,她也用不着躲躲闪闪,比如:“陈老板说,×××找他了,想谋个×××的位置,你能不能帮忙?”通常他会派人去考察,不出大问题他能拍板。这种事也不常有。组织部能考察出大问题的人几乎没有过。
他有门钥匙。不想惊动邻居,用钥匙开门进去。今天,开门见陈碎儿,坐在沙发上,面对着他。他一怔,有作弊被当场发现的感觉。他第一个反应是要退回去,关上门。
石海琴从厨房出来,说:“你来了。”
“陈老板!”黄士宝硬着头皮招呼。
陈碎儿等黄士宝换上拖鞋走到跟前,才慢慢抬了抬屁股。
“坐,吃饭。黄部长来县上,你忙我也忙,见面不多。今天喝几杯。”
桌上摆着四个冷盘,一个热菜。一瓶酒,三个杯。陈碎儿倒上酒。
“好,好的。今天尝尝阿琴的手艺,我还是第一次。”黄士宝说的是实话。
“干一杯。阿琴,你也来。”
黄土宝干了。火辣辣的。他忐忑不安。他和阿琴第一次做爱陈老板就知道了。他和阿琴的性生活就像在玻璃瓶里,陈老板看得一清二楚。奈何不得。今天是什么宴?
她端一盆炒粉干出来,站着喝干一杯。她也有点失态。他俩被陈碎儿玩弄在股掌之中。
陈碎儿与当官的交道打多了,得出结论:他们都是极聪明的人。与他们做事直来直去最让人不防备,最让人放心。丑话明说,不跟人玩三眼猫。
“阿琴对你对我都不是外人。我亮亮底:季兴科你认得吧?路桥的镇长。他看上县土地局局长的空位。论年龄、文化、能力都不差,不过有这三样的干部一箩筐,就看谁能爬出来。你和他都是在镇里干过的,想出来也有情有理。局长给别人不也给了,给他也给了。他不敢找你来找我,我有没有面子等你说句话。这里是给你两万元活动费。”
“钱我不能拿。我不缺钱。”
“这看怎么说了,要升官你不花钱?凭你的工资你拿得出?当官不发财,请谁都不来。”陈碎儿说起话不留情面。有石海琴在,他就是她和他的长辈。
“组织部提拔干部有一套程序……”
“什么程序不程序,你是一把手,还不是你说了算。”
陈碎儿的话太生硬,但是实情。新调到组织部,两位副部长都比他资深年长,他总是谦恭有加,弄得这两位很不好意思。他经常征求下面科室的意见,反而使他们不便工作。那位老办公室主任向他进谏:“黄部长,你是继承党的优良传统,可是社会大环境变了。你是民主作风,别人说你当断不断,你不耻下问,别人说你是故作姿态。你的水平、能力和作风,县里干部不适应。一样鸟啄一样虫,在中央、省里行的,这里不行。”黄士宝越想越感到中肯。
“还要通过县常委会……”黄士宝只有招架之功,机械地一筷子一筷子地夹菜往嘴里送。
“常委谁认得季兴科?不就是你,还有林书记。林书记那边我去说,他那边失手是我的事。行不?天下的事就是人抬人,人帮人。”
“好吧!”
季兴科既然是镇长肯定可以通过考察,上面还有林书记把关。想到这里,他轻松了一些。倒了一杯酒和陈碎儿、石海琴碰杯,一口干了。
“明天我替季兴科摆两桌酒亮亮台,请县上几位头头脑脑出席,你来不来?”
黄士宝说:“让徐副部长去。”
陈碎儿不坚持。
“这依你。两万元你得收下,你没这个本事就没有两万元。本事换来的怕什么!”
“陈老板,你得成全我,钱我不能收。”他央求着说。他喝多了。他苦笑着又说:“人死了还图个全尸呢!”
石海琴没有见过他这个样子。他总是很矜持,很有分寸。她站起来去厨房了,眼睛红红的。她为他心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