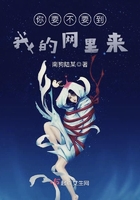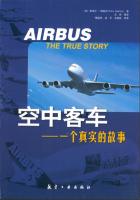巫隐为人清淡,一次性说那么多的话倒把其他几人吓到了。
那个鸟不拉屎,寸草不生的地方如今已经是颐国的附属国了,名为颐栏国。一般由王爷掌管,现在的掌管者是闻风吟的弟弟三王爷闻风凉。
三王爷生性豪放,为人处世不拘小事,是最为像先皇失忆前性子的皇子。
而且有一点也比较像,先皇二十五岁时才有了长子闻风吟,是属于晚子的一类的,闻风凉而今二十四也不见他有婚配。为此太后也催过,可他就是口头上敷衍,实地不见他做样子。
他常年在颐栏国,偶尔过年时才会回来,过完年就匆匆而走。
雨笛的三皇叔不风流,却爱流连于风花雪月之地。
有一次还被雨笛和巫隐碰见,闻风凉看清来人之后手无足措。
这里面还有点故事,巫隐若不是早早地为祭司,太后是有意将他指婚给闻风凉做皇子妃的。
乃至于后来雨笛不止一次地猜测是不是这个原因,但闻风凉对巫隐有没有意雨笛就不知了。
雨笛想来也是,怪不得以前有几次闻风凉爱找巫隐,只怕不是其他原因,而是知道巫隐手中有天机扇的缘故吧。
“你怎么没告诉过我这些?”雨笛不期然道出,把自己也惊到了。
巫隐一直淡漠着,此刻是粲然一笑,“不过是小事,没必要跟你说,再说当时你人可是在风于山。况且,那时我和你的关系还没达到那样吧!”
无话不说,无话不谈的地步确实没有。几年前的雨笛拒任何人都于千里之外,巫隐想接近她都要费尽心思。
“那后来怎么不说?”雨笛鼓着脸问。
“后来都忘了,哪里想得起来。”巫隐低笑着。
“你没有用过天机扇吧?”雨笛急不可待地道,小脸上充分急切。
巫隐向她伸出手,微微笑,雨笛奇怪但是有很放心地把手放在他的手中,等着他的下一步动作。
巫隐只是将她的手包裹起来,说着世间最动听的情话,“我不敢用,如果我死了,我怕你会为我伤心。”
明知道不可能,还一步步地对自己说着这种话,有可能的话,雨笛宁愿从一开始就不知道他是男子。
他的话如此惹人沦陷,无法自拔。
雨笛避而不听,抽出自己的手,顾左右而言他,“这里还有其他人呢。”
另外两个活人装作没看见,在聊其他事。
巫隐的眼神一刹那黯淡无光,恍惚间又明亮有神。
“那个,我们初步判断灾星已经消失了。”夜归冉轻咳了声。
“真的?”雨笛不信。
“就是不敢确定所以才说的是初步。”夜斯简回答道。
巫隐重新扣紧雨笛的手,淡淡道:“现在只能当做消失了,灾星本是天意降临,如若我们挡不住,也就只有让他降生。违天意,是要遭天谴的。”
雨笛宛然笑道:“谁说天意不可违,只是无人试过罢了。”那神情是撒娇,是巫隐很少看见的。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仍是简短的话,巫隐的嗓音适中,听起来就如同他的话一般令人异常愉悦。
“好了,我们也应该回家看看父亲了。”夜斯简挑挑刘海,长长地挡住了他俊毅的右脸。
他们在宫中当差,通常一两个月才回一次家。但夜斯简,夜归冉和巫隐是不一样的,他们只要不在皇上召见时,何时想回都可以。
最近因为灾星一事他们并未回过家,现在这事算暂时解决,是该回趟家了。
夜归冉修长的身子笔直而立,缓缓道:“堂姐,你也该多回家看看二叔他们。”
“我知道。”巫隐答得很痛快,雨笛看见他蹙额一闪而过。
巫隐对他的父母很冷淡,就像陌生人。从小就是如此,别人也不好说什么。
但总归是生身父母,这样的态度免不了闲人闲语。他们没做过什么让巫隐讨厌的事,如果非要说有,那也只有这个了。
八年前选举祭司,他们把尚且年幼的巫隐送上了选举台。
祭司这个职位说好不好,好的是祭司位高权重,无人敢得罪,不好的是一辈子无法嫁娶。
拥有挚爱很幸福,别人有的巫隐没有,别人没有的巫隐却都有了。
“夜,你什么时候能原谅他们?”雨笛对上他深邃的眼睛。
巫隐漠然地说道:“我从未怪过他们。”
“那你就不能对他们亲近点,他们好歹是你的父母。”
“人云亦云,雨笛你被他们影响了。”巫隐转眼看向广阔天地,心中坦荡无比,“我有我的骄傲,做了祭司还怎能再像从前。”
雨笛真想对他说,从前也不见你对人家有多好。
可话到嘴边又泄了气,这不是她该管的。
枫叶红了又谢,听雨眠的祭日也是这几天,雨笛生在一个一年之中最冷的日子,而她母后死在一个微冷的日子。
不管怎样,离开这里之前还是要再去看看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