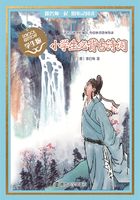“嘭嘭!”我满怀渴望地敲着门。
“来了!”我听见一个轻快的童音。
“妈!老爸回来了!老爸回来了!”芠修欢快地叫着。
“不就是老爸回来了吗!有什么好奇的!”我和芠修开着玩笑,亲热地抱起儿子。房间里有一股浓浓的香火味,略过儿子肩膀,我才发现客厅里有三个老太太坐在藤子沙发上正在吃饭,在人民医院后勤工作的四楼老乡张竟亮家属陪着他们。客厅东北角的一个角橱上摆满了糖果贡品,观音菩萨稳坐其上,三炷香烟袅袅,悠闲地卷入上方,在房间里弥漫着。
她没在客厅里,肯定躺在卧室里。
“李涵穹回来了,吃饭没有?快来一起吃。”张竟亮家属说。论辈分,我还得称呼她奶奶。
出于礼貌,我冲他们点了点头,抱着芠修扭头出了门。
“芠修,你妈在捣鼓啥?”我给芠修买了一把塑料左轮手枪。
“我也不知道。我妈请来的,烧香算卦的。”芠修欢快地拿过枪来,熟练地装着塑料子弹。
“走,芠修,老爸和你吃海鲜去。”我知道芠修喜欢吃海鲜。来到人民医院东面的“胶东小渔村”,我要了一盘辣炒花蛤,一盘海葵花籽,一份三鲜粥和芠修喜欢吃的炸“节柳鬼”。
“我不在家,你瞎捣鼓啥?”晚上回家,我劈头就问。卧室里不仅有一股浓浓的烧香味,还有一股重重的狗皮膏药味,我不禁皱了皱眉头,走到卧室南面开窗子透气。
“你别开!别开!我怕感冒着!我这身体老不好,四楼他奶奶说是不是犯了风水。以前这房子住过的主人得肺癌死了,她就帮我请了几个会做法的老太太,来帮我们看看这房子。”她说,“人家说了,咱们这楼是斜的,我们家又在最东北角,方位很不吉利,楼头北面又对着个大烟囱,不吉利,帮我们做做法事避避邪。”
“做什么狗屁法事!好!我找院长换房子。”我一听就火起来,没好气地说。
“有能耐你就换。”她顶上一句。
“有能耐你找院长去,就知道整天躺在床上当太后。”我也跟上一句。
“我没能耐,我个娘娘身子丫鬟命,我命苦,我哪有能耐!”她躺在床上向外扔着无赖。
“嘭嘭!”外面传来敲门声。
“芠修,看谁敲门?”我把抹布洗干净,扭干水,边倒退着边仔细地擦着地板。地板是新铺的,只要我在家里,我尽量保持整洁。本来崭新的地板,也不知有几天没拖了,到处是黑糊糊的东西,还带着油渍。芠修也不讲究,光着脚丫在地板上跑来跑去,粘得脚丫黑糊糊脏兮兮的。
“老爸,是小舅。”芠修继续在地板上像跳芭蕾舞一样跳跃着。
“姐夫,有没有办法帮我从红沙沟医院调出来?他娘的,李泉雨那个狗东西,就知道自己享受,刚买了个桑塔纳,坐够了,又和人家换了个桑塔纳2000,那个破地方没法呆了。”她三兄弟卫校毕业后托人去了安丘最好的一个中心卫生院,边发牢骚边“呸呸”地一口接一口痰吐在我刚擦过的地板上。我瞪了他一眼,不好发作,继续擦着。
“你干好自己的活,管人家那么多干啥!”我没好气地说。这小子自从分配到红沙沟医院就不好好干,整天横里吧唧的,院长拿他也没办法。有一次和妇科一起给一怀孕的妇女做流产手术,竟然把人家大网膜都给掏出来了也没掏出要掏的东西来,病人差点休克死掉,医院和病人唆了半年多才把事情处理完。为此,红沙沟医院院长李泉雨找我,“李涵穹啊,你怎么给我送了这么个惹事精,活不好好干,还蛮横横的,整天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像个二流子货。你这小舅子,我可管不了。”
“我怎么干好?那医院就那个样子。我是个干外科的,在那里很多我想开展的手术都开展不了。”他说着,脱下自己的外套,露出黑黝黝的胳膊,胳膊上刺着一只大肚子蜘蛛,蜘蛛头是一个大大的烟蒂烫成的。
我一阵恶心。“季菲,你看你,你刺那个东西干什么?”
“嘿嘿,那不是和小王谈恋爱,失恋后外科条件方便刺着玩的,又用烟蒂烫了个蜘蛛头,感觉造形很好,也去不了了,就保留下来了。为此,让李泉雨那个东西好训,说我耍黑社会。有什么不得了,不就是纹身吗,他懂不懂什么是美!”他说着,拿出一支“将军”烟点着。
“你能不能别在家里吸烟?不知道我闻着烟味恶心吗?”我说。
“好!好!不吸了。你清雅,你高洁,俺庸俗。姐姐,我赶紧回去了,不然赶不上公交车。他妈的,就是缺钱,真他妈要想办法挣钱。”他说着披上外套走了。
“你看,你娘家人就这形象!”我禁不住训斥她,她躺在床上一声不吭。
“老爸,明天早上你送我上学吧,不然又得我自己走着。”芠修睡觉前缠磨我。
“不行,等我不忙的时候吧。现在刚去上班,我还得准时赶到。明天一早我就走了。好了,芠修,快睡吧。”我说。
清冷的早上,不到五点,当别人还在暖暖的被窝里品味着不同的享受时,我已经瑟缩着在火车站等车了。昏暗的候车室里,躺着、坐着,用破黄大衣、破被子裹得紧紧的什么睡相的旅客都有。一个卖货的姑娘无聊地趴在柜台上迷糊着,只有一对打工夫妇好精神,男的30多岁偎依在女的怀里,女的爱恋地抚摸着他的乱乱的脏头,一只手轻轻地搬住,另一只手在乱发中仔细寻找着拔着他的白头发,笑嘻嘻地给他看看,然后放在手中轻轻一吹,让其飘入晨风中。
黎明的黑夜,
朦胧了我的眼睛;
昏黄的小站,
模糊了我的倦慵;
长长的铁路,
延伸着无言的人生。
看着熟悉的潍坊,我无法说出自己的心情。为什么偏偏离开别人想进都不能进得去的单位,为什么连送孩子上学的时间都给剥夺了?放弃或许是一种美丽,放弃或许是一种收获,但我看不到,至少现在看不到。看到的只有迷茫,只有模糊,只有凄冷。夜空时有流星倏而划过,留下长长的美丽的尾巴和无限美好的遐想。人生短暂,流星不如,在那一个什么具体工作都没有的闲职上,尚不知几年。三十而立,我都三十了,竟然一切从头开始,一个不知任何结果的悲壮的开始。
确实,当初不知道结果,结果却长恨当初。
100多公里的路程,我走了两个半小时,赶到松堡,正是几个书记和各管区主任上“早朝”的时候。我拿着杯子,前面是他们四个,好笑地走在他们后面,照例重复着他们每天安排工作的节奏。
“好,今天的碰头会就到这里,事情不多,主要关于每个副科级干部述职的事情。几个书记还有没有事情?”郑务聚问我们几个人。
我们几个都摇了摇头。
“大家还有没有什么事情?”郑务聚问各管区主任。
“郑书记,我们片分的那些小猪和老母猪就是凑不齐规定的数来怎么办?规定我们小猪30头,母猪10头,上哪凑啊?我们片养母猪的少,又不像大村片,有很多养猪专业户。”付戈庄片宣传委员李界朋为难地说。
松堡镇养猪专业户多,为了振兴农村经济,扩大饲养规模,镇上决定由松堡村牵头,党委、工商所和地税所组织在镇政府驻地大集生猪交易市场成立“生猪仔猪贸易市场”,逢大集交易。腊月二十三逢年关大集举行市场开业仪式,为此松堡村还专门请来了高密茂腔剧团唱戏三天。为了在开业这天起到轰动效果,党委要求每个包片的必须达到分配的仔猪和母猪指标。
“郑书记,我们片也是,没办法,只好安排支部书记到临镇去借猪。到临镇借的算不算?”包甸子片的组织委员杨禹善说。
“就这么点事还完不成,你们看着办。好!就这样,散会!高书记你负责去大集参加生猪仔猪贸易市场开业典礼!”他挥了挥他那特有的“黑五寸”短手。
“老杨厉害,竟然想起‘借种’!我那片再组织不起来,就把羊染成黑色当猪。”宣传委员李界朋和杨禹善开玩笑。
“你他妈的,界朋,把你在村里撒下的那些野种、野母猪拉到市场凑凑数也够了。”杨禹善也开玩笑顶上。
坐在办公室,我泡了一碗方便面,慢慢地吃着早饭,一大早赶来上班,这就是上班,我提前三个小时起床赶来的上班,无所事事的上班。年关到了,他们比平常都忙活得多,这时可以找很多漂亮的理由和借口谄着媚脸敲开领导家门,而我没有欲望,也不认识哪一个领导,更无须挖空心思地去考虑如何投机取巧。今天也不知干什么,我叹了口气。那些关于什么《农村工作指南》之类的书,我几乎都能背过,已经看得实在是无聊乏味。我顺便拿起一本在火车站买的《知青年代》,权当早饭小菜。里面讲述了下乡知青的不同经历和命运,总比那些没有任何文学水平罗列而成的条条框框的书要好看的多。
“早朝”过后,每个包片的骑着摩托车各自去管区了。郑务聚和荆兆明坐一个车去了财政局,高敬纲坐上桑塔纳去了生猪仔猪贸易市场,王地锡车上装了些礼品,说是过年打发公检法部门,整个大院仅仅两个小时的喧嚣便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我到办公室转了转,公务员李薇薇正在装订年终总结材料,忙活得不抬头;传达室老王在袅袅煤烟中,炉子上放了块铁板炒花生米吃。
“老王,今天怎这么平静?”我问。
“李书记,今天是腊月二十三小过年,又是大集,快过年了,没多少事,他们安排安排就去赶集置办年货去了。”老王说。
我也甩手来到了大集。毕竟是快过年了,摩肩接踵,熙熙攘攘。虽然残雪积水,冰凌垂吊,却挡不住热情高涨,人们恨不得在这一年能卖的卖,能买的买。
“锵刀子!磨剪子了!锵刀子!磨剪子了!”一个老人肩垫一块批布,在行人里面边走边吆喝着。
“高密菜刀了!高密菜刀了!老兄,来把菜刀?”一个小伙子高叫着,在菜板上“嘎巴嘎巴”剁着铁丝。
“小兄弟,算卦相面!不准不要钱!看你面相,日后要做高官。”一个中年人身着青衣古帽,坐在板凳上,面前一桌子,白布铺桌,上摆砚台笔墨,卦签摇筒,桌子前面的布上画有一幅阴阳八卦图,旁边写着:“一条明路指君行,将军下马问前程。”
我笑了笑,摇了摇头。蹲身在一个卖泥老虎的地摊端详起来,我拿起一个对着试了试,老虎“咕咕”叫着,发出低沉的声音。
“2块一个。”老人说。我掏钱买了三个,过年了,总要给芠修买点土玩具。
“咚咚!咚咚!拉洋片,看拉洋片!好看的拉洋片!许仙和白娘子的美丽传说!”一个老人头戴毡帽,脚踩架子鼓,身穿厚棉袄,笑容可掬。旁边立着一个椭圆形箱子,镶着五个镜头,上写“看拉洋片,每位2元”。箱子一边,还立着一块牌子:“拉洋片,又叫‘西洋镜’‘拉大片’‘看洋画’‘西湖景’‘八大片’,是老北京庙会或市场上常见的一种表演,其内容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中外名胜古迹的风景画,一种是传统的民间故事片段。‘拉洋片’相当于今天的幻灯片,在里面画框变换的同时,一人站在旁边配合精彩的唱腔让观众置身于精彩的故事中。”
“咚咚!哎哎,看到了没有?许仙和白娘子来到了苏堤,正是草长莺飞,一片花红柳绿,游人如织,好一派江南美景。哎哎,两人又沿苏堤前行,是段桥,传说是一位姓段的大户人家出资而建……一段恋情结束。下边哪一位看拉洋片?小伙子,看不看?”老人热情地招呼着我。
“小伙子,买不买年画?抹画子!抹画子!好看的抹画子!”一个老人对我说。
老人说的抹画子就是扑灰年画,记得小时候过年赶大集到处是,主要是关于“高级社”“互助组”“合作社”“年年有余”“胖小孩”等许许多多。随着印刷技术的改进,现在大多换成了现代画派,卖这东西的少了。扑灰年画是高密特产,又称“抹画子”。打好腹稿后,先用柳枝烧制成的炭条勾出轮廓,即粉稿,然后扑抹在另外的白纸上,就叫做“扑抹”。这是扑灰年画的第一道工序,如此可以扑抹数张画稿。如再增加数量,可以在扑好的一张画稿上再用柳枝炭条描一遍,重扑。成双成对的扑灰年画也是这样制成的。制作扑灰年画的第二道程序是手绘。扑抹是基础,手绘是关键。手绘复杂得多,主要包括“大刷狂涂”“细心巧画”“描子勾拉”“粉脸”“涮手”“赋彩”“开眉眼”“勾线”“涮花”“磕咸菜花”“描金”“涂明油”等步骤。卖这种年画的地摊在这里到处是,飘飘扬扬地洋溢着浓浓的年味。我逛着看了看,画主要有“姑嫂闲话”“踢毽子”“万事如意”“富贵平安”“八仙庆寿”“牛郎织女”“福寿双全”“双童献寿”“团扇美人”“渔翁得利”“福禄寿三星”“四季花屏”等。这种画倒是有地方传统文化特色,但也算不上好看和有欣赏价值,挂在墙上显得俗了点。我想买几张,低头看也没有合适的,算了吧。
“老鼠跑,老鼠跳,吃了我的老鼠药,蹦哒哒,蹦哒哒,半步倒,把命要。诸位乡亲,请看我的‘半步倒’,老鼠吃了它,半步跑不了。欢迎新老客户光临‘半步倒’,旧客户可拿老鼠尾巴换药,一条一包,春节大回报,一条尾巴一包‘半步倒’。”一个卖老鼠药的干巴老头卖尽风骚,连跳加唱,如同跳“大神”。
生猪仔猪贸易市场热闹非凡,人欢猪叫。小猪到处跑,母猪找小猪,大人找母猪、小猪,没办法,有的干脆找个大网包把小猪圈起来,有的找错了猪吵得脸红脖子粗。
最热闹的要数戏台子唱茂腔的。老太太老头子不嫌寒冷,安心地坐在那里听戏。戏台上正唱着茂腔《小姑贤》。
儿媳我去包包子,
包包子俺不吃它,
听着为娘拉一拉:
羊肉,猪肉滑,
白萝卜馅子娘嫌苦,
红萝卜馅子甜打撒,
韭菜老了塞俺的牙,
塞在牙里没法剔拔。
一个小媳妇青装淡抹扮演儿媳妇,一个高个老头带着个老太太帽子,头插一枝花,穿着个大襟衣服,扮演剧中婆婆,把枣红色拐杖捣得地上笃笃响,气哼哼地嫌儿媳妇做这太咸,做那太淡。唱得字正腔圆,演得惟妙惟肖。
“大兄弟,买本书吧?相书、卦书、人生四时、文革逸闻、正史野史,一应俱全。”一个卖书的招呼着我。我眼睛一亮,蹲身看着书。书很多,有关于卜宅、相宅、相地、堪舆、风水之类的书,有关于文革历史的,还有许多宫廷秘史,但几乎都是盗版的。我随手拿起一本《易经》,易经有很多版本,这一本是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的,作者是珍泉,翻开看来,讲述比较详细,也没有多少错别字。
“老板,这本《易经》多少钱?”我问。
“35元。”卖书的还在招呼着别的顾客。“你先看还有没有需要的书,待会儿优惠一起算。”
难得地摊上见《参同契》,据说是后汉桓帝、顺帝时魏伯阳又名火龙真人所著的道教最早的丹鼎派理论著作。我又拿起《周易十日谈》《麻衣神相》《手相大全》《四柱预测学》《居家风水》等几本书翻阅着。
“老板,有没有‘河图洛书’‘开元占经’‘大小六壬预测法’‘梅花易数’之类的?”这些都是我不知什么时候就知道的一些玄学的名字。
“没有。家里还有奇门遁甲、紫微斗数。”卖书的回答。
蹲在地上腿疼,我起来活动了一下,又挑了几本《毛泽东的读书生活》《文革秘史》《江青传》《四人帮传》《毛泽东读古书》《毛泽东的晚年与早年》《文革研究》等。
“兄弟,还有光盘要不要?这东西过瘾!”卖书的问。
“不要。要这些就够了。算一算,多少钱?”那些垃圾不是我关注的。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偏偏喜欢这些玄学、道学之类的书。
“兄弟,150元。我全部给你五折。”卖书的说。
“给我包好。以后再有这样的书给我留着。”我毫不犹豫地掏出150元。在农村的大集上,竟然发现还有这样的书,已经不易了。
我两手提着书,来回晃悠着,像个打猎的挑着山鸡轻哼出山,像其他赶集的买着白菜、粉条、猪肉、各色糕点、烟花烧纸一样满载而归。
“李书记,去赶集买的书,还没吃饭吧?”伙房里负责采购的小富在大院里见到我,问我。
“看着玩,净些盗版的。还没吃呢?”我说。
“你给我饭盆,我给你打去。”小富接过我的书。
“好。小富,谢谢!”我把饭盆递给他,迫不及待地整理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