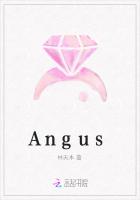“仕途,你家也不能落下。他们收锅铁的怎么没到你家里?不管怎么着,也要为革命作贡献,早日实现毛主席提出的钢铁产量赶英超美的论断。自己仔细找,看家里有哪些带铁的东西,撬下来交公。这急死了,人家方家埠和土山村都敲锣打鼓向镇上报喜了,我们炼了顿子,还没炼好。别忘了啊!”王成才说。
“知道了,一定。”父亲在回家的路上,不断见到大人、孩子用筐子抬着自己家里的破锅烂铁向老槐树底下走。筐子里什么样的铁器都有,剪子、锤子、破铁锨、破簸箕、破门鼻子,只要含铁的就被撬了下来用于炼钢铁。
父亲刚到家,大队的片长王三麻子领着一伙人气势汹汹地闯了进来。
“仕途,交铁!交铁!谁不积极响应大跃进,谁就是反革命。谁说你家因为老四是麻风病人就不来收铁了,为了革命,为了响应毛主席号召,我来,我不怕!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快找,快搬!这锅,这镢,这铁疙瘩,都收走。没有铁引子怎练成钢铁?”王三麻子曾经得过天花留下了一脸麻子,排行数三,因此得外号“三麻子”。
“大兄弟,锅搬走了,我们拿啥做饭哪?”奶奶拦着问。
“大娘,你就等着过好日子吧,人民公社了,进入共产主义了,吃饭不要钱了,敞开肚皮尽管吃,还要锅干啥?”王三麻子说。
大伙不断地找着带铁的东西向外搬 ,把炉底都扒出来了。
王三麻子在房间里转来转去,他的眼睛落在奶奶出嫁时的一个楸木衣服柜子上的铁锁和铁鼻子。
“咦!这不也是铁吗?拿扳手来!”王三麻子吩咐道。
“大兄弟,就这么点小东西,你就放过吧!”奶奶哭着说。
王三麻子不说话,随着轻微的咯吱声,锁和铁鼻子被撬了下来,“当啷”一声闷闷地掉到地上。
“还有谁家?”王三麻子问。
“没有了。”有人回答。
“还有,就是那高老头家。”又有人回答。
“慢条斯理地唆啥?三句蹦不出个屁来!真是的。快去!”王三麻子不耐烦。
全村社员都集中在老槐树底下大炼钢铁。
老槐树的西边,是一堵厚厚的水泥高墙,墙上画的毛主席老人家精神奕奕,满面慈祥,头带大斗笠,上穿白色衬衫,下穿束腰的大肥裤,一手臂上搭着衣服,一手拿着镰刀。老槐树的东边,是一块石雕像,一壮汉伸开有力双臂将一座大山从中劈开,下面文字是:“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老槐树上,三面红旗高高地插在树干中间,上面醒目的大字“人民公社万岁!”“大跃进万岁!”“总路线万岁!”树丛里,一个高音喇叭起劲地唱着“跃进跃进大跃进,快马加鞭向前进。十五年内赶上英国,中国人民有信心”。树底下,十几个小高炉散落排开,像一座座矮小的碉堡,冒着缕缕黑烟。王成才领着社员忙活得热火朝天。有拉风箱的,有操炉出钢的,有填木材、焦炭、铁矿石和各家各户收来的那些锅碗瓢勺、脸盆、驴马的嚼子、晾衣服的铁丝儿、生锈的铁钉等。那木材是就近取材,从降媚山上伐的。郁郁葱葱的降媚山因为大炼钢铁,浑身被砍的像被拔了毛的老母鸡。为了大炼钢铁,果树也难逃厄运。老曹鬼的果园入了社以后,如胭仍然把那些果树看做自己孩子一样,如今也被王成才作为炼钢战备而用,看着粗大的十几年的苹果树被锯断,如胭心疼地直打哆嗦。而那些焦炭和铁矿石都是社员从40公里外的坊子推来的。父亲也曾被安排去坊子推煤,两天一趟,一车子装不了多少,只不过几百斤,路上再颠颠簸簸,推到村里剩不下多少了,有的偷懒的社员干脆把一部分倒进沟里,减轻负担推着跑。
精神是高涨的,干劲是十足的。为了让炉火更旺,社员们用扇子扇,用吹火筒吹,几个人鼓着腮帮子一齐吹。人炼铁,铁炼人,炼铁的烽火燃遍全村。老槐树下歌声嘹亮,烟雾缭绕,一派繁忙热闹的炼钢气象,使人不由得想起真个“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
“乡亲们,加把劲,多出铁水淹死那美国鬼子!”王成才挥臂高呼。
“钢”炼成了,一团黑紫色渣滓像乌龟一样摊卧坑中。王成才领着社员敲锣打鼓,手举红旗,步行5公里,去镇上报喜。那红旗飘飘,上面一个特大的“喜喜”,“喜喜”下面是“热烈祝贺秦戈庄大炼钢铁成功”。
王成才被推选为劳动模范,在全县大会上发言交流,出尽了风头。
秋天到了,是个难得的大丰产年。黄豆嘀里嘟噜、串串厚实压得都爬下了身子,粗壮的玉米顶着长长的黄色的大棒子,个个籽粒饱满;满坡的肥大的地瓜把地面都撑得裂着缝,能看得见地瓜黄色暗红色的皮肤欲裸露地面;熟透了绽开的棉花像朵朵白云挂在枝头上,随风摇曳跳动着;使狗河河边沙土地里的花生带着黄黄的壮壮的秧子,随手一拔就是一大墩;降媚山上剩留的苹果树、枣树挂的满满的,风一吹,那串串枣子发出轻微的啪啪的撞击声,熟透了的吧唧吧唧掉落下来。那种当地叫“仓老鼠”的田鼠被这样一个大好的秋天撑得艰难地晃动着身子爬来爬去,比往年繁殖能力明显增强,到处见“仓老鼠”挺着怀孕的大肚子,身后还跟着一大群小不点坦然地晒着太阳享受人间快乐。黄鼠狼、乌鸦、麻雀、大雁、斑鸠比往年也增多了,趁着人们在忙碌大跃进,频繁出动,搬粮弄仓,享受着他们想象中的现实的共产主义。
“那年真怪了,历史上少有的风调雨顺,种什么长什么,什么虫子也没有。”父亲回忆说。
丰产不丰收,疲于奔忙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人们把大批的玉米扔在田野里,地瓜用犁一翻就埋在地里,棉花烂在地里没人拾,花生熟透了散在地里没人来得及刨。一场秋雨洗过,大多烂在地里,很多又重新发芽,遍地绿油油的花生苗,在秋天的田野里形成一道独特的春天风景。好大的一个丰产年就这样白白地荒在田野里,烂在田野里,烂在疯狂的大炼钢铁里。
一溜长排桌,社员们坐在凳子上紧张地吃着饭。
“三叔,再来碗菜,一个馒头。我还没吃饱。”大狸猫站起来向分饭的李仕隆说。
“就你肚子大,干活净知道偷懒,吃饭来劲头了。”李仕隆说。
“这不能怨我啊,我饭量就是大,活也没少干啊,就是炼不出钢来。再说,人民公社不是管饱吗?那我们跑进共产主义来干啥?他妈的,这共产主义就是男女分开睡觉啊,我和我老婆快两个月没在一起了。”大狸猫嘟囔着。
“你小子说话小心,不怕挨批斗啊!”仕隆说。
大狸猫倒还有精神。父亲胡乱扒了碗饭,又回家给四叔送好饭,回来在草垛旁一歪就睡了。按大队意见,四叔享受村里五保待遇,可以不干活,或安排一些自己独立的活,但不能和社员们一起干活,因为大家都反对,王成才和仕光大爷也没办法。其他社员也像打了败仗的国民党士兵一样无精打采,钢没炼出多少,连日的无休止的劳累使大家站着就想睡觉。大狸猫看炉的时候不敢睡,推煤的路上把小推车一放就睡。
“仕光,仕光,醒醒,醒醒,别睡了!”王成才摇晃着仕光。
“按照上级指示,农业要提高产量,必须深翻地。下午你领着你队里的社员,还有朱功深那个队先拉上去,学校里也发动起来了,去村北面把那十三亩地翻了。最浅两尺,三尺更好。”王成才说。
村北十三亩地,因为那个地方土地连片成十三亩而得名。在秋天的原野里,地里一片热气腾腾,三个生产队的人马都拉上来了。大家互相比赛,用锨挖着土,掘的地里像战争年代的壕沟一样,生土熟土都掺在一起。上级说,深翻地是为了夺高产,究竟多深才能算是深,谁也讲不清。没有人提出怀疑,也不敢提出怀疑,个个鼓足干劲,力争上游,铆足劲儿大翻猛翻。你翻两尺,我就翻两尺半;你翻两尺半,我就翻三尺。谁翻得快、翻得深,就叫放了“卫星”,就是光荣,就是先进。工地上喇叭高鸣,干劲冲天,学校的学生也参与进来。三麻子家女儿嗓子又甜又嘹亮,担任播音员随时播报着不同地方的进度,一会儿一个“捷报”,一会儿一个“卫星”。还穿插着流行歌曲“稻米赶黄豆,黄豆像地瓜;芝麻赛玉米,玉米有人大;花生像山芋,山芋超冬瓜;蚕长猫一样大,猪长像大象;一棵白菜五百斤,上面能站个胖妹妹;鱼苗撒下千万条,条条养得扁担样;玉米秆儿穿九天,浑身棒子有几千……”那架势,那劲头,就这几亩地打出的粮食足够一个飞水镇的人吃了。
为了创造“高产田”,王成才特意在生产队南边菜地里挖了一个长10米、宽5米、深1.5米的大坑,在坑里施上30厘米厚的大粪,然后撒上了20斤麦种,却没有长出一棵麦苗。因为施肥过量,麦粒刚出芽就让大粪给烧死了。无独有偶,土山村为了和秦戈庄比试,把村民圈里的粪全部集中起来,在上面栽上地瓜苗,以创造地瓜高产田,结果与王成才的杰作一样。
“大跃进”中,一些领导干部到基层宣传、描绘共产主义、人民公社的美好前景,以鼓励人民的奋斗精神。在描绘公社的好处时认为,首先,有好的食物,而不仅仅是填饱肚子。每顿有肉、鸡、鱼、蛋,还有更精美的食物如猴头、燕窝、海味等,都是按需供给。第二,衣服穿着方面,一切要求都可满足。有各种花色和品种的服装,而不是清一色的黑色和蓝色。将来,普通服装仅作为工作服使用,下班后,人们就换上皮服、呢绒和羊毛制服,当人民公社都养了狐狸,那时外套就都是狐皮的了。第三,房屋都达到现代城市的标准。现代化是什么?在屋子的北厢有供暖设备,南厢有冷气设备。人们都住在高楼里,不用说,里面有电灯、电话、自来水、无线电和电视。第四,除了跑步的选手外,旅客和行人都有交通工具,航班通向各个方向,每个省都有飞机场,每个地方都有飞机制造厂的日子也不远了。第五,每个人都受高等教育,教育已经普及。这幅人民公社的美景,真让几亿农民乐得合不上嘴。
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康生拟写了一副对联:“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先把人民公社这座桥梁架起来,过了桥就是天堂了。
如今,人民公社成立了,共产主义进来了。时间到了1959年的共产主义社会。由于大食堂的惊人浪费和对1958年大丰产年的破坏,没有多久,食堂就维持不下去了。1958年冬天刚过,食堂力不从心渐渐不支,先是一日三餐变成了两餐,馒头变成了“耙菇”,“耙菇”变成了带着馊味的黑黑的霉烂的东西,后来就是两餐变成了稀饭,再到后来,干脆连稀饭都支撑不下去了。食堂的烟囱眼看着由浓浓的烟雾慢慢变淡,最后烟囱冒不出烟了,关门似乎就在朝夕之间。社员们没有了大炼钢铁的灿烂光彩,个个饿得饥肠辘辘,那一堆堆铁疙瘩在这时黑糊糊地趴在那里,什么作用都起不了了,更不能充饥。
“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