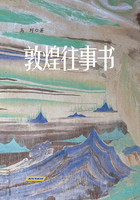那年春天,也就是我打算结婚的那一年春天,一颗彗星出现在我们村子的上空。那是我们见过的最亮也是最不祥的彗星。每天晚上,看着它爬过村子的上空,散播悲伤的种子,我们都试图揣摩它所传递的可怕信息。哈吉·阿里——村里最有学识的人——去了一趟伊斯法罕,从大星相师那儿取回了一份年鉴,以让大家了解将会发生什么灾难。
他回来的那天晚上,村民们都聚集起来,聆听这一年的预言。我和父母就站在老柏树的旁边。这棵老柏树是村里唯一的一棵树。上面挂着各种各样的布条,代表人们的誓言。每个人都神情凝重地翘首仰望星空。娇小的我正好可以从哈吉·阿里那看起来像沙漠中的灌木丛般的大胡子下望向天空。我的母亲——玛辛,指着在夜空中熊熊燃烧的火星说:“看那火红的火星!它会纵容彗星的邪恶。”
许多村民都已经知晓了彗星神秘的征兆,或者听说了彗星所带来的不幸。伊朗北部发生了一场瘟疫,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非命。都格巴达的一个新娘由于地震被困于家中,在她见到新郎之前就已同女宾们一并窒息而死。至于我们村,从未见过的红色昆虫在农田里泛滥成灾。
我的闺中密友歌莉和较她年长许多的丈夫哈桑·阿里一起回村了。她吻了吻我的脸颊,向我问好。
“你感觉怎样?”我问。她的手滑到肚子上。
“很沉重。”她回答。我知道她一定是在为腹中的新生命而感到担忧。
不久,除了老弱病残,大家都已经聚集在一起了。大多数的女人都穿着瘦长的裤子,外面罩着明亮的钟形短袍,头上戴着有流苏的头巾。而男人们则穿着白色的长袍和裤子,戴着白色的头巾。只有哈吉·阿里戴着黑色的头巾,以表明他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子孙。他的手上仍然拿着那个和他形影不离的测星盘。
“亲爱的村民们,”他说话了,声音低沉得就像轮子轧过石头的声音一样,“首先让我们颂扬先知穆罕默德的追随者们吧,尤其是他的女婿阿里,天下信徒之首。”
“愿安宁伴他左右!”我们回应道。
“先说说今年预言中关于敌人的坏消息。东北部的乌兹巴克将遭遇猛烈的虫灾,庄稼尽毁。西北部的土耳其人将会出现逃兵现象。在远西的那些基督教国家中,一场不明原因的疾病将会使它们的国王焦头烂额。”
我的父亲——伊斯马仪,靠向我小声地说:“知道敌人将遭遇不幸总是感觉很好。”我们都笑了,因为事实的确如此。
当哈吉·阿里继续宣读那份年鉴时,我的心就像爬山时一样“怦怦”直跳。我很想知道关于今年举行婚礼会有什么预言——这是我最关心的问题。我开始摆弄头巾上的流苏。母亲总是督促我要改掉这个坏毛病。哈吉·阿里说有关纸、书以及写作的各项事宜都无大碍;南部将发生一场轻度地震;国家将会卷入一些激烈的战斗,鲜血将染红里海。
接着,哈吉·阿里向人群挥舞着手中的年鉴。当接下来的预言需要引起人们的警觉时,他总是会这么做。他的助手,在整个过程中一直拎着一盏油灯,而这时已跳到一旁为阿里腾出空间。
“也许最糟糕的事就是今年将会有一场广泛的不明缘由的道德败坏风潮。”他读道,“这个败坏风潮只能归咎于彗星的影响。”
人群中开始低声抱怨他们在新年伊始所见到的败坏行为。“她从井里过量取水了。”我听到泽依乃拜说,她是戈兰姆的妻子,对别人从来没有好话。
哈吉·阿里终于说到与我的将来有关的问题了。“关于婚姻,未来的一年是复杂的,”他说,“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举办婚礼并无大碍,但是后半年缔结的婚姻将会充满爱但也充满冲突。”
我焦虑地看着母亲,因为我打算那时候结婚,而且我已经十四岁了。她的眼中也满是顾虑,我能看出她不喜欢听到这些。
哈吉·阿里翻开年鉴的最后一页,抬起头,停顿了一会儿,以引起群众的注意。“最后的预言是关于女人,也是最令人不安的预言,”他说,“在这一年,伊朗的女人们将不再顺从。”
“她们什么时候顺从了?”我听到戈兰姆如是说,他的周围发出一些窃笑。
父亲对母亲笑了笑,她也因此而开颜。父亲深爱着母亲,就像母亲深爱着他一样。人们都说父亲对母亲如此温柔,仿佛母亲是续弦之妻。
“女人们将为她们的任性妄为付出代价,”哈吉·阿里警告人们,“许多人会受到诅咒不能生育,而那些得以孕育后代的女人们将会因异常的疼痛而恸哭。”
我和歌莉目光相触,我在她的眼中看到了我的恐惧。歌莉为生孩子而感到忧心,而我为这糟糕的预言而苦恼。我祈祷彗星会飞向太空,让我们安然无恙。
看到我在颤抖,父亲把一床羊毛毯子裹在我的肩上;母亲把我的手放在她的手心揉搓,为我取暖。站在村子的中心,我的周围是我所熟悉的家园。我们的小清真寺就在不远的地方,寺顶闪着瓷瓦的光芒;我每周沐浴的澡堂蒸汽腾腾、灯影斑驳;那个破旧的木棚是每周二才开市的小市场,村民们就在那儿买卖水果、蔬菜、药品、地毯和各种各样的工具。一条羊肠小道穿梭在这些公共场所和一群泥砖砌成的家宅中——那儿是村里两百个灵魂的安身之处——最后消失在山脚之下。这些车辙绰绰的小道便是我的山羊觅食的地方。所有这一切都让我感到安慰。因此,当母亲轻掐我的手看看我情况如何时,我也轻轻地掐了掐她的手。但接着,我抽回了双手,因为我不想像个孩子一样。
“爸爸,”我小声地问父亲,“如果哈吉·阿里的预言成真了怎么办?”
父亲隐藏不了眼中的担心,但是他的声音却很坚定。“你的丈夫会用玫瑰花瓣为你铺路,”他回答,“如果他对你不敬……”
他停顿了一会儿,横眉怒目,似乎他将做的事会难以想象的地可怕。他动了动嘴唇,仿佛要说什么,但始终没有说出来。
“……你随时都可以回到我们身边。”他说。
回娘家的妻子会使家人蒙羞,遭人斥责,但父亲似乎并不在意。在对我笑时,他和蔼的双眼在眼角泛起些许皱纹。
哈吉·阿里在简短的祈祷中结束了集会。有些村民和家人聚集在一起讨论那些预言,而其他人则开始陆陆续续回家。歌莉看似想说些什么,但她的丈夫告诉她该回家了。她小声告诉我她的脚因腹部的重量而感到疼痛,然后就向我道晚安了。
我和父母从村里那条唯一的泥泞小道走回家。道路两侧的住宅似乎都依偎在一起相互取暖,相互保护。我对这条路如此熟悉,甚至闭着眼睛都能在该转弯的时候转弯,走到家。我们家就在村尾,再过去就是沙地和灌木丛了。父亲用肩膀推开木门,我们便走进了这个只有一间屋子的家。屋子的墙是用泥草砌成的。白色的墙粉使墙壁明亮了起来。在母亲的打理下,它总是干干净净。墙上有一扇小门,从这扇小门出去便是一个封闭的院子。我们常常在院子里享受阳光,而无须理会别人的目光。
母亲和我解去头巾,脱去鞋,把头巾挂在门口的挂钩上。我甩了甩长及腰际的长发,摸了摸在门边矮柜上光亮弯曲的野山羊角,祈祷能有好运。一个周五下午,父亲在和我散步时,击毙了一只偶遇的野山羊。从那天开始,这个羊角就成为我们家中值得骄傲的一件物品。父亲的朋友常常赞扬他如野山羊一样敏捷。
父亲和我肩并肩坐在棕红色的地毯上,那地毯是我在十岁的时候编织的。他闭目养神了一会儿,我觉得他看起来非常疲劳。
“我们明天还散步吗?”我问。
他的眼睛慢慢睁开,“当然了,小宝贝。”他回答。
父亲早上必须在农田里工作。但是他坚持除非真主召唤,否则任何时候都不会中断我们的散步。“因为你即将成为一个繁忙的新娘。”他沙哑地说。
我把目光转向别处,因为我不能想象要离开他。
母亲扔了些干粪到炉子里烧水泡茶。“给你们一个惊喜。”她一边说一边给我们端来一碟新鲜的鹰嘴豆甜饼。这些甜饼散发着玫瑰的香味。
“愿你的手永远康健!”父亲说。
这是我最喜欢的甜点,所以我吃了很多。不久,我开始觉得累了。于是我像平常一样在门附近打开铺盖。我在父母的交谈声中睡着了。他们的声音让我想起了鸽子“咕咕”的叫声。我甚至似乎看到了父亲搂着母亲,并亲吻了她。
第二天下午,看着大家从农田里纷纷回家了,我站在门口翘首期待着父亲归来。我总是喜欢在父亲进门前就为他斟好茶。母亲正蹲在炉子前烤面包准备晚餐。
父亲仍然没有到家,我走回屋,剥了些核桃放在小碗里,把采摘来的蝴蝶花插在一个装着水的小罐中。我又走出门,看看父亲是否已经回来,因为我很期待与他一同去散步。他在哪儿呢?许多人都已经从农田里回来了,也许此时正在他们的院子里洗去一天的尘土。
“我需要些水。”母亲说。于是,我抓起一个陶罐,走向水井。在路上,我碰到了染匠易卜拉欣。他奇怪地看了我一眼。
“快回家吧,”他对我说,“你母亲需要你。”
我感到奇怪。“但是她刚才叫我来打水。”我说。
“没关系,”他回答,“告诉她是我叫你回去的。”
我飞快地走回家。陶罐“砰砰”地撞着我的膝盖。快到家时,我看到四个男人搀扶着一个瘫软无力的人。也许在农田里发生了什么意外吧。父亲时不时会带回一些这样的故事,比如有人被打谷耞弄伤了,或者是被骡子踢伤了,或者是在打架中流血了。今天,他一定也会在喝茶的时候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
这些人艰难地扶着伤者向前走着。他的头靠在一个人的肩上,所以我看不到他的脸。我祈祷他能早日康复,因为男人生病无法工作的家庭将会很艰苦。当他们走近时,我发现伤者头巾的裹法很像父亲的。我赶快告诉自己,这没什么。很多人裹头巾的方式都是一样的。
前面的那个人踉跄了一下,让他们几乎抓不住伤者。他的头耷拉着,仿佛已经不是身体的一部分,双腿也软弱无力。当我看到他的脸时,手中的陶罐应声落地,碎片散落在我的双脚四周。
“妈妈!”我呜咽着大叫,“快来!”
母亲一边走出来,一边在衣服上擦掉手上的面粉。当看到父亲时,她尖叫了一声。住在附近的女人们纷纷走出屋子,像一张网似的围着母亲。母亲悲伤地号啕大哭,痛苦地扭动着身体。那些女人们轻轻地抓住她,扶着她,拨开她脸上的头发。
他们把父亲扶进屋,让他躺在床上。他脸色蜡黄,嘴角淌着唾液。母亲把手放在父亲的鼻孔前探了探他的鼻息。
“赞颂真主,他还在呼吸!”她说。
和父亲一起在农田里工作的纳吉在告诉我们事情的经过时,双眼不知道该看哪儿。“他看起来很累,但是在下午之前还很好。”他说,“突然,他抓着头倒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气。后来便不省人事了。”
“愿主保佑你的丈夫!”一个我不认得的人说。当他们尽己所能地让父亲舒适一些后便离开了,嘴里喃喃地为健康祷告。
母亲眉头紧蹙地帮父亲脱去棉鞋,抚平他的罩衫,整了整他头下的枕头。她摸了摸父亲的手和额头,说父亲的体温正常,然后吩咐我去拿毯子给父亲盖上,让他保暖。
父亲的事在村里迅速传开,朋友们纷纷过来帮忙。科尔苏带来了她在第一场春雨中接的雨水。毛拉已经为这些雨水祈过福。科尔苏将这些水洒在屋子里,以庇佑父亲能早日康复。易卜拉欣站在院子里,开始诵读《古兰经》。歌莉手里抱着熟睡的儿子,给我们带来了热面包和炖扁豆。我泡了一壶茶让大家暖身,然后跪在父亲身旁,看着他的脸,祈祷他能眨一眨眼睛,或者甚至扭曲一下面部——任何让我确信他仍然活着的讯息。
村里的医生拉比阿在夜幕降临时分来了,双肩各背着一袋满满的草药。他把草药放在门边,开始为父亲检查。油灯的灯光很昏暗,火苗不时地跳动。在检查父亲的面部时,他眯起眼睛,说:“我需要更多灯光。”
我从邻居那儿借了两盏油灯,放在被褥旁边。医生托起父亲的头,小心翼翼地揭开他的头巾。他的头看起来严重浮肿。灯光下的他面色如蜡,斑白浓厚的头发也显得僵硬、灰白。
拉比阿摸了摸父亲的手腕和脖子,发现没有找到自己要找的东西,于是把耳朵贴在父亲的胸前听着。这时,科尔苏小声地问母亲是否需要添些茶。医生抬起头,让大家安静。再次倾听之后,他起身,面色凝重地说:“他的心脏在跳动,但是很微弱。”
“阿里,人类的王子,请赐予我丈夫力量吧!”
拉比阿拿起他的布包,抽出一些草药,告诉科尔苏怎样煮强健心脏的汤药。他承诺明天早上会再来为父亲检查。“愿主赐福于你!”他说完便离开了。科尔苏折去草药的茎,把草药扔进罐子里,加入母亲刚才煮沸的水熬炖。
拉比阿离开的时候,停下来和站在院子里的易卜拉欣说了几句话。“不要停止祷告。”他警告说。然后我听到他小声说:“真主也许今晚就会召唤他了。”
我仿佛在舌尖尝到了铁锈似的味道。我找到母亲,冲进她的怀抱,和她相拥着哭了起来。我们都能从对方的眼里看到悲伤。
父亲开始发出一些喘息的声音。嘴角仍然淌着唾液,嘴唇微微分开。他的呼吸粗重得像风扫落叶般。母亲从炉边冲过来,草药的汁液染绿了她的双手。她倾身看着父亲,大叫道:“天啊!我的爱人!天啊!”
科尔苏赶忙走过来,凝视父亲,然后拉着母亲走回火炉边,因为我们都爱莫能助。“我们赶快炖好药,帮助他减轻苦难吧。”科尔苏说。科尔苏的双眼总是那么明亮,脸颊微红如石榴,证实了她草药师的力量。
草药炖好冷却之后,科尔苏把药汁倒入一个小碗里,端到父亲身旁。母亲托起父亲的头,科尔苏小心翼翼地用勺子试着把药喂进他的嘴里。但是大部分汤药都溢出来,浸湿了被褥。第二次,汤药喂进去了,但父亲被汤药呛得喷出药汁,有一会儿甚至几欲停止呼吸。
总是十分冷静的科尔苏放下碗,摇了摇手,看着母亲的眼睛,建议说:“我们最好等他睁开眼睛了再试。”
母亲的头巾歪了,但她没有注意到。“他需要吃药。”她疲弱地说。科尔苏告诉她父亲更需要呼吸。
易卜拉欣的声音开始变得沙哑。科尔苏让我去照顾照顾他,我倒了些热茶,拿了些院子里种的椰枣给他。他用眼神向我表达谢意,但是没有停止诵读,仿佛他的诵读可以延续父亲的生命。
走回屋的路上,我撞上了父亲的手杖。它就挂在通往院子的小门旁边。我想起上一次散步,父亲带我去看了一尊藏在瀑布后面古老的女神雕像。我们沿着礁石慢慢移动,直到找到那尊藏在水流之下的雕像。女神戴着一顶高耸入云的王冠,美丽的胸前飘着一块薄纱,脖子上戴着用大石头做成的项链。她的双脚被衣服遮掩着,那衣服似乎要卷进水流之中。她张开有力的双臂,宽阔的怀抱不让须眉,仿佛可以随心所欲地向瀑布施法。
那天,父亲很累,但他仍然气喘吁吁地从陡峭的小道一直走到瀑布,带我去欣赏那令人惊叹的景观。此时,他的呼吸越来越吃力了,呼气时还“呼呼”作响。他的手也开始抖动,就像焦躁不安的小老鼠一样。它们爬上他的胸膛,挠着他的罩衫。长期在农田里工作,他修长的手指被晒成了棕色。指甲缝里还有一层土。平时,如果不是很累,父亲在进屋前就会把指甲清理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