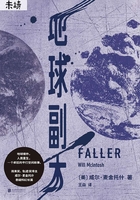引言
湖北土家族作家羊角岩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以庞大笔触抒写反映鄂西清江民族风情的乡土诗集《鄂西倒影》(他写诗时使用的笔名是其本名刘小平),2000年荣获“湖北文学奖”,随后湖北电视台根据其诗作拍摄的诗歌艺术片《清江倒影》获第六届湖北省“五个一工程奖”。清江土家文化情结是其诗歌的起点,《绣鞋垫》、《鹭鸶》、《腊月》、《傩戏》、《下里巴人》、《女儿会》等一批简洁、凝练、充满浓郁乡土情结的作品,为其建构了一个地域文化的高地和根据地。2004年后,他开始转向小说创作。2007年12月号《民族文学》杂志上他开始以“羊角岩”为笔名发表了小说处女作《一滴水消失于清江》(中篇小说),旋即长江文艺出版社于2008年7月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红玉菲》。《红玉菲》总约30万字,于2006年10月动笔,12月初完成初稿,其后得到武汉大学著名文学理论家於可训教授、三峡大学罗义华博士精心指导,七易其稿。该著讲述的是鄂西南清江中下游“盐阳村”农家子弟田浩禄高中毕业返乡劳动,参加高考被“政审”卡住进不了大学门槛,进县制药厂当临时工因解决不了“农转非”而长期饱受歧视、排挤甚至被陷害沦为阶下囚,却最终不放弃做人良知与追求理想,由一名打工仔成长为知名企业家的故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詹晓厚在《中国民族报》上评论:《红玉菲》的主人公田浩禄30年挣扎的创业史就是清江边土家儿女在当代的奋斗史,也是整个少数民族在改革开放年代的命运的一个缩影[1];於可训教授认为“《红玉菲》是一部反映当代青年的奋斗史和成长史的小说。田浩禄的经历,在当今中国,尤其是对正在奋斗中的农村青年来说,有较广泛的代表性”[2]。那么这部羊角岩从诗歌到小说的“转型之作”到底有什么独特的文化蕴涵和小说学价值呢?
一、历史审视,反思当代岁月沧桑
《红玉菲》独特的表面结构是以三个女性覃怡红(红)、向明玉(玉)、郑菲菲(菲)名字结构布局,贯穿于男主人公田浩禄的成长史和奋斗史,其实在其背后还有一个隐性结构布局,即以岁月变迁来影射时代的沧桑风云。在这里,作者采用了“户口”、“政审”等特定时代无可怀疑的社会历史符码来绾结。其中社会巨变及主流意识形态对人物命运的影响尤为巨大,对一个青年理想的伤害也最深。
田宏伟(国民党逃兵)的早死,让田浩禄家孤儿寡母成为盐阳最穷的人家,其大爹田宏发去台后的“海外敌特关系”,更使其在高考政审时尽管以高分322分(夷水区第二)而无缘大学门槛,及至在冲出盐阳后的制药厂招工考试中又一次以这个理由被拿下,当时主流意识形态(二元对立的战争文化心理)对社会的控制可见一斑;“文革”初期,马必贵是盐阳的土皇帝,靠造反起家,把盐阳村的女人们视为可以随便占有的“便宜”,田浩禄与马必贵的恩怨本质上就是暴力和反暴力斗争的结果,甚至包括向明玉的香消玉陨也不能不说与这件事有关。从文化上讲正如王富仁在《中国反封建的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中所指出的那样,“即使阿Q成了‘革命’政权的领导者,他将以自己为核心重新组织起一个新的未庄等级结构”[3]。巴山县制药厂的胡周银(胡诌)、慕容聪(贪恋荣华富贵,为人阴险精明)、李和平(外和平内则精通官场手段)等也可视作这个文化系列现象,他们是后文革改革开放形势下,经济和政治体制双重结合下官僚新贵和贪腐的典型。作者借制药厂职工的口声巧妙地表达了群众的愤懑:“像胡周银这样的人,连一个制药厂都管不好,而且举报信都堆成了山,偏偏他是官运亨通,居然当上副县长了。”
药厂小社会,实则是大千世界的缩影。小说在关注人事浮沉的同时,以独特的洞见,写出了官场人物的心理和文化。田浩禄因为拒绝做假证以协助胡周银夺取药厂厂长大权,被诬称为“喂不饱的狗”,卷入一场无法避免的旋涡,继而妻死子亡,连顶职的机会也被人捷足先登,不得已到销售部换一番天地。而范勇在得知细节后,也曾自责,因为当时见田与胡表面上走得近,他并没有积极帮田解决“户口”问题。作者借叙事主人公的心理把官场文化的内幕做了揭蔽:“领导们之间,表面上一团和气,平时都是笑嘻嘻的,背地里却在使暗劲儿,钩心斗角,拳打脚踢。”确实,官场文化是具有辐射感染力的,这一大酱缸之毒确难以斥清。以李和平为例,他冒充老同学田的口气,写匿名信欲把胡扳倒,好让自己当厂长,待见胡大旗不倒,却又在其手下更加恭敬,伪装得言听计从。其他的一些次要人物也是耐人寻味,值得一析。如王德满在八四年官复原职后,“首先培养自己的儿子入了党,后便顺理成章地接上了革命的班,当上了村长。”再如,贝锦卡酒楼是县工商银行信贷部张主任的老婆蔡姐开的。所有这些讯息加起来,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对当下官场史治的殷忧。
“农业户口”无疑是小说主人公在当代社会遭遇不公的重要语符,是小说在描述田与三位女子的情感纠葛时出现最多的关键词。覃怡红生下来就是“非农户口”,“天生就透着高贵。”她母亲高老师在得知女儿与田浩禄相恋时,认为不是门当户对,硬是拆散了他俩。向明玉因为招工考试,解决了户口,就比覃怡红的身份更高——供销社是大集体、“二国营”,以至田浩禄觉得跟她结婚是让她这朵“鲜花插到了牛粪上”。多年后,户口问题略有松动,郑菲菲建议浩禄去买一个“蓝本儿”(仅限于在县内使用的非农户口本),田浩禄唏嘘叹道:“过去我想有一个非农户口,是因为户口就是前程,就是生命的全部意义,就是招工就业的象征,就是各种社会保障和福利的代名词,含金量太高了”。而在这以前,最令人心碎的是他给自己未出生就夭亡的儿子取名为“公平”,并发出质疑:“为什么同样是人,却要被分成三六九等?为什么非农业户口的混蛋也可以招工当官,平步青云,为什么农业户口的才子却要饱受压抑之苦?为什么有的人一生下来就是非农业人口该高人一等,为什么有的人为了改变农业户口要埋葬自己的一生?”这些疑问无疑传达了对一个时代的反思与拷问。其它诸如粮票、黑市粮价等都烙下了一个时代的影像痕迹,有种不懈追问的气势。
二、民俗演绎,尽展巴土文化与风情
《红玉菲》中人物的出生起点是在盐阳村,第三部分《菲》正式创业成立医药公司时即名“盐阳医药公司”。小说借叙事主人公之口道出了“盐阳”内涵。“盐本来就是一种药,是生命所必须摄取的一种元素;阳,则是生命的阳气,阳刚。”考“盐阳”一词可得《后汉书》说:廪君蛮“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4]“盐阳村”今天的土家族亦即古代巴人后裔,“盐阳”构成了某种象征符号。
小说在展开情节,铺叙故事的同时,巧妙地穿插巴人起源的创世神话、传说和图腾崇拜。小说开始以梦境写“廪君与盐水娘娘”的传说。第二章《月圆江清》中也串廪君(向王天子)的传说。“很古很古的时候,在清江下游的武落钟离山,有赤黑二穴,廪君(巴氏之子巴务相)诞生于赤穴中,其余四姓樊氏、瞫氏、向氏、郑氏则居于黑穴之中。巴务相在部落之间的比武结盟中,因为善于击剑和造船,而成功地击败了另外几个部落的若干挑战对手,被推举为巴人的首领,被人们尊称为廪君。”
我们有理由认为,羊角岩笔下的盐阳、夷水、乃至巴山县都烙有巴人起源地——湖北长阳的印迹。他笔下的田、覃、向、郑都是古巴人姓氏的基本类别(覃是长阳县土家族最大的姓氏之一,有学者考证“覃氏源于瞫姓”)。此外白虎图腾崇拜,盐、斗、牛角等崇拜都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甚至田氏三姐弟“福”“禄”“寿”也留有鲜明的民族文化心理特色。
土家族作为巴人后裔,主要分布在湘鄂渝黔交界的武陵山区,而巴山县被认为是土家族摇篮。穿插于小说文本间最多的就是这样一种民族文化积淀与氛围。民歌,按民族文化文学概论可称为“礼俗歌”,“如祭族歌、婚礼歌、丧葬歌等。”[5]举凡薅草锣鼓的《一步到田中》,嫁女称“红事”而不称“喜事”,请“十姊妹”,唱《哭嫁歌》,姐妹唱《十杯酒》,娘家兄弟背着新娘上花轿等等。小说还穿插了民间歌舞表演和服饰,如撒叶儿嗬舞蹈、花姑子舞蹈、南曲、毛古斯、肉连响等,民族服装“一律大红颜色,在衣服、袖口和对襟上则镶上了金色的有着虎头和船船花图案的花边”。寿终正寝的老人是山民向往不已的“顺头路”,并不把老人去世当成一件悲伤的事,称“白喜事”,对孝子说“恭喜你尽了忠孝”,“欢欢喜喜办丧事,热热闹闹陪亡人”。哀乐套曲《十幡鼓》,歌颂母亲恩情的《十月怀胎歌》,跳撒叶儿嗬收场鼓师所唱的《刹鼓歌》,葬仪时所使用的唢呐、鞭炮、三眼铳等等构成了巴山(长阳)独特的民间民俗文化内涵。土豆粉蒸肉、土家凉皮、炕土豆、清江鲢于鱼火锅,喜欢吃辣等,则都体现出浓郁的土家饮食文化风格。
“情歌在少数民族文学中比较发达。‘以歌为媒’是我国众多的少数民族婚姻习俗,也是情歌在这些民族社会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体现。”[6]《红玉菲》中写情歌的片段和情节有三处,尽管情歌也属民歌,与礼俗歌有紧密关联,甚至可说候难舍难分,但由于爱情在文学上的独特地位与价值,本文将其单独列出,分析研究。如小说开头在写梦境时即穿插了巴人始祖廪君与盐水娘娘对唱情歌神话传说的情景:“上滩不急慢慢悠,爱姐不急慢慢逗,有朝一日逗到手,生不丢来死不丢,除非阎王把命钩。”(廪君),“小小鱼儿紫红鳃,下游游到上游来,游过百张金丝网,躲过千竿钓鱼钩,情歌钓我我上来。”(盐水娘娘)这是鄂西五句子情歌,羊角岩将其改造为创世神话中一个情歌对唱的场景。还有一处写田浩禄冲出盐阳,到建筑工地当民工建制药厂,回忆爱情,形单影只,独自唱那古老而忧伤的情歌,抒发爱情创伤:“昨日与姐同过坪,风又吹来雨又淋。风又吹来撑不得伞,雨又淋来交不得情……”
最具民族风情的场景莫过于浩寿(浩禄之弟)结婚时人们跳的花姑子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