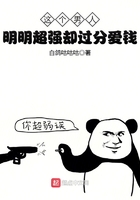睁开眼睛的时候,雪酿躺在一张梨花木的床上,身上的锦缎被子异常柔软。
环顾周围,华贵异常却处处透着危险的气息。不远处,一男子正坐在自己的对面品茶,两人之间虽只隔一道淡绿色的珠帘,却看不清容貌。
“你醒了?”
那声音带着并不友善的玩味,雪酿本不打算理会,可他却撩起珠帘踱着步子走到床边,双手撑在自己身后的墙壁上,像是盯着猎物一般。
“你是谁?”她下意识的问。
杨文翎忽然笑了起来,明明害怕的连声音都在颤抖,可是却假装坚强的样子真的很可爱。只是可惜,她的身份注定了只能是自己手中的一枚棋子,别无选择。
“我是谁并不重要,但是从今天开始,我是你的主子,唯一的主子。”
“雪酿独自一人,从未拜在任何人的门下,何来的主子。”高声回击,她不屑道,“还是说你这人生病糊涂了,见了一个人就想收为仆人!”
“怎么和主子说话呢!”
红衣女子的长剑出鞘,泛着冷光的剑锋已经触到她的脖颈。杨文翎抬抬手,“红鸾,对待雪酿要温柔些,她皮肤娇嫩,若是留下一两道疤痕就不美了。”
“你为何知道我的名字?”
“嘘!”单指抵在她的唇边,杨文翎邪魅的声音再次响起,“我不但知道你叫雪酿,还知道你虽是花满楼的头牌,却至今身子清白。只可惜,三日后,将被公开拍卖。”
“你到底是谁?”
“还是那句话,我是谁并不重要,你只要记得,从今往后,我是你唯一的主子就够了。”
雪酿一股怒气冲到头顶,连思考都省了一口咬上他的手臂,死死的不肯松开。
杨文翎也不挣扎也不怒,只是平静的看着她,眼底有着笑意,好似在看闹剧一般。
她被那股平静威慑到,不自觉的松开了嘴,背对着的红鸾用余光瞥见主子手臂的血迹后不由分说的直接扇了一巴掌过去。雪酿只觉得嘴里的腥味扩大,脸颊也火辣辣的疼。
“如今可是舒服了?”杨文翎似是怜惜的拂上瞬间肿起的脸,“这就是不听话的代价。”
他拒绝了红鸾的包扎,趁着雪酿皱眉之际快速将一粒白色药丸塞进她的嘴里,并强迫其咽下。
“你给我吃的是什么?”
心里有一种不好的预感,雪酿想要将其抠出来,奈何只是徒劳。
“一种白色的药丸而已,无毒无害。只是它里面包含一只叫翠谷的蛊虫。”他钳制住那好看的下巴,眼底露出与此时不相符合的怜惜,“只要你乖乖听话,翠谷就会安稳的休眠,若你不听话,它便会开始吃你的血,直到雪酿变成血酿”
“卑鄙!”
狠狠的朝他的脸上啐了一口,雪酿的另半边脸很自然的又被扇了一巴掌。
“这算不得什么,日后你会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卑鄙。”他嘴角弯起弧度,指着刚燃起的香,淡淡道,“你有一柱香的时间考虑,是现在就顺从的应了为我做事,还是待会儿生不如死的求我为我做事。”
“不需要考虑!我就是死也不会为你做事!”
“死?不不,我想你误会了,死太简单了。”
“雪酿!”
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凤姨从门口缓缓走了进来,眼里是她熟悉的冷漠。
“凤姨?”
视线在三个人只见徘徊,雪酿似乎明白了些什么,她很想笑,哪怕扯着嘴角很疼。
“这就是凤姨的主子?”
“是,也是你的主子。”凤姨面不改色,一杯人参茶递过去,“主子请用茶。”
“这下你可明白了?整个花满楼都是我的,而你,花满楼的头牌,自然也是我的。”杨文翎优雅的端起茶盏,浅饮一口,“所以,你的命当然也是我的。”
“若我不答应呢?”
“你以为自己有得选择?”
他弯着眉眼,一只手却突然狠狠的掐住她纤细的脖颈,雪酿感觉空气一点点被夺走,整张脸涨的通红,她拼命的拍打着那看似纤细却十分有力气的胳膊,但对方却丝毫没有松开的迹象。
“我想,这样的痛苦并不会让你记得谁是你的主子,但我要告诉你,你的命随时都掌握在我手里,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亦是!”缓缓的松开手,他对凤姨招招手,“人是你调教的,自然也该你让她彻底的记住谁是主子。”
“是,红凤明白。”
说着,凤姨从怀里掏出一片窄窄的竹叶,只见它通体翠绿仿若未经雕琢便已天然成型的翡翠。将其放到唇边,轻轻一吹,一曲悦耳的曲子便流淌在空气中。
三人好似沉醉在曲子中一般,神色享受,只有才缓过气来的雪酿感觉全身上下像是有万万只蚂蚁在到处爬动,她很想挠一挠,双手却被红鸾死死的按住。
“若是挠坏了,就卖不得好价钱了哟。”杨文翎依旧是那调侃似的音调,里面却充满了冷酷无情。
随着曲调的转折,雪酿只感觉瘙痒的感觉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蚀骨的疼痛。她全身蜷缩在一起,骨头像是被人一刀刀的剁碎、血肉更像被人用弯刀一次次的剜起般。
“啊!”
她紧紧咬住嘴唇,不想在这群人面前屈服,却还是忍不住叫了出来。
“杀了我!你杀了我!”
“杀了你?”像是抚摸爱人一般,温柔的拭去她脸颊上如水的汗珠,杨文翎叹息道,“我舍不得。养了你十年,一刀杀了岂不是赔本的买卖?我虽不是商人,却也懂得这个道理,没有收回成本前,是不能放弃的。哪怕商品已经毫无价值,只要持有者还有兴趣,仍旧可以任意处置。”
曲调还在继续,雪酿恨不得用眼神在他身上刺出千千万万个洞,但只是一瞬间,她仍旧只能疼痛的满床打滚。
“替我办事你不亏的。”转身走向珠帘后的椅子,他幽幽道,“差事办得好,荣华富贵自不必说,若最后我还对你有兴趣,封妃入宫也不是不可,毕竟女人的身子对我来说清白与否并不重要。”
“封妃……入宫?”她倔强的咬住锦被,用仅存的思绪来理解他的话,“你……到底谁!”
“女人与男人讲话,不要吼,知道吗?”
“你到底是谁!”
雪酿用尽所有的力气喊出这句话,真个人却被忽如其来的冷气折磨的哆嗦不成人形。
“你很痛苦是吗?那就喊出来啊,只可惜,这里没有人会救你,更没有人敢帮你。”杨文翎心情大好的抚了抚衣袖上的褶子,“雪酿,你没有别的选择,除了死,只能心甘情愿的帮我做事,当然了,死,你是死不成的。因为翠谷只是会让人生不如死。”
雪酿的美丽的眼里充满猩红的血丝,偶尔似乎还有极细的细条形状突起。周身的寒冷让她觉得自己好似掉进了冰窖,又疼又寒,就连喘出的气都带着霜。
“再考虑一下吧,或许明早你就有答案了。”
说罢,杨文翎示意凤姨停下来,但是翠谷的疼痛丝毫没有减轻,反而更加疯狂,整间屋里,回荡着她痛苦的哀嚎。
月亮升至夜空的最中央,窗外一个黑衣身影徘徊良久,最终选择默默离去。
天边泛起鱼肚白的时候,雪酿已经记不清自己昏死过多少次,只是再次睁开眼的时候,瑚岚肿的如核桃一般的眼睛和那熟悉的嘤嘤哭声唤起了熟悉的记忆。
六岁那年,凤姨将瑚岚和自己从乞丐窝里抱了出来,从此,她便是花满楼的头牌,衣食无忧,再也不用与那些又臭又坏的乞丐争抢一碗已经馊了的泔水。但是,随之而来的却是十年囚禁般的生活。
没有人告诉她长大后要做什么,只是不断的灌输十六岁被拍卖的时间观念。
“瑚岚。”
她的嗓子嘶哑如垂暮的老人,一双颤抖的手想要触摸熟悉的温度却在空中快速垂落。
“主子,主子你醒了吗?”
瑚岚将她的手紧紧的攥住,眼泪不由分说的再一次夺眶而出,眼前这个被折磨的不成人样的女人真的是那个曾经千娇百媚的主子吗?
她的眼睛曾经宛若磁石,如今却空洞无物,毫无生气的脸就像被抽干血肉的木偶。
雪酿很想扯出一个笑容宽慰瑚岚的心,但是用尽全力也只能眨一眨眼睛,干裂的嘴唇不做任何表情已经疼的深入骨髓。
“主子,别勉强自己。”沁湿一方素帕,小心翼翼的擦拭着她的脸颊,眼泪仍旧一滴滴的往下落。
“瑚岚知道主子无法接受现实,但是现实就是如此,谁都无力改变。昨日夜里,我就被绑在门外,听着您一声声的叫,却连寸步都难行,咱们现在根本无力反抗,纵使以卵击石却连求死的能力都没有。”
听着她断断续续的说着,雪酿也忍不住流下泪来,这一次不是因为疼,而是哭瑚岚的无奈和自己命运。
“主子,您就听瑚岚一句,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想一想您游历天下的梦想吧,想一想您对自由的向往,若是眼下连命都没有了,还谈什么未来呢?”抬起她的手,瑚岚的动作轻若飘云,“不要管那位主子是谁,瑚岚只想您能活着。”
泪水滑落在白玉的枕头上,良久,雪酿那双毫无生气的眼睛里有了丝丝情愫,她点点头,却没有说话。
是的,昨夜他说的没错,自己根本就没有选择,除了认他当主子,帮他做事,再者便是生不如死的折磨。
墨渠的脸再次浮现在脑海里,他的笑容就像一轮红日,温暖着这具冰冷似死尸般的身体。
自己还没有穿上嫁纱,还未成为他的妻,怎么可以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去?
想到这里,她再一次对着瑚岚点了点头。心里宣誓道,我要活下去,不管用什么方法都要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