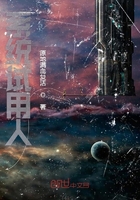且说贾琏向凤姐要银子,欲盖目下之短行,谁知银子没要到,反彰露从前之劣迹,只得悻悻而去,另找贾珍父子商量不提。
如今只说贾政回家,众子侄俱来请安。贾母问了一回探春的消息,贾政少不得禀明一番。贾母年迈之人,想着小孙女远在异域他乡,一无亲故,心下不免伤感。贾政少不得安慰一番。然后弟兄相见,齐到宗祠行礼。众子侄都随同前往。拜祭罢,贾政于祠旁厢房坐下,叫了贾珍、贾琏等人过来,问起家中事务。贾珍拣可说的说了。贾政道:“我初回家,也不便来细细查问,只是听见外头说起你家里更不比从前,诸事要谨慎才好。你年纪也不小了,孩子们该管教管教,别叫他们在外头得罪人。琏儿也该听着。不是才回家就说你们,因我有所闻所以才说的。你们更该小心些。”贾珍等脸涨的通红,也只答应个“是”字,再不敢多言。贾政也就罢了。回至西府,王夫人吩咐厨下整酒,与他接风洗尘。贾环、贾兰替另拜见。那些家人小厮,丫头媳妇,一齐俱来磕头。贾政见贾兰越发出落的面如满月,丰姿俊雅,深为欢喜。再看贾环,大是粗鄙暗昧,仍是先前模样,究竟不甚钟爱。歇息了半日,忽然想起一直未见黛玉,便问王夫人:“为何如今短了一人?”王夫人知是想着黛玉,前因家书未报,现又才到家,正是喜欢,不便直告,只说是病着。问宝玉时,便一力夸赞宝钗,说是幸而他的功劳,宝玉的病才日渐的好了。因撺掇贾政:“宝玉如今也不小了,是时候也该正经议亲了。若论模样儿,行事做人,宝丫头一概应是首选。”贾政迟疑道:“宝玉的亲事不比别人,只怕还要先问问老太太。”
正说着,见赖大一脸汗进来,禀道:“老爷,才听见信,史家被抄了!”贾政一惊非小,霍然起身,问:“究竟所犯何事?”赖大道:“定的是‘结交外官,外任亏空’。另外还有几件事。”贾政道:“快说。”赖大道:“有人告发东府里的珍大爷引诱世家子弟赌博,这一款还轻;前阵子,忠顺王爷因其是卓异的官,举荐说‘人品贵重,必能承担大业’。就着其署了关差的印。谁知如今竟反过来告其‘为利忘本,走到银子窠里去,索诈贪污,私弄手脚,扭曲作直,非刑拷打’,又弹劾什么‘一印数官’;还有一大款,咱府里的琏二爷国孝、家孝期间,强占良民之妻为妾,因其不从,凌逼致死。又还拉出一个姓张的来。只怕连都察院都有不是,为的是姓张的起先告过。”贾政不觉眼中流泪道:“不争气的畜生,番番撞祸!非要闹到家败人亡方算了事!”赖大抹着汗道:“还有,隐匿江南甄家和如今坏了事的史家的财物、人犯……”贾政跺脚道:“了不得了!”赖大又道:“还有,以死囚把薛家大爷替出逃匿之事;又有御史参奏平安州,迎合京官上司,虐害百姓好几大款。”贾政慌道:“那管他人的事!到底打听我们的怎么样?”赖大道:“说是平安州,就有我们,那参的京官就是咱家大老爷。说的是包揽词讼,重利盘剥,百姓受害,有冤莫诉,有苦无伸。”贾政不等听完,眼中簌簌流泪道:“大老爷也忒糊涂,东府也忒不成事体!”因急的即忙望宁府飞走过去。
谁知,气未喘定,一时又有周瑞家的慌慌张张的进来禀报:“太太,才孙家派人送了讣闻来……”王夫人豁然起身:“谁家?”周瑞家的颤声道:“孙绍祖,孙家。说是,咱家二姑娘殁了。”王夫人满眼流泪道:“什么时候的事?怎么就殁了?”不等回话,便又喃喃垂泪道:“我就知道,那孩子……活不长……”一语未完,只见凤姐泪光满面,扶着小红颤巍巍的进来:“太太,这个事,可怎么回老太太去呢?”王夫人心如刀绞,泪下沾襟:“这事瞒不住。你就过去实说了吧。”凤姐痛哭一场,凄惶而去。一时贾母闻知,痛的肝裂肠断,老泪纵横:“多大个年纪,离了我才几天呢!”因让立即去把贾赦、邢夫人叫来,一面又痛哭道:“我只朝他两个要人,作爹当妈的,不替孩子打算,生把个小命儿给断送了!”凤姐等生怕哭坏了贾母,忙收泪百般劝慰。谁知,贾母一时又想起黛玉来,想着府里如此连三接二,都是不如意的事,那里搁得住?心口疼的哭一声“肉儿”,叫一声“林丫头,二丫头”,道:“怎么就忍心早早的把我抛撇下,就都这么去了!只留着我这老废物,在这里做什么!”一时贾赦、贾政、邢夫人等听见消息,纷纷过来,合力再三安慰,方止。众人俱守着贾母,至深夜方散。
只说贾政回来,因告诉王夫人,才在东府里听见说,薛蟠如今重又被捕回来,正等着重新治罪。王夫人心下煎熬,沉吟不语。半日,方垂泪说:“他是自作自受,现在连老天也帮不了。”因趁便也将黛玉已死的话告诉。贾政唬的魂不附体,不觉掉下泪来,连声叹息。王夫人也撑不住,在旁痛哭一场,又细说了一番李纨当时如何一力操办的后事。幸有玉钏等人在旁百般劝慰,方勉强止住,重又说些喜欢的话。因就便说道:“眼下老太太这样伤心,两府里又接接连连的诸事不顺,不如趁势把宝玉的婚事给办了,必要借喜气冲一冲,或许就好了,也未可知。”贾政道:“才老太太也是这个意思。我还纳闷呢,怎么这个时候跟我说起这事来了。又说打卦的说,要娶个金命的人过来帮扶。又说有‘金玉’的道理,婚是不用合的了,即挑了好日子,按着咱们家分儿过了礼。赶着挑个娶亲日子,就照南边规矩拜了堂。原来竟是这样。”说着,见王夫人又是一包眼泪,因又想到他身上,复又道:“老太太这个年纪,既有这个意思,我那里还敢违拗?自然是老太太的主意,该怎么便怎么就是了。但只姨太太那边,不知说明白了没有?”王夫人拭泪道:“姨太太是早应了的。只为蟠儿的事先前没了干净,所以这些时候总没提起。”
贾政道:“这就是第一层的难处。哥哥在监里,妹子如何出嫁?再者,我的起身日期,再不敢多耽搁,就只这几天,可怎么办呢?”因夫妻们盘算了一夜。第二日,贾母叫贾政过去,商量道:“你若诚心给他办呢,我自然有个道理,包管都碍不着。姨太太那边,我和你媳妇亲自过去求他。蟠儿那里,我另央人去告诉。如今府里如此连三接二,都是不随意的事,必要借喜气冲一冲,方可扭转。从此,一天好似一天,岂不是大家的造化?这会子只要立刻收拾屋子,供喜神,准备花烛,铺排起来。一概亲友不请,也不排筵席,只为冲喜。宝丫头心地明白,是不用虑的。内中又有麝月,也还是个妥当孩子。再有个明白人常劝着更好,他又和宝丫头合的来。再者,姨太太曾说宝丫头的‘金锁’也有个和尚说过,只等有玉的便是婚姻。可知这段姻缘,是早就注定了的。这么着,都赶的上。你也看见了他们小两口儿的事,也好放心的去。”贾政听了,不敢违命,勉强赔笑说道:“老太太想的极是,也很妥当。只是要吩咐家下众人,不许吵嚷的里外皆知,这阵子办这个事,总是有越礼处。姨太太那边若果真应了,也只好按着老太太的主意办去。”贾母道:“姨太太那里有我呢,你去罢。”贾政答应出来,心中好不自在。因赴任事多,兼两府里诸事连连,自然少不得各处夤缘请托,种种应酬不绝,竟把此事听凭贾母交与王夫人办理。
只说这夜,窗外唿喇喇刮起一阵怪风,刮的影乱灯昏。贾政连日内无来由的耳热眼跳,意乱心慌。这时只觉困倦上来,倒身便昏然睡去。恍惚间,只见元春浑身血淋淋的走来,眼中垂泪,口叫:“父亲。”贾政大惊,急躬身跪下:“娘娘这是那里来,如何竟这般形容?”元春滴泪道:“父亲,孩儿遭奸人陷害,可怜数载宫闱,敬修懿德,克谐内助,夙夜匪懈!如今被奸贼做害我一个大逆不道之罪,不能辩雪。孩儿怎肯贻羞父母,辱败宗社?而今,儿命已入黄泉。只因心里放不下父母双亲,故来相告。”贾政听见“儿命已入黄泉”几个字,唬的魂不附体,满面泪流,竟再也道不出一个字来。元春悲悲泣泣,泪下沾襟道:“从来富贵若浮云,吉凶倚伏信难分!但看古往今来那些豪门望族,无不是先祖们九死一生挣下家业,无奈膏梁的子孙,性情异样,安乐场中,并无善书入目,善言入耳,那肯效法祖先,培植后来的元气。终日妄行妄为,一朝生事则百计迎求,父为子隐,群小迎合,虽暂不罹祸网,而从此越加放胆,必至破家灭族方罢。何况宦海风波,险巇无常,无异袖蛇而走,抱虎而眠,还望父亲及早抽身退步为上。需知冰山不久,梦景无常,早寻觉路要紧。”一语未尽,只见烈焰腾空,直透九霄,元春踏起五色莲花,冉冉腾空而去了。
贾政举步相送,竟被绊了一跌,惊醒转来,已是一身冷汗淋漓。王夫人在旁亦醒,忙让点灯上来。贾政不住搓手嗟叹:“回京多日,几次使人进宫探听娘娘消息,无奈至今亦无音信。使我日夜不安,心神恍惚。”王夫人在旁簌簌落泪道:“我才梦见娘娘身穿血衣,拉着我大哭不止,未知有何吉凶?”贾政闻时,竟如顶梁骨失了真魂,再出不得一声。只是心内乱想:“怎么我和夫人竟同时做此恶梦?想是娘娘必有不祥之事,故我终日心神惶惑。”因不肯惊扰了王夫人,只说:“无妨。”便就安寝。只等天明再使人到宫里去打听,看是到底如何。
且说宝玉如今日渐将养过来,因便拄着拐,日日踱到潇湘馆、木石盟处徘徊瞻顾。因想着从前的欢笑盟约,今日之寥落孑然,后日相思熬煎的光景,不觉越添了怨痛积伤。又见那株石上仙柏,满树枝叶均已萧然剥落,树干却依旧冷逸凌云;石子后面的小竹细草,在风中摇摇落落,似有无限幽意隐隐。因伏在山石上大哭一场:“林妹妹,我只道送了三妹妹回来,便可完结心愿。谁知如今竟与你天人永隔!你如今到底是那里去了呀!你可知道,我如今真正是被逼的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妹妹若在天有灵,就请来对面开示一语,告诉我,这场伤心,何日才能了结收场?”因又摇摇晃晃的走至潇湘馆去叩门,满嘴只叫:“紫鹃,开门。”却见苍苔露冷,院门紧锁,院内阒然无声。隔着门缝看进去,满眼只见落叶萧萧,寒烟漠漠,不觉更复泪如雨下,连又叩击数十下,只管伏在门前大恸不止。谁知麝月在后远远走来,见此情状,不觉停下脚步,掩面泣下。宝玉那里浑然不觉,仍旧扣门一声,哭喊一声:“林妹妹,我来了……紫鹃……雪雁……快来开门!”麝月实在看不下去,哭着跑过来,扶起他道:“二爷,快回去罢。老爷叫呢。才和老太太商量了,三日后,要给你和宝姑娘完婚呢。”
宝玉如闻惊雷霹雳,震的两眼睖睖睁睁,半日无语。麝月生怕他又激出病来,忙紧紧的拉着,一路去了。宝玉之病,原本尚未大愈。如今一腔深情正为黛玉不能解释,又听见要让他和宝钗完婚,因更加神出鬼没,不得主意。任人上前如何问话,只是不答。麝月深怕他旧病复发,因满屋里又点起安息香来,定住他的神魂,扶他睡下。谁知宝玉人在昏睡中,依旧满嘴里只是哭嚷:“林妹妹,我如今要叫他们弄成了一个负心的人了!非是我负你,一死一荣端有谓,苍苍造化意何深!”
谁知惜春因接连情殇了黛玉,孽殁了迎春,不免兔死狐悲,凄惶自伤,终日似染怔忡之症,愈发与人隔绝了。可巧这日在地藏庵里看到一篇忏悔文:
弟子自违真性,枉入迷流。随生死以飘沉。逐色声而贪染。十缠十使积成有漏之因。六根六尘妄作无边之罪。迷沦苦海深溺邪途。着我耽人举枉措直。累生业障一切愆尤。仰三宝以慈悲。沥一心而忏悔。所愿能仁拯拔善友提携。出烦恼之深源。到菩提之彼岸。此世福基命位各愿昌隆。来生智种灵苗同希增秀。生逢中国长遇明师。正信出家童真入道。六根通利三业纯和。不染世缘常修梵行。执持禁戒尘业不侵。严护威仪蜎飞无损。不逢八难不缺四缘。般若智以现前。菩提心而不退。修习正法了悟大乘。开六度之行门。越三祇之劫海。建法幢于处处。破疑网于重重。降伏众魔绍隆三宝。承事十方诸佛无有疲劳。修学一切法门悉皆通达。广作福慧普利尘沙。得六种之神通。圆一生之佛果。然后不舍法界遍入尘劳。等观音之慈心。行普贤之愿海。他方此界逐类随形应现色身演扬妙法。泥犁苦趣饿鬼道中。或放大光明。或见诸神变。其有见我相。乃至闻我名。皆发菩提心。永出轮回苦。火镬冰河之地。变作香林。饮铜食铁之徒。化生净土。披毛戴角负债冤。尽罢辛酸咸沾利乐。疾疫世而见为药草。救疗沉痾。饥馑时而化作稻粱。济诸贫馁。但有利益无不兴崇。次期累世冤亲现存眷属。出四生之汨没。舍万劫之爱缠。等与含生齐成佛道。虚空有尽我愿无穷。情与无情同圆种智……
他本是有宿慧的,一见此言,当下便幡然彻悟,原来盛衰本是回环,万缘无非幻泡。为人在世,不过镜花水月。今正好借此清净之地,虔修来生,以脱金枷玉锁。因自此,索性住进庵来。终日动静尊严,意不散乱,屏息万缘;内心既寂,外境俱捐。入夜焚香趺坐净修,自摄其心。早朝夜晚,淡水蔬食,清静无为,倒也无荣无辱;暮鼓晨钟,一盏清灯,半床禅榻,更觉乐在其中。
贾珍、尤氏闻知,虽多次遣人前来访寻,无奈何,他执意不愿意再回俗尘。贾珍、尤氏虽然日日相互指责抱怨,也只得随他去了。不知后事如何,下回分解。